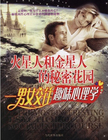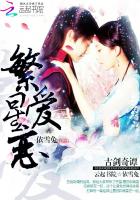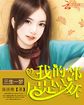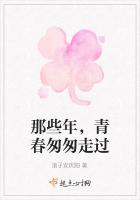除邱紫华、钱念孙的著作外,还有几种从宏观上对中西文学特质和规律进行探索的小册子。其中,白云涛的《酒神的欢歌与日神的沉咏——中西文学传统比照》(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从文学类型、作家的经济收入与知识结构、审美风格、文学的文化土壤与文化精神及小说诗歌作品等几个层面入手,对中西文学的不同的传统做了比较观照。肖锦龙的《中西文化深层结构和中西文学的思想导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在对中西文学史上的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中,试图总结中西文学思想的特质。邓晓芒的《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西方古典作品中选取了几部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若干代表作品进行比较,从哲学的角度对中西文学中人物形象的人格结构做了分析和总结。这几本书都在十来万字的有限篇幅内试图从宏观上抽绎出中西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虽不乏一些新的见地,但总体上看,这类研究还只是处在初步的、尝试性阶段,它也是今后的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研究应该努力开掘的重要领域。
(第三节)西方文论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研究
西方诗学或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研究,与上述平行阐发的研究不同,主要是传播、影响和接受的实证性研究。1980年代后,国内多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有关的论文。90年代,又出版了若干种专门著作。以专著而论,有四本书很重要,那就是罗钢著《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论》,殷国明著《二十世纪中西文学理论交流史论》,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和王攸欣著《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
罗钢(1954—)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中西现代文学理论比较研究的著作。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共分六章,前五章分别对周作人、茅盾、郭沫若、梁实秋四位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对五四时期及2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了研究,最后一章对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接受的基本机制和规律做了总结。作者对所要研究的“点”的选择是颇见眼光的,虽然只是周作人、茅盾、郭沫若、梁实秋等四个人,但他们却分别是中西某种重要文学理论思潮——如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的纽结点,具有典型性的、标本式的个案研究的价值,通过它们可以抓住五四时期至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论的“汇流”之脉络。作者深入系统地研究了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着力考察了西方现代文论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发生的创造性的变形和转化,并以中西文论的“汇流”为切入点,总结了中西文化交流和转化的基本规律。作者在每一章中都有独到的看法,它们均曾在出书前公开发表过,并被不断转载和征引,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其中,关于梁实秋与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关系研究一章,尤显新意,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文章。
殷国明的《20世纪中西文学理论交流史论》,在论题上与上述罗钢的著作基本相同,但论述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20世纪中西文论关系史的较为全面系统的著作。读书界需要这样一部全面系统的著作,因此该书在选题上相当有价值。当然,说它“全面系统”也是相对的。20世纪中西文论交流中的问题毕竟十分复杂,殷国明的这部书也采取了以点代面、以史代论的方法。全书共分上下两编。第一编主要以中西文论交流中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中心,分专章展开个案的研究。这些人物分别是王国维、梁启超、尼采和弗洛伊德、鲁迅、庞德、克罗齐、钱钟书。下编则以西方文艺思潮为切入点,分专章分别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与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作者在研究这些问题时,较充分地吸收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有关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例如,在《导言》中作者从中国古代的“通”与“同”这两个概念的阐发入手,指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本身,就是一本新的、更大范围内的‘同’与‘通’的历史。中国人在文中再一次发现了‘同’——这个‘同’是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相交接、相交流、共命运的‘同’,同时又是在多样性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和发扬自己特色的‘通’——的意义。”又如,在上编第六章中他提出了“红色古典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1949—1979年期间以共产党的理论原则创造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形态,是很有道理的。但本书在研究对象的厘定和框架结构的安排上,似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上编第六章《往者与来者相遇——古典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所论之古典主义主要属于“文学思潮”的范围,但作者为什么把这一章置于上编而与人物并列,却不是放在下编与其他的思潮并列?从本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上看,作者是将“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潮”做同一观了,而且是以“文学理论”涵盖“文学思潮”。实际上,一般看来,“文学思潮”的概念大于“文学理论”,因为“文学思潮”需要由理论和创作两根柱子来支撑。而且作者在论述文学思潮时,例如在谈到象征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时,用了不少篇幅对中国古代的“象征主义”展开论述并以西方的象征主义进行平行的对比,虽然这种对比也许是必要的,但却使话题离“中西文论交流”远了些。这些就造成了全书的“史”的客观性与“论”的主观性出现了视域不太重合、不太聚焦的问题。
作为一部比较完整的文论交流史,殷国明在上述著作中以意识流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心,以最后两章的篇幅论及80—90年代中西文论的交流。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西文论的交流空前活跃和空前复杂,这些文字远远不能说明其中的源流经纬。2000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从“文学批评”这一视角,详细地评述了西方文学批评在当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的情况,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选题上体现了将历史意识和学术的当下性乃至前瞻性相统一的敏锐眼光。该书以西方不同的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为单元,分专章评述了西方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情况。在《绪论》中首先做了概观,然后依次评述了精神分析学、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美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映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十一种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的引进和批评实践。
全书结构布局清楚合理,反映了主编对论题的清晰准确的统驭与把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些章节的执笔者同时又是他所研究的那种西方批评方法在中国传播与实践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如,王宁撰写《精神分析批评学批评在中国》,叶舒宪撰写《神话—原型批评在中国》,金元浦撰写《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在中国》等,都有助于强化本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全书各章对西方有关文学批评流派方法的介绍和梳理简明扼要,对西方文学批评在当代中国的流转际遇的材料掌握比较充分全面,可以成为读者了解这方面情况的首选参考书。当然,也存在一些值得再讨论的问题。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实践者,客观地说是功过并存,成败参半。由于本书的作者们对西方各种新批评在中国的接受与实践基本上采取了赞赏的态度,再加上所评述的当事人是当今学界的活跃者,因而对西方文学批评运用中的许多负面现象指陈不够,剖析、批评乏力。
例如,书中提到的甚至表示赞赏的某些热衷于西方文论的文学硕士博士乃至中青年教授们,常常以外来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方法”来掩盖思想的陈旧与贫乏,以莫名其妙的新名词、新概念来包装和粉饰陈词滥调,甚至有些人写文章时故意“解构”现代汉语的句法规范,故意混淆“体验”的、朦胧诗式的破坏性语言与规范的学术语言的界限,给出的书名或写出的文章、文句令人莫名其妙,如同梦呓,将学术研究变成了无聊的文字游戏,败坏了学术空气,对学习中的青年学生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对此,学术界已不断有人撰文指斥和批评,甚至是指名道姓地指斥与批评。这对于维护求实、扎实的学风是必要的。作为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总结性的著作,《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在这方面理应有着明确的态度。
在西方诗学对中国的影响研究方面,除了上述的历史梳理和断代性的、概论性的研究之外,还出现了以个别人物为中心的个案研究,有关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王攸欣的博士论文《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王国维和朱光潜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史具有典型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王国维的研究,关于朱光潜的研究,也有大量论文和若干专著问世。但将两人的美学贡献置于“中国美学接受西方美学”这一语境中加以研究,此前还无人尝试过,在选题上是新颖的。这种课题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比较的研究,第一个层次是以王国维、朱光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对西方美学的接受研究,第二个层次是王国维与朱光潜之间接受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王攸欣以他们两人为中心对中国现代美学接受西方美学进行个案剖析,具有重要价值,有新意而又不偏僻。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美学的研究。
作者认为,虽然王国维在理论上颇怀疑叔本华的解脱是否真能实现,但在《红楼梦研究》中还是着力论证《红楼梦》是表现“解脱”的,因此符合文学的最高理想;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的全部观念直接来自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是叔本华的“理念”的对应物。中编是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的研究,指出30年代的朱光潜在有关论著中都是以克罗齐美学为理论支柱的,但朱光潜未能全面把握克罗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思维、概念和运用方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发生误解,其接受“是不够成功的”。
后来朱对克罗齐的理解更深入了,但由于时代环境和政治压力等诸种原因,他和克罗齐逐渐拉开了距离,甚至对克罗齐做了全面否定和批判。但王攸欣分析说,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克罗齐的影响在于促使朱光潜尽量远离其观点,这种影响决不可轻视,是决定朱光潜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来作为其美学支柱的重要因素”。王攸欣的这个结论为比较文学中的“反影响”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
王攸欣在评价朱光潜《诗论》中提出的“诗的境界”(王简称为“诗境论”)时认为,诗境论是融合东西方美学的自觉的尝试,是以传统审美趣味为根基,以克罗齐美学为骨架,表达了近于王夫之诗论的思想,作为探讨诗歌乃至艺术本质的理论是“不太成功”的。下编是王国维与朱光潜两组接受的比较,分析了两人在接受西方美学的背景、方式和接受观念的异同。全书表现出了学术研究中可贵的独立思考的、批判的精神,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见。看来,今后要使中西比较诗学和比较美学进一步深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深度的个案研究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