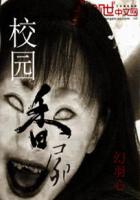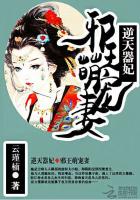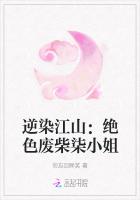所谓“跨学科”研究,不是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也不是局限于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应是指外来文化与学术思潮——包括外来宗教、哲学、美学、心理学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其实质是以跨文化为前提、以跨学科为途径与手段的文学研究,简言之,“跨学科研究”就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学”方法。20世纪最后二十年间,颇有人提倡“跨学科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提倡与研究成果之间还存在相当的差距。
(第一节)“跨学科研究”的理解、界定及研究
“跨学科研究”,也称作“超学科研究”或“科际整合”,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学科的界限,研究文学和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把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美国学派”的主张。雷迈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说:
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研究文学跟其它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大都全盘接受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有的比较文学基本理论教材甚至用五分之二的篇幅、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跨学科研究问题。但似乎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无条件的,那就是“跨学科”的同时,必须“跨文化”,即超越民族、超越国界或语言。
换言之,“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才是比较文学研究。这实际上似乎也是雷迈克的原意。上引雷迈克定义的第一句话“超越一国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它……”这样的表述,也清楚地表明“超越一国文学”是一个前提条件或限定因素。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则“比较文学”难以包容和涵盖“跨学科研究”。诸如“文艺美学”、“文艺民俗学”、“文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都是“跨学科研究”,但恐怕没有人将它们视为“比较文学”。“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都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
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往往都是“跨学科”的。即使纯粹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实际上也是跨了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是,我们却难以把这些称为“比较文学”。
由此可见,假如把“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研究对象、研究领域而不是研究方法来看待,则研究的可操作性就成大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的学力有所不逮,精通多学科的全才、通才在“知识爆炸”的当代社会不知可有?搞不好就会务广而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学科对学科的研究往往大而无当而不可行。所以,我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较为成功的个例(如钱钟书的研究)是将“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使用,即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超越文学自身的范围,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而并不是将多个“学科”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笼统地谈论文学与另一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跨学科”的方法也就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学”的方法。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成果也不太丰富。对此,杨周翰先生在1989年在为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文中说:
本来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它艺术或其它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对于前者,我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后者,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显然不足,不少人对这种研究方法还相当陌生。这当然与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介绍工作甚少有关,恐怕更为重要的是,从事这方面实际研究工作的学者并不多。
因而杨先生特别赞赏乐黛云、王宁两教授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认为“乐黛云、王宁同志先行一步,他们主编的这本《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为我国比较文学学者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杨先生在这里也明确地把“跨学科研究”界定为“研究方法”。这比此前和此后流行的某些比较文学教材上的界定显然更为准确。王宁在本书《导论》中也明确指出了“超学科研究”是一种“基本方法”——
我认为,所谓超学科比较研究除了运用比较这一基本方法外,它还必须具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两极效应。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另一极则平等对待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及其它艺术门类的关系,揭示文学与他们在起源、发展、成熟等各阶段在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然后在两极效应的总和中求取“总体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它的起点是文学,经过了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本体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本体超越,得出的结论大大超越原来的出发点,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可以说是对“超学科(跨学科)研究”的这一基本方法的具体而又正确的界定。《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是一本论文集。收乐黛云、王宁、张首映、许明、徐志啸、张连奎、王锦园、吴晓明、王长俊、孙津等人的十五篇文章,论述了哲学、语言学、宗教、艺术、心理学及当代西方有关文化思潮与文学的关系。以概述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总体关系的文章为多,而真正把“超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文学基本方法并运用于具体问题研究的少。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80年代我国比较文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一般理解和实际的研究取向。
不过,鉴于此前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文章和著述不多,对有关问题加以论述虽因话题太大而不免蜻蜓点水,但对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还是有启蒙之功的。特别是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文学与其他艺术》两篇长文,既纵向地梳理了文学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的关联,又紧追当代世界自然科学及其他学科的新趋势和各门艺术的新潮流,高度概括了文学与自然科学、与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具有很高的信息知识含量。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有关观点和材料也运用到了乐黛云撰写或主编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与教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90年代后,“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仍然不够景气,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是太少。由于跨学科研究范围极大,这方面的单篇文章选题不便,故十分少见,专门著作也同样的少。1980年代中期,为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对文学研究的束缚,文学批评界兴起了一股“方法论热”,视图从国外的其他学科领域,引进新思维和新方法,寻求文学评论的新视角和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其中,自然科学中的“熵”原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被许多人推崇并加以运用。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南京大学汪应果的《科学与缪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该书试图运用自然科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它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系统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域从混沌向有序转化的机理和规律——来解析中国现代文学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具有80年代后期“方法论热”的鲜明印记。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论述了中国新文学的起源与自然科学精神的关系,中编用耗散理论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嬗变及有关作家作品,下编论述了自然科学修养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该书在自然科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上有探索之功,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在看来,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这种嫁接主要还停留于自然科学相关概念的移植与运用,有时为使用而使用,就不免显得牵强。十年后,在这方面又有刘为民的《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出版,这是一部有一定系统的专题论文集,以自然科学为切入点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探讨了科学思想、科学思潮、科学知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文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诸学科的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较之自然科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切合实际需求,也可收到良好的学术效果。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叶舒宪在比较神话研究(详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就是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随着研究实践经验的日益积累和丰富,叶舒宪在这一点上越来越自觉,并在进入21世纪后系统阐述了“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详见《文学与人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他还倡导文学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与性学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出版了《文学与治疗》和《性别诗学》(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两部专题论文集,可以看作是“文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延伸。
在“文学人类学”之外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为数寥寥。其中,余宗其的《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地》(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一书是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的拓荒性的著作,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作者以中外文学作品为基本资源,以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对文学与法律的关系的做了全方位的阐述。
其中包括文学案件法理阐述学、文学法制人物评估学、文学法律文学鉴赏学、文学名著法学赏析学、作家法律立场类型学、文学法理学、文学民法学、文学经济法学、文学犯罪学、文学婚姻法学、中国当代文学法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的法律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对婚姻法实施的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定罪量刑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法律与权力、中国当代文学中法律与道德、西方文学对剥削阶级法律的批判等二十一章内容。全书以文学研究为表现形式,以法理阐述为具体内容,着意追求文学研究与法律研究的统一,实际上是以法律为切入点,对中外文学所做的法学解读。它不是文学与法学两个学科关系的原理性研究,而是运用跨学科的方法、超文学的方法所做的文学研究,因而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从这一点上看,《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地》一书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具有示范意义。
((第二节))外来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跨学科研究
1980年代后,外来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主要形式。
首先,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在外来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宗教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持久不衰的热点,而随着宗教研究的深入和文学研究的深入,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就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许多研究者将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80年代,公开发表的有关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文章就有约四百八十篇。其中,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是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作。进入90年代,在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现了若干有份量的学术专著。
较早出版的有关中外宗教与中外文学研究的专门著作是马焯荣的《中西宗教与文学》(长沙,岳麓书社1991),这是一部五十八万字的大作,是作者数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该书共分五编。第一编《宗教·文学·意识形态》,属于总论部分,第二编《自发宗教与文学》,第三编《人为宗教与文学》,第四编《宗教史与文学》,第五编《宗教文化与文学传统》。全书视野很开阔,纵向贯通古今,横向跨越中西,将中西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的许多重要问题都纳入了研究的范围。作者所指涉的宗教不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成体系的“人为宗教”,也包括了原始宗教、自然宗教。作者总结了宗教在中西文学中的表现,如图腾崇拜与中西文学、鬼灵崇拜与中西文学,儒道佛与基督教及其相关的文学等,并概括了中西宗教与文学的某些不同特征。
如,认为中国的宗教文学是“杂色宗教文学”,西方的宗教文学是“单色宗教文学”;认为中西宗教史的差异表现为中国宗教史上的三教合流和西方宗教史上的政教合一;中国宗教是从多神教到多神教,西方宗教是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等。作者在分析中西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注意揭示中西宗教与文学的联系性、共通性和差异性,在此过程中注重对与宗教与关的作家作品的进行具体的分析,从而有效避免了架空之论。总体上看,这是一部中西宗教与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概论性的著作,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基本理论及相关知识,是中西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有益的入门书和参考书。但由于涉及问题很多,有些地方的材料和观点不免流于一般化。
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研究及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颇具规模的重要领域。20世纪初以来,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不断涌现。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但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本土化,并产生了禅宗这样的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并不纯粹是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换言之,未必所有的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所以,笔者在这里不打算涉及所有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而是将重点置于跨越中国和印度两国文化的有关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孙昌武和谭桂林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
南开大学的孙昌武教授主攻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研究,出版了《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及论文集《诗与禅》(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等著作。其中,《佛教与中国文学》是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历史的、概括性描述的著作,描述的重点是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者在前言中强调,他不是把佛教单纯作为一种宗教来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认为虽然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的诸问题已被更多的人所重视,并已出现了不少成果,但对基本的历史情况尚缺乏全面的梳理,因此《中国文学与佛教》把全面系统的描述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历史关系作为自己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