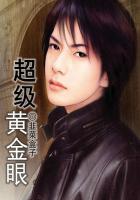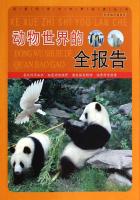曹志鹏无奈地把瓶子接过去,下了很大决心才接受喝酒这个“命令。”
酒辣辣地顺着喉咙滑下来,落在肚皮里。过一会,那种难掩的滋味慢慢萦绕到唇齿之间,陈那花的酒又是一种别样的味道。曹志鹏赶紧把瓶子递过去,抓起手中的红薯,急促地狠狠咬了一口。
“难喝吗?”
“……”曹志鹏嘴里鼓鼓的,他微微地摇摇头。
“慢慢吃。这是我拌的凉面,看看好不好吃。”陈那花把凉面递过来。曹志鹏赶紧接过来,手里红薯的手指夹着筷子,轻轻地拌着。
“村里为什么不修一条通到乡里去的公路呢?这样大家出门就方便了呀!”曹志鹏把红薯吞下去,问了一个他早就想问的问题。
“路?有啊!”陈那花漫不经心地说,她忙着拌自己手里那碗凉面。面条黄黄的,一些红汪汪的辣椒缠绕在其间。
“有路?有路怎么还需要爬山?”
“路又断了。”
陈那花挑了一筷子面条,递进嘴里,吸吸乎乎地将面条吸溜进嘴里。她似乎对曹志鹏问的这个问题毫无兴趣。
“断了?断了再修啊!你不知道,一条路的价值有多大。你看你们这里,山上成片的果树,山下还有一汪清澈的湖水。有了路,你们这里可以将果实卖到山外,也可以让城里的人来这里旅游。村里的男人们,也用不着都跑到外面去打工了。我觉得你们这里大有可为,道路一通,黄金滚滚流。”
“切,什么黄金滚滚流?我们不稀罕。”陈那花还是埋头吃着碗里的面条。
“我说这么多,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们这是云梦村,不是黄金村。我们不需要什么黄金滚滚流,这样悠然自在地生活着,有什么不好?外面,外面会让我们伤心的。”
陈那花从篮子里拿出两个鸡蛋。她在身旁的石头上碰了几下,手麻利地将蛋壳弄下来,递给曹志鹏,“来吃个鸡蛋。”
曹志鹏困惑不解地看着陈那花,手机械地接住了陈那花手里的鸡蛋,“这个世界,早就是金钱统治的世界了。确实有一种唯利是图的恶劣风气,那要看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控制力。也有控制得好的,既与外界保持着联络和沟通,又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相互相成,保持了一股活力。”
“我告诉你,我们村曾经富过。”陈那花拍了拍自己的手,抓起那个瓶子,凑到嘴边,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口。
“以前村里有一条很宽的公路,一直通到水城去。通到水城,也就能到阳城,到北京到上海去。但是后来一次山洪暴发,路被冲断了,我们也无心去修,大家觉得那样也好。路从云梦山下通过,你看,那边最高的山就是。山体滑下来以后,大家觉得那山有些神秘,而且山体也不稳,谁也不敢去触动那里。自从云梦山垮了以后,悄悄地流传着一种说法,能爬到云梦山顶的人,就是最勇敢的人。听村里的人说,这么多年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上去过。对于村里的人来说,心里总是蒙着一层胆怯的阴影,也觉得勇敢是没有用的东西,没有必要去尝试。
从乡里到这里,路断了以后,大家习惯了从这一边翻山到村里来。这一路上,路比较窄小崎岖,过去有一些零散的村寨,后来都搬迁到乡政府附近去了。所以,你来的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但也太远了,太不方便了。到一次乡里,要走四五个小时。我想到乡里去买点东西,想起那么长的路途,我先就打退堂鼓了。”
“实际上并不太远。你第一次来,一定被人骗了,带你走了冤枉路。”
“你们走,要多少时间?”
“走得快两小时,像我们这样走惯山路的,一个上午有个来回。走得慢的话,得三个小时,像你这样再绕绕路,中间休息一会,不就得四个小时吗?”
“看来真是被人骗了。你说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通路?”
“通路?通路既是好事,也有不好。通往外面的路修好以后,马上就有三四个人来村里办工厂了。一个在路边的山上开砂石厂,把山挖得空荡荡的,还成天弥漫着厌烦的粉尘。还有一个人来村里办橡胶厂,没到一年,村里那个湖里的水就臭得像猪圈。另有一个人说山里可以挖煤,招村里的男人去下井,没到两年,村里的男人死了十多个。男人们挺开心,赚了钱,赌博的赌博,到城里去找小姐的去找小姐。过去在我们身上生猛的那些男人,全都变得软软的。我们听人说可以吃药,买了药来,他们在我们面前不吃,跑到城里的那些卖的女人那里去吃。男人们一个个自以为有了一点钱,狂妄得很,而稍微触碰一下,才知道都是一些外强中干的废材。”
“钱是把双刃剑,能让大家赚到钱,改善生活,但会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好和坏同时存在,究竟弊多还是利多,难以说清楚。”曹志鹏叹了一口气,抓起瓶子来又喝了一口酒。酒的味道香香的,有一股月季花的味道。
“除了办工厂破坏环境以外,还有很多让村里人气愤的事。乡里的干部三天两头来村里,吃吃喝喝不说,还干一些坏事。他们来村里推广烟叶种植,强迫我们把地里长得不错的其他作物全都铲掉来种烟叶。烟叶种出来,却没地方收,听说跟乡里联合种烟的人跑了。烟叶既不能吃,又不能喝,让大家伤透了心。”
“政府的建设作用和破坏作用同样大。”
“还有,村里办工厂用环境换的经济,大部分落到原来那个村长白景明的手里,他到水城到阳城去买房买车,做生意。平常很难看见他的面,即使坐着车来,也呆不了多久,但村里的一切他都控制着。听说这个人前不久得了胃癌死了,也算报应。”
“经济的发展,不能给村里的人带来好处,便宜了少部分贪腐的人,这肯定会严重伤害村人的心。”
“受伤害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些女人,他们把我们女人当什么呀!玩物?妓女?想怎样就怎样,我们谈不上尊严。我们女人不干了,就联合起来,准备把那些人赶走。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家伙,哪里赶得走。他们从外面招来一帮年轻小伙子,碰到我们去表达意见,他们就戴上面具,挥着棍子朝我们猛砸。我们这些女人在那场战斗中,损失惨重。就算这样,我们这些女人还是不屈不挠地坚持了下去。”
“看不出来,云梦村的女人革命精神更足。这也就是女人们更愿意留在这里,承担革命后果的原因吗?”
“不对,这是云梦村女人们对无止境的欲望更有控制力的原因。”
“说得很好。欲望实际上是一个中性词语。无欲,人没有动力。欲望过强,破坏力太大。如果保持一种合适的欲望,这才是关键。
“我们这些女人的行为惊动了乡政府,乡里的蔡乡长来到村里,坐了几个星期,希望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对这个蔡乡长,从心里是看不起的,她说的话谁都不会听。”
“为什么会这样?蔡乡长不是挺好的吗?长得漂亮,又是你们村的人。”
“她呀!她就是靠身体作为资本,通过要挟等手段,离开云梦村,当上一个芝麻官的。她跟我们不是一路人。这样的女人,我们瞧不起!”
“瞧不起?瞧不起一心往上爬的女人?你们的观念还很意思嘛!”
“我们觉得,如果喜欢,不在乎是跟谁玩。但是,靠着那种事,去极力去谋求利益,却是让我们羞耻的。这就是良家妇女和****的区别。那是一种交易,而交易就会带来肮脏,你说怎么会一样?”
“呵呵!后来怎么样?”
“男人们极不支持我们的行动,乡里也极力压制我们的言论,那些老板更出格,想出不少下流招数来围堵我们。大概闹了将近半年,双方都有些疲累了,事情也僵持着,我们都想出去打工了,离开云梦村。没想到,那年夏天,一连下了十来天的暴雨,雨很大,那个在云梦山脚下,公路旁边的砂石厂突然就垮了,半座山垮塌下来,完全掩卖了那条公路。公路断了,没有人愿意修,再加上这帮女人的反对,那几个厂卷铺盖走了。这个村子,繁茂的树木掩盖了过去那些工厂的痕迹,慢慢恢复成现在的样子。你现在看到的美丽,是靠这十多年大自然慢慢修复的结果。能修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我们女人愿意过这样的生活,而男人们耐不住寂寞,纷纷走出去,到外面打工去了。”
“就留下孤独的你们!”
“孤独?为什么说我们孤独?我们有我们的乐趣。我们很乐观,并不觉得有多苦。”
“村长带给你们的?”曹志鹏嘻嘻地笑起来。
“村长?”陈那花的脸一凝,直起腰,冲着曹志鹏打了一耳光。这一耳光有些突然,根本来不及躲闪。但是,耳光落到脸上,疼痛的感觉并不明显,像一只手掌摸着他的脸。“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吗?跟谁做什么不重要,而在于我们是否开心。”
“我听说,在村子里,村长就是皇帝,你们全都是他的嫔妃。”
“放屁。”陈那花说了一句脏话。不过她很快意识到了,她笑了一下,手撑到后面的草地上,身子斜着,头往上仰,“还是跟你说一个笑话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