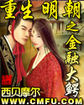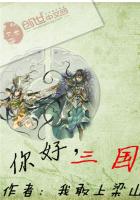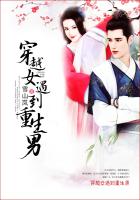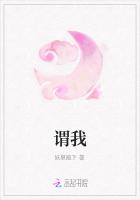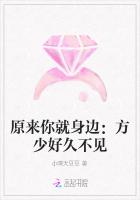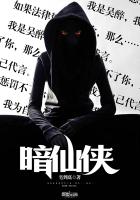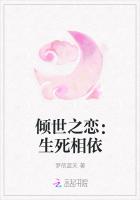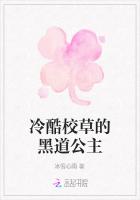据1993年版《宁海县志》记载:“宁海县始建于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县治设白峤。”
然而,这个建于西晋太康元年(280)的县治白峤到底在何处却始终无法求证。一般,人们认为如今宁海城关县城东就在白峤岭的“上白峤”、“下白峤”,这两个小山村便是古县治所在。
但是,稍一琢磨便不难发现,根据现在的白峤村的地理位置、人口分布、交通状况以及历史遗迹等等判断,这里并不像是曾经建制309年的宁海古县治白峤。
据《嘉定赤城志》记载:“武帝太康元年,析临海郡之北置宁海县,旧志云,治白峤。”
《晋书·地理志》又有载:“临海郡统县八: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
这段文字就讲述了晋朝时期的宁海归属于临海郡。当时的临海郡就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大致上管辖着现在的台州、丽水、温州等地的各个县城。而在当时建制的宁海县则是从临海郡和会稽郡各割出一块土地组成。那时的宁海县大致上囊括了如今的“宁海”、“象山”、“三门”、“天台部分地区”、“临海部分地区”等地域。因此,古宁海是属于比较大的县城了。
此外,迄今为止,在“上白峤”、“下白峤”二村尚没有任何考古发掘,也没有出土一些古建筑和碑刻遗存等考古学上的实物证据用以证明该处曾设过县城。
这么多年来,学界基本上停留在县治的名称传承上,没有进行深入的史学考证和考古发掘研究。
一个存在了309年的县城,为什么就这样湮没无闻了?
宁海西晋开县时的县城到底在哪里?现白峤是不是就是原来的古县城呢?
既然要考究宁海古县治位于何处,那就不得不先从宁海县的存废变迁史来着手了。
光绪《宁海县志·地理志卷一》中有一段引录自《三国·吴志》的话:
“太平三年析章安置临海县。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领县六,治章安。”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三国时期,宁海尚属于吴国临海郡的章安县。直至西晋太康元年(280),宁海才设县治。这在《嘉定赤城志》中可找到记载:
“武帝太康元年,析临海郡之北置宁海县,旧志云,治白峤。”
《晋书·地理志》载:“临海郡统县八: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
上述材料表达的意思为:武帝太康元年(280),在临海郡的北边置县城宁海,县治在白峤;临海郡统辖八大县,其中亦包含了宁海。
而在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中,有一段引自《晋书》的文字也印证了西晋时对宁海的记载:
“(太康元年)六月,东夷十国内附。是岁,以司隶所统郡置司州。凡有州十九,郡国一百七十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诏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史百人,小郡五十。”
吴地的临海郡,是一百七十三个郡之一,宁海则是该郡管辖的八个县之一。照此来看,宁海应是太康元年(280)始建,且隶属于临海郡。
但据《太平寰宇记》引《临海记》载:“晋永和三年,分会稽郡八百户于临海郡章安地立宁海县。”
这似乎否定了太康元年(280)建县之说,提出了宁海建县时间在东晋永和年间。而晋永和三年(347)比《晋书》所记载的太康元年(280)足足晚了67年。
另据《嘉定赤城志》注引《宁海土风志》载:“宁海县本汉回浦、鄞二县,太元二年,裂鄞之八百户,安北乡二百户置宁海县。”
这里所载的太元二年(377)更是将宁海置县的时间延后了97年。
这三则记载在宁海建县的时间上有着相违的叙述,使得宁海的建县笼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相对而言,西晋建制的说法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此后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四朝,宁海县建制都延续如旧,一直没有变化。
直到隋朝时期,宁海被废。
《嘉定赤城志》载:“隋开皇九年平陈,废宁海,复入临海。”
《中外历史年表》载:“正月,隋师入建康,俘陈后主,陈亡。二月,隋置乡正、里长治民。岭南冼夫人经陈后主劝始降,于是陈之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皆入于隋。”
也就是说,“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废会稽郡,改东扬州为吴州,治所在会稽县(今绍兴市),并鄮、鄞、余姚三县入句章县,县治迁小溪(今鄞县鄞江镇)。废宁海县,分其地归句章和临海。”即隋开皇九年(589),隋高祖文帝杨坚攻入陈国首都建康,俘虏了陈后主陈叔宝,陈国宣告灭亡。隋朝建立后,杨坚对原陈国地域划分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宁海县,归入临海县。这就是宁海在历史记载中首次被废的因由。
从宁海始建(以《晋书》)到被废除的这309年里,史料中并未出现县治迁徙的记载,那么县治应当一直都是设立在“白峤”。然而,这个存在了309年的古县城,如今又到底何在呢?
宁海自隋朝撤县以后,其间32年未曾复县。直至隋末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618)。是年,梁萧铣称帝;唐高祖李渊也在同年称帝,号武德。
武德四年(621),李渊部将李靖包围江陵,萧铣投降;唐将杜伏威活捉了控制浙江的割据者李子通,押往长安,于是安徽、江浙一带都归入唐版图。
《唐书·地理志》载:“武德四年,析临海置宁海县,治海游。”
《宁海旧县志》载:“武德四年,杜伏威擒李子通,献其地复置宁海县。”
但是这次的复县将县治改设在海游(有学者认为此海游即现三门县海游镇),其中有什么因由呢?对此,学者提出一说,即是“白峤”的位置已佚。而更多的人则以为:作为县治存在了309年的“白峤”古县城,其规模与繁荣程度必定不一般,却在废县后的短短三十几年间荒废到无人问津的程度,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为何复县不再以白峤为治呢?这已成了谜。
这次复县仅仅维持了3年,其后宁海又撤归章安县。据《太平寰宇记》载:“唐高祖七年省宁海入章安。”唐太宗李世民时,宁海仍无县治。这段时间又中断了65年。因此可以说自隋到唐,宁海设县中断了将近百年,中间只恢复过3年。在这近百年间,“治白峤”已经开始湮没无闻。
宁海再度复县,是在唐武则天时期。
《旧县志》载:“武后永昌元年,复置县。县治广度里。即今县治也。”从此,宁海县至今存续了1320年,县治又改成了广度里。后来,又分出了象山县。
《唐书·地理志》载:“唐中宗神龙元年,以县东地海岛辽阔,析为象山县。”
《嘉定赤城志》与《太平寰宇志》则记载为神龙二年(706)析。
乾隆《象山县志·地理志·沿革》载:“唐中宗神龙二年丙午,御史翟皎请以象山名县,以地有山,宛如象形也。于晋为宁海县地。”因此可推断象山建县至今已1300余年。
明崇祯《宁海县志·舆地志》载:“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王浚以兵徇地,请析临海之北二百户、鄞地八百户置宁海县,治白峤。”因此,这个“徇地”并“请”独立建宁海县的人,就是打下建康、灭了东吴的大将,即“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赫赫有名的益州(四川成都)刺史王浚。他有没有到过宁海,目前史料中还未发现有记载,但作为一个提出区域划分议案的官员,他应该是到过宁海实地考察的。
清光绪《宁海县志·建置志·城池》载:“宁海置县以来,城凡三徙。始建于白峤,再徙于海游,三徙于广度里,即今地。白峤、海游旧制不可考。”
清《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载:“晋太康初,析宁海县,属临海郡。宋以后因之。隋省入临海县。唐武德四年,复置属台州。七年省。永昌元年,复置。”
元延祐《四明志·城邑考》(袁桷,1266—1327)载:“(宁海)县旧治海游镇,永昌初徙今治,筑城周不及二里,寻废。”
《读史方舆纪要》载:“嘉靖三十一年,以倭患筑城。万历十九年,以淫雨城圮,复修筑,周六里有奇,编户百十三里。”
明崇祯《宁海县志》载:“(宁海)县治广度里,晋初设白峤,唐徙海游悬渚。”
上述材料将宁海县的三废三设说得一清二楚,但关于旧县治“白峤”与“海游”没有详细记载,仅存有其地名。而自宁海县治设为广度里后,筑县城,周围600步,建城隍庙(址在今桃源南路)。唐神龙二年(706)以县东地域辽阔,析归新建之象山县。
到清朝修志时,甚至直接记载为“白峤、海游旧制不可考”。“白峤”与“海游”似乎就此退出了宁海的历史舞台。清朝修县志,距“白峤”始置县已经过去了1600多年,其间除了统计赋税时,对清朝时的白峤村有田地地名的记载外,再无其他涉及古县城的记载。
根据光绪《宁海县志·乡庄》中记载:“白峤庄,距城七里,其田二石起亩,无水利,居第三等。计积里二十六,民田八,涂田十四,地四。且有山海之利。赋居第四等。村十五,白峤,港头,蒲澳,薛坡,应家庄,上盘屿……”从这段不难看出,对人口、土地、海涂的情况记录,都无不显示当时的白峤只是一个小地方,同现在的白峤村相差无几。这并不像是一个1600多年前就置县的地方。
从相关资料中能看出,西晋时设县的县治白峤,作为一个历时309年,起始一千户人口的县城,经历了中国人口四次大南迁中的三次,即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五胡乱华”和唐朝“安史之乱”。宁海接纳了大量避难的北方人口,人口迅速增加。一直到中唐武则天时恢复建县。人口的迁徙会不会是影响宁海县治改设的原因之一呢?
1730年前的宁海“白峤山”是哪一座,是不是就是现在的白峤村边的200多米高的白峤山?1400多年后的明、清的《宁海县志》记载是对的吗?现在的白峤山、白峤岭得名始于什么年代?因什么原因得名?是不是晋朝时此山就叫这个名?
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无法从史实材料中得到解答,不妨从地方传说上去寻求突破口。人类社会在有文字记载以前,依靠传说、神话记述历史,留下一些不连贯的历史信号。值得重视的是,现在许多神话传说已经有了考古发掘的实物可以印证。宁海始建县于道教盛行的西晋,地理位置偏僻而山川秀美,其地名的起源一直与神仙传说有关。考据地名,往往从《水经注》、《山海经》、《列子》、《拾遗记》中去寻找一些历史的碎片。宁海的地名“丹邱”“白峤”“尾闾”“回浦”“桃源”“天台”“瀛台”“桐柏”“真逸”,莫不带有道教文化的“仙气”。从这些带有道教色彩的地名中,可以探索出一些被历史掩埋的真相。在宁海的地名中,最有价值的能够探究古县城在哪里的,是“白峤”和“尾闾”这两个地名。
峤,无论是在古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是一个特指名词,没有歧义,是指神话传说中五座仙山之一的“员峤”。这为探寻古县城提供了一条捷径,“白峤”就变得有迹可循了。
员峤和尾闾在古代神话中是并提并存的。
《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
杨伯峻集释:“《释文》云:峤,山锐而高也。”这里所说的渤海,不是指现在山东的渤海湾,而是指现之东海,因为有史料明确指称“尾闾”“归墟”在东海,而五座仙山同尾闾是在一起的。按照这个神话传说,五座仙山是在激流汹涌的无底之谷,大海之中,山山相隔又很远,有七万里。仙山的顶上有九千里的平原。其上住有仙人,长满奇花异草与珍禽走兽。
员峤原是海上的仙山,即是海岛。那么它又是怎么跑到宁海的岸上的呢?《列子·汤问》中又有一个更神奇的传说:“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沈……仙圣之播迁者巨亿计。帝凭怒,侵减龙伯之国使厄。”
本来玉帝怕仙山漂移不定,于是就派了十五只大鳌背着它们,结果让龙伯国的巨人钓走了六只,用于灼骨占卜计数。员峤山没有了依靠,漂到了北极,沉入了大海,仙人都没有地方住了,只好搬迁。玉帝大怒,于是惩罚了龙伯国人。由于晋时道教盛行,宁海此时建县,境内又人迹罕至,山川秀丽,宜居宜隐,宁海的一些险峻高山就附会荣膺了这些传说中带有仙气的地名。应当是能够基本符合这种传说条件的山,才会被叫作“员峤”仙山。大多仙山都是缥缈无处寻的,也许这也是“白峤”今不可考的原因之一。
那么,“尾闾”又如何呢?“尾闾”在古神话中又称“归墟”,是万壑归宗的大海中的大漩涡、无底洞。同样典出《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
《庄子·秋水》也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
成玄英疏:“尾闾者,泄海水之所也。”
李善注引司马彪曰:“尾闾,水之从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东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称尾。闾者,聚也,水聚族之外,故称闾也。”
与员峤山不同的是,“尾闾”在宁海有准确地点可考。经一些老渔民介绍,在三门湾外五屿门海域确有叫尾闾的地方。历代县志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尾闾,在东海中。与海门马筋相值,其水湍急,陷为大涡者十余,舟楫不敢近。世传东海泄水处。宋主簿常具公事至海门,登山纵观大海,亲见其势,皓之迈载入《夷坚志》。”此处的“登山”指的是登上宁海白峤山,即在白峤山上能俯瞰大海,亲见尾闾,这与神话中的仙山之说也相符。
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尾闾具有更大的知名度,更广的地域范围。一种说法是“尾闾”是百山之尾,是大海中的火山喷发形成的海礁。
《庄子·秋水》成玄英疏引《山海经》(今本无):“羿射九日,落为沃焦。”太阳射下来成了海中礁石。这显然是古人对海底火山喷发形成岩礁的一种观察记载。神话史研究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说字典》里,对“沃燋”的注释为:山名,亦名“尾闾”。
吴任臣《山海经广注》辑《山海经佚文》:“沃焦在碧海之东,有石阔十万里,居百川之下,故又名尾闾。”因此有网友说沃焦是太平洋中的夏威夷,中国人的祖先早就到过美洲。
显然,宁海三门湾中的“尾闾”,也就是宁海西晋建县时,海上先民见到的五屿门暗礁区海流中巨大的激流漩涡,而附会神话传说而起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