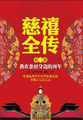古往今来,乱世出贤臣,盛世出奸佞,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唐玄宗开始陶醉于自己的伟大功绩中,犯了很多帝王都容易犯的错误:亲小人,远贤臣。自唐玄宗宠信李林甫的第一天起,即宣告着盛唐不再,明君不复!
开元初期,由于政局不明,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唐玄宗日理万机,时常通宵达旦处理政事。唐玄宗处理政事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今日事今日毕,哪怕是在就寝后突然想到了好的治国点子,他也会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绝不会拖到明天处理。那时的唐玄宗,真是事必躬亲,累得像只不停歇的驴一样,但甘之如饴。而在唐玄宗的身边,则围绕了一大批贤相名士,他们给唐玄宗出治国安邦的主意,提施政富国的意见,唐玄宗都欣然接受。唐玄宗给予这些国之栋梁极高的特权,如果有要事请奏,侍卫们不得阻拦,否则将会受到严厉处罚。在明君贤士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篇章。那时的贤臣对于唐玄宗而言,是左膀右臂,理所当然得到唐玄宗的极大尊重与礼遇。然而到了开元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兴盛,百姓安居,社会稳定,唐玄宗与忠臣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千古一相姚崇因下属过错,被逼辞去宰相职务,继任者宋璟因过于耿直,屡遭贬职。究其原因,不过是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编织的神话,飘飘然不知所以,渐渐听不得众大臣的谏言、诤言,反而更希望从众大臣的口中听到颂扬。而那些直言敢谏、一心为国的忠臣,认为阿谀奉承非君子所为,所以当善于谄媚逢迎、溜须拍马的李林甫走进唐玄宗的生活中,并获得唐玄宗的赏识时,他们很快便败下阵来,毫无还手能力。
李林甫是开国皇帝李渊兄弟平肃王李叔良的曾孙,也算是宗族子弟,可惜到了李林甫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落了。李林甫从小不学无术,不务正业,但因为嘴甜,会说些恭维奉承的话,讨得舅舅姜皎的欢心。正是凭着这一技之长,李林甫得以一路爬升至宰相之职,荣宠19年不衰,此是后话,按下不表。当时,当朝宰相源乾曜与姜皎联姻,李林甫便利用舅舅的姻亲关系,从源乾曜那里谋得一份国子监的差事,主要负责监察管理皇子们的学业工作。这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实权。李林甫自然不甘心管理一群学生,便利用职务之便,结识了御史中丞宇文融,后经过宇文融引荐,拜御史中丞,正式进入朝廷权力中心。随后,李林甫继续钻营,官至礼部尚书,真的入阁拜相了。
当时宰相有三人,其一便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大学者张九龄,而侍中裴耀卿也是朝廷重臣,只有李林甫资历尚浅,又不善理政,只会溜须拍马这一个本事,因此对张、裴二人很是嫉妒。尤其当他得知唐玄宗在准备任命自己为宰相时,张九龄曾出言劝阻,更是对张九龄怀恨在心。但当时张、裴二人朝中势力稳固,且为唐玄宗所倚重,于是,李林甫便躲在暗处寻找合适的时机,欲将张、裴二人一并除掉。
为了实现自己独掌大权的政治野心,李林甫千方百计地揣摩唐玄宗的心思。精于钻营的李林甫深知他们这些官员的荣辱全系在皇帝一个人身上,皇帝若宠信谁,那这个人便可扶摇直上;皇帝若厌恶谁,那这个人的好日子怕也就到头了。那时唐玄宗在位已久,怠于政事。每逢商议政事,张、裴两人事无巨细都与皇上据理力争,狡猾的李林甫则利用各种机会,挑拨离间,制造唐玄宗与张九龄之间的君臣不和。
是时,武惠妃构陷太子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唐玄宗恼怒之下欲废除三人爵位,张九龄直言劝谏。于是,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说:“皇子们的废立本是皇帝自己家的事,哪里轮得到我们这些臣子们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话里话外直指张九龄管得太宽了,这是皇帝放纵的结果。当然,这些话最终如李林甫所愿传到了唐玄宗耳朵里,虽然唐玄宗最终听从了张九龄的谏言,但内心里已经对张九龄心生不满,而对“体恤”自己的李林甫心生好感。
736年,唐玄宗巡游东都洛阳后,欲返回京师长安,唐玄宗召集百官意见。裴耀卿认为时值三秋农忙时节,皇上返驾,必将加重沿途官员百姓接待的负担,延误农时,因此提议秋收后再返京师。张九龄等众官员附议。李林甫当面不表态,待百官离开后,方表明自己的看法:“长安、洛阳就像是皇家的东宫和西宫,皇上御驾往来,难道还要等待什么时机吗?”这话真真切切说到唐玄宗的心里,于是不顾张九龄等人的反对,匆匆回了长安。经此一事,唐玄宗更加亲近李林甫了。
真正使唐玄宗与张九龄君臣心生嫌隙的,是唐玄宗打算提拔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对于唐玄宗这一决定,张九龄公开表示反对,认为牛仙客论学识、论功绩还不足以担任尚书一职。李林甫故伎重施,当面不表态,私底下却对唐玄宗说:皇上任人唯贤,只要有真本事,即使肚子里没有墨水又何妨?再说牛仙客是块当宰相的料,做个尚书算什么,张九龄根本就是书生之见,不懂得皇上爱惜人才的用意。这一番言论下来,更加坚定了唐玄宗任命牛仙客为尚书的决定。通过此事,唐玄宗认为李林甫并不专权,有荐贤之风,张九龄却有拒贤固位的嫌疑,开始疏远张九龄。
自开元中期以来,唐玄宗就对朝臣们结党讳莫如深,一经发现朝中有结党之事,就毫不手软地将当事人罢免。而当朝两大宰相张九龄与裴耀卿经常同气连枝,他们联合百官力谏唐玄宗的一些不合理行为,让唐玄宗感到权力受到极大的制约,因而对二人大为恼火。于是,善于察言观色的李林甫便借机制造事端。李林甫曾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不学无术,遭到张九龄和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弹劾,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心生怨恨,暗中授意其爪牙寻找他们言行不当之举,欲加陷害。李林甫的爪牙打探到严挺之前妻的现任丈夫王元琰贪赃犯法下狱,严挺之正在设法营救。李林甫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除掉严挺之的机会,便使人奏告唐玄宗,建议将严挺之连坐。张九龄不忍朝廷因此而丧失一位难得的人才,所以极力为严挺之辩解,并转托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便诬陷张九龄与裴耀卿有“阿党”行为,此举正好顺了唐玄宗的心意,于是趁机将张、裴两人罢知政事,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就这样,唐玄宗被老谋深算的李林甫玩弄于股掌之中,忠奸不分,开始亲小人远贤臣,亲手为自己制造了凄凉可悲的晚景。
为了独揽大权,方便自己为所欲为,李林甫竟然取消了唐玄宗开元初期制定的谏官议政制度,堵塞了唐玄宗了解下情的渠道。李林甫曾把朝廷所有的谏官召集到一起,暗中威胁道:“当今皇上是多么贤明睿智,我们领会圣意还常常来不及,还需要什么谏论?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用于仪仗队列的骏马?往往那些终日不作声的马匹就会吃到上等粮草,而只要有一声嘶鸣,就会立即废弃不用。以后虽然再不作声,还能重新入选吗?”李林甫明目张胆地威胁谏臣缄口,企图在朝中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一个叫杜琎的谏官偏不理睬,坚持上书言政。李林甫为了杀一儆百,当即将其贬为地方县令。自此之后,满朝文武只李林甫一家之言。
李林甫对贤能之士加以诬陷、排挤与打压,却把一些无才亦无德的人引为同僚,宰相陈希烈、户部郎中吉温、节度使安禄山都曾受到李林甫的引荐,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因而官路亨通。然而这些人反复无常,政治站位上如墙头草一般摇摆不定,缺乏足够的忠诚,待李林甫年老力单之际,纷纷倒戈唐玄宗的新晋宠臣杨国忠。750年,杨国忠状告李林甫与御史大夫王有结党嫌疑,唐玄宗一生最恨大臣结党,当初李林甫正是抓住了唐玄宗这一心理,捏造张九龄结党使其被贬谪,这是李林甫政治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没想到自己最终也栽在捏造的“阿党”问题上。然而李林甫为官之时树敌过多,待到他蒙难之时,曾经受过李林甫刁难的朝廷官员无不落井下石,根本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说话。直到此刻,李林甫方才深刻体会到被诬陷有苦难言的滋味。752年,李林甫愤懑忧郁而终,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