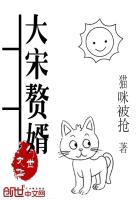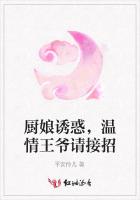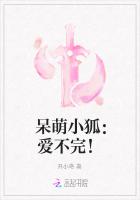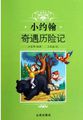陈征平
1915年由云南首义的护国运动,在中华民国建国史上可以说起着拨乱反正的关键作用。因为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并创立的共和制国体,正面临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帝制复辟者的颠覆,尽管此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已经察觉,并曾发起过二次革命,但由于时机尚未成熟,缺乏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以至惨遭失败。但到1915年,其情况已大不相同,首先袁政府为获得帝国主义支持,与日本签订的试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已激起国人的极大愤慨;与此同时“筹安会”的设立并运作,则成为直接的导火索。从而,当蔡锷、唐继尧等领导云南护国军提出倒袁护国时,短短几个月便一呼百应,对时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大致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云南护国
首义,使袁世凯称帝的合法性遭遇挑战。此前当袁世凯积极筹备称帝时,尽管时人亦有异议,但在帝制派的打压下,尤其有“二次革命”的前车之鉴,使初期各派别及地方势力也只能表面上进行附和。以至当蔡锷等起兵后,曾有人言:“云南漾电唐继尧等劝袁世凯取消帝制并限答复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页)。到京之前三日,唐继尧尚有一电到京,与漾电词旨极端相反,政事堂通电所谓事隔三日,背驰千里。”《申报》1915年12月31日。与此同时,袁世凯等帝制派亦大耍两面手法,如通过成立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组织“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解决国体问题,并指挥各省“代表”就地投票以体现“民意”等做法,)参看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来骗取人们对帝制合法性的认同。然云南护国运动的发起,则使其皇帝迷梦惊醒,也使袁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如报载:“云南广西反对帝制勃发消息,或其电报为政府方面勒,或系叛军止其电报,致无从得消息之法。据外国人方面本日接到广东电报,谓广东目下犹无如斯形势,惟反对之气势已十分澎湃。”《申报》1915年12月23日。可见,尽管当时信息沟通存在阻滞,护国起义的消息尚不确切,但广东地区的民众已经开始呼应。
第二,义旗
义旗所指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周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及不同地区的起义运动,对袁政府造成重大威胁。北京政府对云南护国军起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欲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即乘“南方不稳之防备,决定急派守备北京之第十师第三十九团及第四十九团南下”。《申报》1915年12月23日。而此时,云南组成的护国军由蔡锷率领,总共3130人,分三梯队,向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出兵,出发时所带饷糈,不够两个月的伙食津贴之用。“假使不得他省的响应,护国军的前途,甚不可知。”(参看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但在北军于四川对云南护国军进行围堵的过程中,由于周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各地起义运动频发,1916年1月24日贵州宣告独立;3月中旬广西宣告独立;4月7日广东宣告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告独立;之后是四川、陕西等宣告独立,以及肇和军舰、山东民军、江阴吴江、福建护国军等起义运动以及海外华人的支援,如:
(1)云南在护国运动之初,即有致华侨两电,一是“述起义之理由”;二是“乞协助军费”。(《申报》1916年1月20日)
(2)“李烈钧从海外带来数十万元,是华侨张木欣(云南腾越人)慨然借助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03页)
(3)据各国公使通过本国调查:“留日美两国华侨者大概相同一致主张,推翻帝制还复共和。”“留法国华侨者颇有种种反对帝制之议论,惟尚无若何确定。”(《申报》1916年1月20日)
(4)孙中山亦“特派冯君自由前来南洋、澳洲等处,宣布国内进行情形,筹集巨款”。(《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5页。)使云南护国军的声势迅速壮大。有如研究所指出:“护国军本身的力量虽然不强大,但既然举起讨袁的旗帜,配合上全国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对袁世凯便成为重大的威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第三,护国运动
随护国运动声势不断扩大,各国出于自身利益,使袁对外借款受阻,袁政府亦失去外国势力的支持。研究认为,1913年孙中山所领导反袁之“癸丑赣宁之役,袁氏所以战胜民党的,全在帝国主义的大借款”。(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而此时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改变,欧战发生,英国等帝国主义对中国无暇顾及,加之对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亦有疑虑,因而害怕由帝制问题导致政局不稳而使原有利益格局重组。据报道,在护国运动发生后,其时北京政府与美俄日英几项借款之商议即受阻滞,认为该“各端均为外交上最重要之事宜,恐在二三个月内尚未易完全解决”。《申报》1916年1月18日。而欧战后对华势力执牛耳者之日本,对袁及反对派的态度亦视双方力量之消长,当看到反对派力量逐步壮大,便开始与云南方面联络,消息传出曾受袁之责问:“日本政府秘密派员到滇是何用意?”与此同时,又“曾有某某两公使亲赴外交部与陆国务卿会晤,为口头之谈判,曾质问中央政府究能以若干时日平定西南各处之乱事,以维各国之商业”。《申报》1916年2月14日。而在护国运动初期,云南曾对各国发出通告,其大意为:“独立军维持共和之宗旨,并恳请各友邦对于南北战争严守中立。”对护国运动之前“中国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协议契约等条件均承认有效。独立军管辖以内之外国人生命财产完全保障。在帝制问题发生以后中央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协议契约等件均不承认。独立军发见以战时禁制品输送于中央政府者,直行没收之。凡有援助中央政府之外国官吏及商人等,独立军均视为极端反对之人”。《申报》1916年1月28日。加之起义后革命声势不断壮大,这必然对驻华外国势力的动向产生影响,基于如此之国际国内背景,1915年至1916年之交,各在华国家均对帝制予以反对并对袁政府发出多次警告,参看《申报》1916年3月26日。“袁氏卖国的外交于是全然失败,帝制的成功遂以无望”。(参看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0页。)
第四,逼迫袁政府
逼迫袁政府步步退却,帝制丑剧终被制止。处心积虑称帝的袁世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帝制念头的,因为它代表着受中国两千多年皇朝思想浸润、并能获有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保守势力的政治主张。因而在护国运动发生之初,如前所述,当即考虑的是如何将其剿灭在事态扩大之前。而面对反对声浪逐渐扩大,才不得已于1916年2月提出了“帝制延期”,参看《申报》1916年2月12日。即称帝时间往后推,但实行帝制依然是早晚之事。其后由于形势进一步紧逼,3月初才有“取消帝制”之说,即商议“取消年号及恢复共和”,但“究能见诸实行与否尚难预料”。参看《申报》1916年3月8日、9日。以至外电亦将“筹备总统问题”之明令称为“官样文章之敷衍”。《申报》1916年3月27日。护国军显然并未被蒙骗,仍在激战之中,不得已3月26日即有“发表帝制取消问题纪详”。但此时“帝制取消于南方时局(已)毫无显著之效力。闻黎段徐联名电告南方领袖,以帝制已撤销,南方所要求之一重要条件已经遵办,双方宜暂停干戈,以待和平解决”。《申报》1916年3月30日。其时评曰:至此,“以军略言,中央已成反攻为守之势;以政治言,中央即无统治全国能力之可言。”《申报》1916年4月18日。但南方反对派认为:仅帝制取消不行,必须恢复约法,且袁世凯下台。由此在4月由“中央对退位问题之踌躇”《申报》1916年4月2日。演化为“各方面对于逼迫总统从速宣布退位情形较数日间益为剧烈,有刻不容缓之势”,《申报》1916年4月19日。进而只有提出“退位与改组内阁”。但仍只是“在观望时局之中,于事实上丝毫无所表现”。《申报》1916年4月24日。而此时护国军的战果亦不断扩大,迫于时局,袁于5月初提出“顾念危局,承认退职”,《申报》1916年5月5日。但其间又“忽起忽落”,“不知确否”。《申报》1916年5月23日。中经“南京会议”调和而未成,《申报》1916年5月18日。直至6月初袁因气急毙命才不光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护国运动则义旗所指,使事件结果亦成为“正义终究战胜邪恶”的又一典型范例。
综上可以看出,云南首义的护国运动,对当时政局的变化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从地域上,起于西南滇黔两省,波及范围则从西南向周边省份扩散而达于全国;在政治上,则不仅影响了本国政权之变更,甚至影响到各国在华势力的政策调整;在结果上,则达成了运动发起之初衷。不仅如此,该运动本身还内涵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首先,进一步检验并深化了国民对共和制的选择与认同。近代以降,面对西方列强的政治与经济入侵,知识分子与社会精英们亦长期图谋富国强兵之路,并认为国体改革乃强国之先机。如载:“自外力内侵,清廷穷蹙,国人激于时事,急图改良,于是革命、立宪、君主、民主各党竞出,而谋国之心则一。”(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1984年版(内部发行),第271页。)而辛亥革命成功,显然是激进主义道路走向成功的标志,但究竟是走激进还是渐进的路子更好,“反思进化论的学者有些是坚决赞成改良而反对革命的,回顾这一段历史,可能更赞成梁启超的主张”。(吴丕著:《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然政治家的过人之处,或许就是能洞察时局,顺应民心。如被认为与梁启超同为立宪派之蔡锷,在辛亥革命之后即指出:“近政体确定,全国思想皆将冶为一炉,即平日政见稍殊,果系杰出人才,皆宜引为我用。现值肇造之初,万端待理,只宜唯贤上是任,不可过存党见,使有弃才,益自树敌。”(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1984年版(内部发行),第271页。)并于1915年毅然领导了拥护共和的护国运动。这同时也反映出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即在国体确立之后,依然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又由于“自癸丑赶走革命党以后,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官吏的削刮,北洋驻防军队的野蛮,比以前的革命党还厉害;当时国内的报纸虽然不敢揭载,但是事实是不能掩盖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因此至1915年之民意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载:“民国二年之二次革命,晋人初无赞同之意,而此次自滇黔发难,人心因之大移观念,已绝对不同。”(《申报》1916年4月17日。)又有:“议院政治复现,则现居官位亦难久保,故皆大为忧闷。惟商民方面,则以帝制取消,理所宜然,息事宁人,莫善于此。并以已死之中华民国今复重生,吾民仍不失为主人翁虚名,欢欣之情溢于言表,商学界皆奔走相告。且有人刊发传单通告,商民店铺所有簿据经官厅压迫书写洪宪纪元,不过旬日,顷已纷纷改书中华民国五年之红签覆贴于上。”《申报》1916年3月31日。而在叙府失陷后,受伤的护国军士则对北军言:“我们是不愿做一家一姓的奴才,自愿来打倒袁皇帝,将来做一个民主自由的人民,虽死也是心甘情愿。”(《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一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3页。)据此可以看出,时值1915年,不管是出于经验抑或信仰,共和思想已是广为百姓所接受,而护国运动则顺应了人们对共和国体的选择与认同。
其次,护国运动是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之延续,证明了孙中山此前倡导反袁的历史正确性。“二次革命”发生于民国二年,民元“袁世凯在京就任临时总统后,极力排斥革命党人,当张振武方维枪毙之后,党人即蠢蠢思动,认政府之杀非其道,杀非其时,杀非其地。后以各方布置未周,其事遂寝。然此后南方各省愈与袁政府相水火矣。二年七月,遂有二次革命之役”。(贾毅君著:《中华民国政治史》卷上,上海书店(据文化学社1932年版影印),第7页。)
而另有人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宋(教仁)案真相暴露”,孙中山亦“由日返沪,认定新中国建设的重任决不可托诸袁,而倒袁又决非法律口舌所能奏功,也一点不犹豫的主张立即兴兵讨袁”。(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二次革命失败。“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云贵义军未起以前,袁逆之爪牙腹心多散布一种流言,谓非袁则乱。国民之无识者,亦畏袁逆及其爪牙腹心之武力,以为非袁真乱也,遂种种拥护袁逆,一若袁逆去而中国即陷于不可收拾之境者然。”(《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3页。)
当然,研究认为:“民国二年时并不是‘民心’对于袁氏有如何特别的好感,不过是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他们方可安居乐业的意思。”而“假使袁政府在赶走革命党以后,果然有若何的德政在民,或者还有几分拥戴的心理,但是自从癸丑赶走革命党以后,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第383页。)由此,当护国运动发起时,老百姓是“每得一南军胜利之信,犹互相告述,兴味甚浓。至如北军之克服叙州取回纳溪,在政府方面极力铺张,以示威武,而民间反以沉寂态度相对付。质言之,晋人始终未忘其旧爱之共和而已。然晋人绝爱和平,初非好有事者。对于袁项城初亦无轻蔑之意,而此次自滇黔发难,人心因之大移,观念已绝对不同”。(《申报》1916年4月17日。)孙中山亦言:“今云贵义师起后,响应者达六七省,拥护共和之声遍于全国,而袁逆乃不幸于未明正典刑之日,见绝于天。”(《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3页。)
“文归国,既以用兵之原为父老昆弟,告曰:吾素与袁氏非有私怨,为其坏约法叛民国,是用讨之,以惩不义,而奠我国家。……今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让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则今犹是志亦愿与国人共勉之也。”《申报》1916年6月9日。当然,“共和体是否为世界之最良,此事可(听)之数百年后学者政治家之论定。然在吾人创造民国,则实本良心上之所信,而不惮牺牲一切个人之私利而为之。其得多数人之赞同,绝而复续,要亦人人本其良心之所信,而无何等自私之念于其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8页。)
第三,地方分裂局面凸显,开启了中国“由震荡到有序”的历史变迁之途,在人类社会进程中,亦存在着与自然进程相似的运动规律。以物理学和系统论的观点:如果某个“系统对这一入侵来说是‘结构稳定’的,新的活动方式将不能自己建立起来,而且这些‘革命者’将无法活下去。但是,如果结构涨落成功地施加自己的影响,例如,假设这些‘革新者’赖以繁殖的动力学是足够迅速,使它们可以侵入该系统而不是被消灭,那么整个系统将采取一种新的活动方式,其行为将由一种新的‘句法’所控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已面临了“革新者”已经侵入该系统(推翻晚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其必然者,是这种从形式达于内容的政治结构变动,“可以引起一个全新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将剧烈地改变该宏观系统的整个行为”。(伊·普里戈金等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第238页。)
对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必然发生社会剧烈震荡之要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一般归结为“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其所领导的军事运动很难有效地承担起将反帝反封建斗争进行到底的历史重任”,因而,当1916年护国运动愈演愈烈,袁政府撑持不住时,“北洋军阀开始分崩离析,北洋武人中再也没有一个像袁世凯那样能够统制各路诸侯的核心人物”。(章开沅等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390页、第700页。)
与此同期,“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省联合之军政府也于广东成立”。参看《申报》1916年5月13日。因为南方护国军不仅要求袁世凯下台,并认为要真正恢复约法,不清除帝制派余孽则“一日不能取信于南方”。《申报》1916年6月20日。尽管之后南方军政府亦曾取消,但已经埋下再次分野的必然性。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在当今形势下,即使袁氏退位,袁派势力仍将掌握政治上之中心权力,故有新思想之革新派主张绝不能为彼辈所容。”(《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5页。)
而从规律来看,当这种革新的因素已在某个社会安家落户,其所造成的“涨落不是在衰退下去,而是可能被放大,而且影响到整个系统,强迫系统向着某个新的秩序进化”。(伊·普里戈金等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事实正是如此。护国运动“帝制战争的目的在倒袁,袁的倒毙算是帝制战争的正产物;袁死而北洋政府失去一个统帅的首领,伏着分裂的危机,便可算是帝制战争的副产物。但除此之外,还有—些副产物,就是在帝制战争中南北各方地盘割据思想的潜滋暗长,培植许多小军阀的基础。”(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而之后,也正是在地方分裂的争斗中,亦为各种政治思想文化的多元存在提供了空间,如新文化运动即发生于此后不久,当时政治思想意识影响较大者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而又是在持续的论争、实践(历经战争与社会动荡)与历史选择过程中,最终为以毛泽东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贯彻铺平了道路,并再次以人类历史进程演绎了自然法则中“由震荡到有序”的理论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