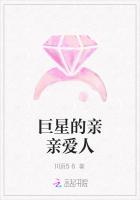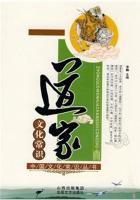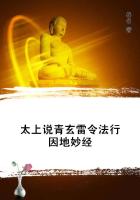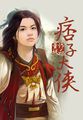童银舫
2009年11月7日,我正在参加作协组织的绍兴采风,手机响了,一看,是华宇清教授的手机打来的,但声音却不是他的。因车上人声嘈杂,我无法听清对方的每句话,只是隐约听到“今天刚办完他的后事”。我怕听错了什么,不敢多问,而游览的兴趣一下子消失,水乡景色顿时蒙上一片阴云。
当日回到家里,急忙上网查询,终于在浙江大学网站上见到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顾问、杭州市亚太文化研究会会长华宇清先生,因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2日下午2时55分逝世,享年72岁。
一
在我的印象中,华宇清教授是个从不摆出大学教授架子的知识分子,他真诚待人,和蔼可亲,笑容可掬,谦逊低调。他敬畏学问,一丝不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在他的眼里,只有可敬的长者,可爱的学生,只要人家有一点长处,就予以肯定和表扬,从无恶言厉色的时候。
我与华教授相识于1984年。当年,我正在一所中学任代课教师,业余编写《慈溪书话》和《三北名人录》。当时的大学教授,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何等的人物,简直是学问和真理的化身!当知道杭大教授华宇清先生是慈溪老乡时,20岁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给他写信,征集他的材料。华先生很快给了回信——
童银舫同志:
您好!
收到您的信,十分高兴!您在教学之余,还研究地方文史,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这是要向您祝贺的。
《金果小枝》,手头已无书,待再版后,一定给您寄上一本。明年还有三本书可出版,到时也一定赠送。
编撰《慈溪名人传》很好,但我不算名人,可不必考虑。
近日正筹备全国性的讨论会,实在忙,恐您挂念,先给您寄上一信,待后我们详谈吧!
祝
好!
华宇清
1984.10.3.晚
这是华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笔迹秀丽端谨,语言朴实又谦逊,竟然一连用了七个“您”字,让我终生难忘,并且影响我以后的处事态度。
1985年,我和本县几位文学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七叶诗社,斗胆聘请了慈溪籍的三位文学家作为诗社的名誉社长和顾问,名誉社长是崇寿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两位顾问,一位是鸣鹤镇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版本学家、诗人路工先生;另一位是白沙镇人,杭州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外国文学专家华宇清先生。华先生十分支持我们的诗社,1985年12月14日,他在来信中说: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你们成立七叶诗社,就是做叶的事业,一片片小小的绿叶,它植根在肥沃的土壤上,必将以它的生命的光辉,启示着人们为着崇高的事业而奋斗!
袁可嘉先生是老九叶诗社的著名诗人,他任你们的名誉社长,这是非常理想的,在他的鼓励和关怀下,你们的诗社一定会很快的发展。他最近来信,对你们的诗社非常关心,说“此事关系培养新生力量”,他是乐意担任名誉社长的。路工先生担任你们的顾问也很合适,至于要我担任顾问,实在不敢当,但我一定支持你们!
今寄上《金果小枝》上册,赠给诗社的同志们!
1986年10月24日,他又专门来信:
你们寄来的《七叶诗刊》都收到,我每期都读了。诗友们的诗,感情都很真实,有不少诗写得很清新。从近几期的诗歌看,诗人们的进步很快,诗歌的思想倾向更健康了,正如黄江风、黄梅峰在第十期编后语中所说:“值得庆喜的是,诗友们都从花草丛中走来,跑到太阳下沐浴了,朝着大海的波涛拼进了。”
我很希望有机会和诗友们见见面,大家一起交流思想,谈论诗歌欣赏和创作。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诗社在受到经费毫无保障(完全自费)、联系方式落后和成员意见不一等制约下,勉强维持了一年光景,编印了十一期社刊,终于不了了之。现在想来,我除了感激袁可嘉、路工和华宇清先生三位乡贤前辈的无私帮助,也为我们的幼稚无能、半途而废而深感愧疚和惋惜!
二
我不懂外国文学,无法对华宇清教授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成果进行评述。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金果小枝》一书,却是当时广大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千方百计借阅传抄的一部热门书。这部书初版于1982年12月,大约在次年春上市,初版为平装本,印数26500册,但一上架就被争购一空,1985年重印时,又出版了精装本。本书的副题为“外国历代著名短诗欣赏”,共收了33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诗500余首。“所选的短诗,大部分是特请著名翻译家、专家、教授从各语种的原文选译的”(《金果小枝》后记),华先生自己也翻译了一些。书中除了对各国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作了简要的介绍外,他对每首诗都以“随感”的形式作了简析,往往一语中的,给读者以点拨和启发。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孙席珍教授在序中称本书“破除了门户之见,不拘一格,见好花便予采撷,见佳果随即拾取,看来意在使读者开拓眼界,一尝新味,我认为这也不失为本书的一个特色”。
我每次拜访华教授,他总是跟我谈泰戈尔,他说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亚洲第一个受世界公认的学者,泰戈尔作为中印文化民间使者,对中印文化的民间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华教授特别兴奋,说他的一部学术专著《真实与神秘——泰戈尔研究》即将出版,另一部《泰戈尔传》也将在台湾出版。他还谈了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老子对泰戈尔哲学体系的影响。
我陆续收到华教授编的有关泰戈尔的书。如《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吉檀迦利——泰戈尔散文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泰戈尔诗歌精选》(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泰戈尔诗选(导读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等,有的还有精装本、豪华本。他在信中还说将出版《泰戈尔研究论文集》、《泰戈尔中短篇小说精选》,翻译《泰戈尔自叙》,成为一个系列。他的这些著作中,《泰戈尔散文诗全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奖和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三
华宇清教授甘于寂寞,一心扑在学术上,不愿张扬,更不屑炒作。1994年12月9日,他在信中说:“在学术上要搞出一个体系是很难的,我正在努力。我只想默默地工作,不想宣传。因为与老一辈专家如袁可嘉、季羡林等是不能比的,我非常钦佩他们,我们的功底与他们差得太远,所以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才好。”当时他已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正教授,全国有名的外国文学专家。
记得2002年6月,华教授在回乡为他的89岁老母建造新居时曾破例接受家乡媒体《慈溪日报》的采访,但他照例不谈自己的学术研究,只谈家乡的变化、童年的往事和对朋友的思念、对老母的孝心,害得记者花了不少精力搜集他的材料和著作,然后写成《不愿张扬的华宇清教授》公诸报端。记者在文中说:“虽然华教授学术成果累累,但家乡并没有很多人知晓,这是因为他不愿张扬,喜欢低调。他不喜欢记者采访他,也不愿媒体宣传他,但他喜欢跟晚辈交流。他从不摆架子,总喜欢以诚相待,以朋友的身份和人交谈。他是位谦虚、热情、和善又风趣的老人。他思路敏捷,语言跳跃飞快,往往在说甲的时候,又说到了乙,然后又延伸到丙,和他在一起,总让人受益匪浅又让人快乐无穷。”记得那天他来我的书斋,直夸我的书比他还多,说一个人能坐拥书城,宠辱皆忘,是人生一大快事。同时,能有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相往来,谈天说文,交流读书心得,彼此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未经此道者,难以体会,所以更显得珍贵。
华教授极重乡情、人情、友情,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素不相识的读者,他总是热情相待,有求必应。他曾在家里设宴招待我,甚至回家乡时与学生、亲友相聚时,也是他掏腰包做东,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有一次——1998年3月15日,他来慈溪讲课——辅导外国文学,附近几个县市的电大自大考生都慕名前来,课堂坐了好几百人,连走廊都挤满了。他操着家乡的口音,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把课程重点都罗列了一遍。据说效果极佳,许多考生后来都取得了满意的成绩。那天中午,他回绝了主办单位的宴请,叫了几个学生、朋友聚餐,事先声明由他买单,反客为主,其乐融融。
往事如烟,音容宛在。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和善如弥勒,爽朗似大侠,知识渊博,谦虚内敛的长者、学人突然离去,他没能来得及从容整理完成《华宇清文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泰戈尔《飞鸟集》云:“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或许可以用在他的身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