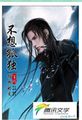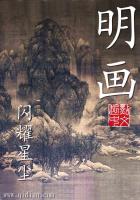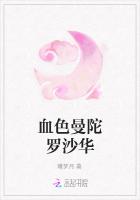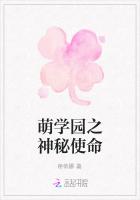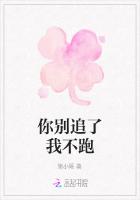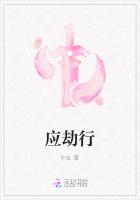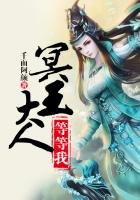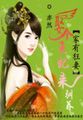余麟年
一
宓莲君先生名清瀚,观海卫镇宓家埭人,光绪辛卯(1891年)浙江乡试中第86名举人,三年后赴京会试未中。按清代的科举制度,只有会试考取进士后才符合入仕首选,但吏部有“大挑”的规定,举人如接连三次参加会试不中者,可选择其中部分优秀者,出任官职。宓莲君感到参加会试前途渺茫,“大挑”取仕严而又严,等待大挑也很难求得一官半职,于是决定放弃仕途,把攻读科举之学转变为钻研岐黄之学,按照中国知识分子“人不能当良相,亦应当良医”的为人宗则,悬壶为民治病。他攻读《内经》、《难经》、《神农本草》、《金匮论》以及其他历代名医著作,深入研究脉法。因善治伤寒火症,被人称为“当代张仲景”,成为誉满江南的名医。甬上名医范文虎临终前感到后继乏人,曾感叹道:“我道无人续。”后起之秀三北名医洪潜菊看了宓莲君许多方剂、脉案后曾指出:“宁波府下医道能续文虎和超越文虎者唯清瀚耳。”
中医诊断疾病靠“四诊”之说,即望、闻、问、切,就是通过以上四种手段,考察诊断病情。宓莲君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大胆提出以“切”(切脉)为主诊断疾病的主张。他认为人的有病甚至预知生死,均反应在脉上,而三诊(望、闻、问)中所收集的病案往往多有假象,如大热反寒、大虚反实,甚至回光返照等各类虚假现象,常为医者所错觉。而脉无假象,只要细细辨之,即能正确地判断疾病,故提出“舍症从脉”的识病主张,即对一切疾病的诊断必须以脉象来辨虚实、寒热、阴阳、表里,进行辨证论治。他对历代脉法还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在长期治病实践中写成的《清瀚自省录》被当代医学界视作珍宝。自然,也有医者贬其过偏,提出轻三诊而重一诊,只能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应用,若普遍推广,实属过偏。何况,在某种情况下,“舍脉从症”亦是上工(高明医生)治病要诀。这一争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在延续着。
宓莲君先生常言,有人久病不愈,非医者不良,实与药物不道地和煎沸不合理有关,他对煎药用水用火要求都十分严格。指出水是一味重要药物,不能随便,按照不同处方,有的要用井水,有的要用河水、长流水、天落水、存雪水、泉水……而煮药用火有文火、武火、桑柴火、百草火及煨、隔水煮等多种,若随随便便,药效减矣!他对煎药时间有严格规定,草本药物煎几分钟即可取其汁,金石药,如龙骨、牡蛎、代赫石、磁石、自然铜等往往须煎几小时才能得其精华。除严格做到先煎和后入外,他还提倡先吃二汁,二汁药和头汁药混合后服用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宓莲君先生有句格言:“药不道地害人匪浅。”如杞子必须选用甘肃的,沙蒺藜宜用潼关的,红花最好用藏红,南、北五味子功效有别,非三年不能称陈皮,不宜用当年萸肉,非三黄不能称真牛黄,洋春沙(蚕粪)要用夏蚕,桑叶必须经过霜降后才可入药,特别是芦根、霍香、佩兰必须用当天采集的。尤其鲜芦根,退热功同犀角、羚羊,若用干的代之,贻误病情。
宓莲君先生十分重视食疗,他指出,“要长寿,宜清淡,淡味为百味之首”。又提倡每晨宜喝淡盐汤一碗。所谓淡盐汤,不是普通食盐,而是用淡竹盐饮之。其具体制作,用雌雄淡竹各半,锯断下留竹节,每节放足食盐,在火中煨煅,冷却时盐成竹状,研末后再入淡竹内,如此反复三次,研末即为淡竹盐。这类盐清火,去痰,壮肾水,暖丹田,宽肠胃,每晨少量饮之,可却百病。
二
宓莲君先生曾是我家保健医生,先祖父和先父常言,“先生者,神脉也”。现根据他们早年口述记录介绍几个病例略窥之。
早年观海卫义桥有清代翰林陈祥燕先生(庶吉士,任江西鄱阳知县),请他开一个滋补膏方,之后即来我家用饭。祖父问他,祥燕兄无恙否。他回答三月内必死。这一回答,令祖父感到突然,因为祥燕先生三天前曾来我家,送来他的临池,祖父还为他身体健康而祝福。问祥燕先生患了什么不治之症,宓先生回答:“无病也,唯脉搏出现有规律结代,结代者死脉也,若有病出现结代,倒非凶象,燕兄无病结代,内脏败矣。”后不等二月果然亡故。
观城胡家有一青年,年方二十,患了肺痨(肺结核),请先生诊治。先生切脉后诊断为房痨,即色欲不节,肾水不能制火,致心火上炎克为肺金所致。只有“独宿丸”方能治其病。所谓“独宿丸”者,要绝房事一百天,否则无药可救。先生再三叮嘱患者,并关照其父母妻室严防。由于该患者久病性患亢进,禁忌一月又行房事,病情迅速恶化,请先生诊治,先生按脉确认行过房事,无药可救。患者矢口否认,先生即拂衣而出,经患者父母再三挽留,先生回:“不服独宿丸,即使华佗扁鹊再世也难活命。”果七日内死亡。
宓莲君先生书法工整,脉案精通,他的处方本身就是艺术珍品,我家就有范文虎、宓莲君等处方裱装成册,可惜“文革”时当作四旧被毁了。
三
宓莲君先生上午在家悬壶行医,下午出诊,他有诗云“自缘出行喜肩舆”。“肩舆”即轿子,因寒暑要长途出征,他出行必坐轿子。由于沿途病家很多,故常常在轿中过夜。并在轿内放着医书点着蜡烛,在轿中时睡时醒。有时连鞋落在路上也不知不觉,到了病家,常常要讨鞋穿,故三北地方有请宓莲君先生治病要备鞋一双之说。他医德高尚,不论富贵贫贱均同样对待,对危重病人,用药后即使不请他复诊,也要进行再访,甚至为贫穷者付钱买药,并备有急救的丸、散、膏、丹免费供人使用。宓先生对钱十分慷慨,但有一样非常吝啬,他在开处方时如药方被风吹走或落地玷污,再不换第二张药方,而是把药方直接写在桌子上。故有人称他为“讨鞋先生”和“桌上郎中”。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和沈旭娜同志一起拜访名医张迪蛟先生,并于早年和浙江中医研究院的吕志连医师共同搜集过宓先生医案,他们一致认为宓莲君先生确实是近代名医、儒医、医学理论家,而家乡慈溪却无他的记载,实在可惜。宓先生对药物道地泡制、应用、煮沸和禁忌等许多说法值得当今医学界学习和借鉴。当然,随着科学发展时代进步,先生许多珍贵的医学遗产也有许多可以商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