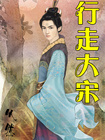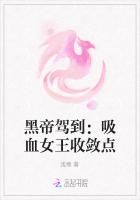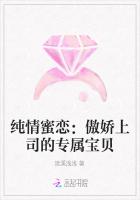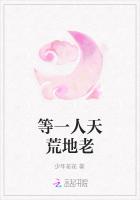笼中之鸟
尔朱荣及其党羽自从拥戴元子攸即位以来,已接连击破葛荣,平定邢杲,屠灭元颢,擒拿万俟丑奴,使本已无力回天的北魏王朝又枯木缝春,重新屹立在北方大地,是再造北魏江山的赫赫功臣。此时尔朱荣的处境比曹操当年要好得多,他俯视整个帝国,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位敌手,谁都不敢对抗他的威严。可他如果像曹操一样聪明,暂时克制住自己的贪婪,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使北魏政权日渐转入己手,那么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将会出现一个被称为尔朱王朝的政权。
然而尔朱荣的功业早已被历史的尘埃覆盖,只在“河阴之难“中留下了比董卓更重的骂名,因为他的残暴无情,他的粗俗不堪,他的贪婪自大已注定了他和家族的迅速灭亡。
他本性的残暴使世人心惊胆战。他心血来潮,一朝可以屠灭两千朝官;他会让手下与虎豹肉搏,即便死伤无数也丝毫不顾;他喜怒无常,刀槊弓矢,片刻不离于手,心中稍有不顺,即行杀戮,亲近左右也朝不保夕。
他文化上的粗俗与汉化已深的北魏君臣更是格格不入。他举止轻脱,只以驰射为乐,他对衣冠礼乐丝毫不通;他喜欢喝得烂醉如泥,在酒酣耳热时狂跳胡族舞曲,狼嚎不止;他逼群臣同乐,与其共舞,王公妃子亦不能相免,直至闹得天昏地暗才善罢甘休。
他对帝位早就贪婪不已,与元子攸更是势同水火。他早欲称帝,四铸金人,受神意阻拦后才作罢;他又操控朝政,一手遮天,对帝位依然虎视眈眈。
自古以来,君王和权臣之间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争夺,即便贤明如霍光,终不免家族夷灭的惨剧。而尔朱荣对魏室虽有再造之功,可他的暴虐和猖狂更甚于董卓,他与元子攸之间毫无弥合的可能。
所以这天下大定后,最烦恼的却是那个君临天下的人——元子攸。各地的叛军看似与元子攸捣乱,但实质上却近似于他的盟友。元子攸本来还可依仗他们与尔朱荣对抗,使尔朱荣无暇顾及操控朝政,为自己赢得东山再起的机会。
可现在这些不中用的盟友被尔朱荣统统地拔除了,只剩下自己孤零零地苦苦相撑。元子攸明白这决裂的一刻终于来临了——尔朱荣平定关中后,下一个剪灭的便是自己。元子攸身上流的是狼族的血,他不会心甘情愿地沦为尔朱荣的笼中之鸟,他决意要破笼而出,即使最终拼得笼破鸟亡也在所不惜。
可元子攸也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虽身为皇帝,但自身实力却与尔朱荣相差悬殊。从军队来看,国中能征善战的部队几乎全部听命于尔朱荣,只要他一动手指头,自己便无还手之力;从朝政而言,元天穆、尔朱世隆等人占据着朝廷的要害位置,而自己的左右也全是尔朱一党;从地盘来看,现在关中、山东、河北、山西这些要害之地全部掌握在尔朱家族和党羽手中,自己唯一能争取的只有洛阳、河南一带。
如此看来,自己似乎已接近穷途末路,祖宗江山即将沦于尔朱荣之手。
但元子攸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从君臣名分讲,他是君,尔朱荣是臣,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顺,而尔朱荣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背负篡位的恶名。从人心向背来看,尔朱一党犯下河阴之难,残暴无比,人神共愤,而他能体察民情,与民同乐,为天下人所寄望。从文化种族而言,尔朱一党多是羯族遗种,粗俗不堪,只以驰射为乐,对衣冠礼乐更是一窍不通,毫无政治远见,与天下早已汉化的大流相背离,而自己和洛阳百官对中原文化早已融会贯通,为天下民心最终所向。尔朱荣只是凭武力取得一时优势,只要自己抓住时机,适时出击,依然可以力挽狂澜。
不甘和仇恨让元子攸咬牙切齿,时时刻刻欲铲除尔朱荣而后快;但实力的悬殊让元子攸更是心惊胆战,在做决定时往往投鼠忌器,比哈姆雷特王子更加犹豫不决。面对尔朱荣实力上的威压,元子攸在以后的行动中把自己的优柔寡断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尔朱荣却无任何担忧,他认为元子攸已成自己的笼中之鸟,现在只需玩一些古代那些权臣和弱君之间的禅让游戏,江山自然会落入己手。此时一手遮天的他更加有恃无恐,四处挑战元子攸的尊严。
由于尔朱荣的权倾朝野,对朝政说一不二,那些官场上的野心家都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地往晋阳跑,走尔朱荣这条终南捷径。尔朱荣来者不拒,大批举荐官员,北魏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全都应承。
可也有意外,他的特权受到了挑战。他举荐了一个类似于阿猫阿狗的角色去接任曲阳县令,可能这个人的出身和才识太不堪了,当时的吏部尚书李神俊便很不识抬举,以阶位悬殊为由,把那人给拒绝了,另派他人前去上任。
尔朱荣闻讯大怒,但他选择的不是向组织申诉,而是自作主张,马上让那位老兄鸠占鹊巢——自己跑过去直接上任,把那位朝廷举派的县官一赶了事。当然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尔朱荣窝在山西的时候就干过:他一怒之下便敢把对自己不敬的肆州刺史关押,派自己的亲属担任此职,而无能的朝廷对此也是不闻不问。所以现在权倾天下,随意补个县令在尔朱荣这里更是小菜一碟。
那位顶撞他的李神俊知道惹了大祸,也赶紧辞职避祸。尔朱荣毫不客气,让自己的堂弟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兼任吏部尚书,几乎把朝政全都包揽下来。得寸进尺的尔朱荣玩起了釜底抽薪之计,他知道河南之地汉化最深,对他的抗拒最强,是元子攸对抗自己的唯一屏障。他开始投石问路,向朝廷举荐自己的党羽担任河南各州的地方官。在尔朱荣眼里,软弱的元子攸肯定会对他言听计从的。
绝境挣扎
可元子攸知道河南之地是自己咸鱼翻身的唯一本钱,绝不能对尔朱荣一让再让,便非常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尔朱荣的要求。尔朱荣没有死心,继续授意元天穆向元子攸重申这一无理要求。面对元天穆的苦苦相逼,元子攸依然死死守住底线不放。
元天穆见游说不成,终于恼羞成怒,说出了大逆不道之语:“天柱既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违之,如何推荐数人为州官,竟然不用?(尔朱荣因数次功勋,在讨破元颢后,被前无古人地封为天柱国大将军)”这话已经说得毫无臣子之心了,完全是在威逼利诱:这天下都是尔朱荣打下的,这官员还不是任由他随意安排,你这小皇帝得顺着他的意,有个台阶下就行了。而且话中带话,言外之意便是尔朱荣要是想当皇帝,你也得乖乖地听命于他。
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元子攸没有丝毫示弱,却敢于针锋相对:“尔朱荣若不为人臣,把我也一并替代;如他还有臣子之节,无代天下百官之理!”元子攸忧愤之下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只要我还是皇帝,这江山就是我的;尔朱荣要是想当皇帝,那么就索性夺过去,我不会这么心甘情愿做傀儡的。
尔朱荣见自己的试探失败,恼怒交加,说出了心里话:“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但由于当时天下未稳,尔朱荣尚不敢轻举妄动。
趁着关中平定,尔朱荣再次发出试探,向朝廷奏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言,已斥遣令去。”九锡之礼是古时天子赐给功勋格外卓著的诸侯、大臣(如匡扶社稷、再造江山)九种器用之物的礼节,如车马、衣服、斧钺、弓矢等,是皇帝赏赐大臣的最高礼遇。按常理而言,尔朱荣的功业获得九锡是理所当然的。元子攸要是大方识趣点,应该早点主动赐予才对,不必等尔朱荣来讨的。
但是九锡之礼在中国走马灯似的王朝更迭中早已变了味,远不是赏赐之礼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在这之前接受过九锡之礼的都是何人:王莽被西汉授予九锡,结果立马篡位,建立自己的新朝;曹操被东汉授予九锡,他的儿子曹丕后来篡汉建立曹魏;司马昭被曹魏授予九锡,他的儿子司马炎紧接着篡魏建立晋朝。
而与北魏百年对立,只有一江之隔的南朝,九锡之赏和篡位换朝这两者相伴相随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南朝那几位开国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都曾毕恭毕敬地接受过前朝的九锡之礼,然后立马接受禅让,改朝换代。由此可知,九锡在那时早已成了篡逆的代名词。北魏自建朝以来,无人享受过此等赏赐。尔朱荣并不满足天柱国大将军一职,他知道接受九锡之礼后,离帝王之位便只有一步之遥,便向元子攸提出了这一要求。
但尔朱荣也知道这要求的分量,所以也把话说得非常委婉:是我手下不懂事,说该给我九锡的;可我自己很低调,非常忠心耿耿的,已把这一派胡言的家伙教训了一顿。他的话外之音便是:元子攸,有些事,你该主动一点,别老让我这么逼着。
面对尔朱荣再次的投石问路,元子攸更加厌恶痛恨,马上就坡下驴,夸奖尔朱荣做得很好,很有臣子之节,没有留给他一丝幻想。
见此计又不成,尔朱荣并不死心,他明白该亲自跑一趟洛阳了,把那些历史旧账全部清算干净。
千钧一发
公元530年的农历八月份,也是尔朱天光平定关陇的第二个月,尔朱荣欲借此新建功勋,以皇后(尔朱荣嫁了两次的活宝女儿)即将产子为由,要进京朝拜。
此言一传,整个朝野震动:狼来了!自元子攸即位以来,尔朱荣一共只到过洛阳两次,但那两次他都不得不来。第一次是拥戴元子攸登位,沉杀了胡太后,屠尽了百官;第二次是击败元颢和陈庆之,扶持元子攸重返洛阳。连上次他在邺城击败了葛荣的数十万大军,他都没去洛阳亲自领赏。而这一次,他竟然以探望女儿这样的家常事为由入京,人人皆不信服,都认为尔朱荣此行必定深藏着巨大的阴谋。这对洛阳而言,无疑是地震一般的消息,全城人情忧惧,惶恐不安。蝴蝶效应果真明显,那边尔朱荣的消息刚一传出,胆小者如中书侍郎邢邵早已离城而去,向东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