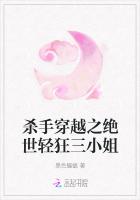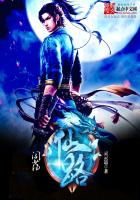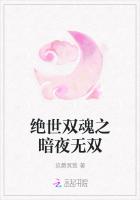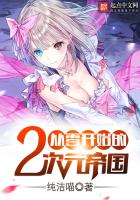将曾被排斥、遗漏在外的文学,例如通俗文学(还应加上旧体诗词、戏曲)重新纳入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这不应是简单的“拼盘”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一个研究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别的研究,而是从“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二者的既对立、竞争、制约,又互相渗透、影响的“关系”中去把握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生态发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65展,由此将会展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景观。在这方面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包括原始资料的重新发掘与整理)要做。我在准备本文的写作中,读到了董健先生在《文学评论》1998年第7期上所发表的《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艰难历程———20世纪中国戏剧回顾》,文章明确提出:“20世纪中国戏剧最大的、带根本性的变化,是它的古典时期的结束与现代时期的开始,是传统旧剧(戏曲)的‘一统天下’被‘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崭新的戏曲文化生态所取代,并且由新兴话剧在文化启蒙和民主革命运动中领导了现代戏剧的新潮流”。
文章还指出,在20世纪戏剧发展中争论最大的“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戏曲的问题,一是传统戏曲自身如何进入现代即如何寻找与新时代结合的途径问题”;文章同时具体揭示了传统戏曲的两种变革模式,即梅兰芳式的“体系内”的“移步而不换形”的变动,与田汉式的追求“传统戏曲与时代结合”,“对其进行改革与利用”;又高度肯定了田汉“将传统戏曲的某些艺术‘基因’(如结构的开放性、情节的传奇性、表现的写意性)移植到话剧创作中”的经验———董健先生在这里完全打破了将现代戏剧史的研究局限于单一的话剧发展史的研究格局,从“话剧—戏曲二元结构”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与描述,这无疑是为现代戏剧史的研究与书写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的。
在我看来,这类“关系”的把握,也适用于电影文学与儿童文学、民间文学的引入。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增添了这几个文学类别的内容,这只是一个开始;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深入到电影与电影文学对现代小说与话剧创作的影响;民间文学研究与创作的关系;“儿童的发现”对现代文学观念、思维、创作的意义与影响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总之,《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卷开拓了一个大的研究格局,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这就使本书的文学史叙述具有一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可以看作是本书作者所代表的几代学者的学术品格,这对现代文学研究始终保持活跃的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
(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主编,共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十卷中《1921:谁主沉浮》(孔庆东著)、《1928:革命文学》(旷新年著)、《1942:走向民间》(李书磊著)、《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著)四卷,都写的是“现代文学”这一段。我所要讨论的是前三本。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虽是一套丛书,主编有总的设计与要求,但对各书作者的制约并不大:这是一匹匹自由惯了的“天马”,各人尽兴地在那里发挥着自己的文学史想象,每一本都是独立的个人著作。丛书副主编孟繁华因此坦然宣布:《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对文学史写作而言,是“回到了一家之言的传统”,“它不再是系统而成熟的‘流别之学’,不注重源流识别和清理,着意强调了某些精彩的特写镜头,而不意属结构的匀称、评价的适中”(《“流别之学”与一家之言》)。而这样的“个人写作”恰好是对传统的“集体写作”的一个反拨。———“集体写作”是四九年以后开始盛行的,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就达到了顶点。最近二十年盛行的似乎是个人著述,但在文学史写作中,无论是通史,还是文体史(小说、诗歌、散文史……)、地区文学史(如沦陷区文学史、东北文学史)等等,仍然是以集体写作为主,而且基本上是前述教科书式的写法,而有些个人著述,也是按照时代(或一个时期)流行的观念、模式、结构、语言去写作的,仍然带有明显的“群体”的印记。我因此而产生这样的感慨:如果我们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观、文学观、文学史观,恐怕很难有真正的“个人写作”。
也正因为如此,当我看到李书磊谈及他的关于“如何认识与评价历史”,也即“如何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和应然性的问题”,并且明确提出“我倾向于把已然的东西都视为必然”;看到孔庆东如此谈到他的“革命文学观”与“20世纪文艺观”:“艺术与革命最根本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反抗,他们的本质都是理想与超越,都是颠覆、毁坏和创造、重建”,“其实,艺术就是革命,革命就是行动艺术”,“革命的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象征的和表现的,革命艺术的极致就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极致”;“没有哪一个世纪的艺术像20世纪这样充满了反抗与破坏,荒诞与扭曲,具有超乎寻常的群众性与政治性。撇开政治、革命这一维度,就无法准确理解20世纪中国的现代艺术”———面对这样的旗帜鲜明的宣言,一方面,我并不(或者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并且希望另有机会与这两位作者进行学术的论争;但我同时又感到一种兴奋:这毕竟是经过严肃的思考而产生的他们自己的对历史、文学艺术,以及历史(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独立见解,并且已经贯彻到各自的研究实践中,展现了不同于他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67人的文学史的想象与评价,孔庆东对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的重新解读,即是一例。这样的著作当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引起愤怒,但近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文学界的“人云亦云,东抄西抄,千篇一律”的平庸局面,那没有争论、缺乏冲击力、毫无生气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静,就这样被打破了。
真正的“个人化”的文学史书写就这样开始出现了。无论如何这是应该欢迎的。
(三)
孔庆东在他的“后记”里有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与思考:“曾和师友议论过文学史应该越写越厚还是越写越薄。我以为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当定论形成之时,便越写越薄;当定论发生问题时,便越写越厚。厚则有缝隙,可以颠覆定论,然后再渐次薄下去。未来的若干年内,我想是应该写得厚一点的时候。”———读到这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联想:前面所讨论的《中华文学通史》近现代卷,以及我们所写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主要作者是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老师辈的学者,实际上是用教科书的形式将这两代人的文学史想象(它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文学史叙述)定格下来;按孔庆东的观点,是应该写得薄一点的,但我们还是写得太厚了。而孔庆东、旷新年、李书磊这样的更年轻的一代,作为学生辈,他们是从学习我们的文学史著述开始进入现代文学的;但现在已经成熟到发现我们的叙述与想象的“缝隙”,进而“颠覆定论”了。开始时难免有种种不成熟之处,甚至在揭示前代人“缝隙”的同时,自己也留下了不少容易被人攻击的“缝隙“;但现代文学研究或许就将因此而进入新一轮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面对这样的前景,我是很受鼓舞的。
因此,他们的著作当然要写得“厚”一点。———想想看,单是一个年头(1921、1928、1942)及其前后,就各写了二十多万字。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的观照、想象与叙述方式;于是,原先进入不了研究者视野的文学(社会文化)现象现在进入了;原先被忽略了的原始资料现在被发现与激活了;原先觉得无话可说的地方现在有话(而且是很多的话)要说了,等等。人们突然发现,过去认为已经十分狭窄的现代文学研究天地,原来竟是如此的广阔,还有多少“生荒地”
等待着人们去开垦与发掘啊。我知道,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的研究者与研究生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地”已经被前几代的学者“分割”完了,自己只能做些“补遗”的工作。这样的无所作为的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一点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几位年轻朋友的写作实绩是可以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的。
关键是前面已经说到的文学史观念、想象、方法的转变与创新,寻找与确立属于自己的历史观、文学观与文学史观,抓住这一环,整个研究路子就活了。
那么,我们这里讨论的几位年轻的作者发现了什么“缝隙”,并怎样开始了自己的想象与叙述呢?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三位作者都选择了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的历史评价作为突破口。这可能有更为深刻的9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背景,这里暂不作讨论;我想说的是现代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发展的背景。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很长的时间里,现代文学的叙述是一种等级制的历史叙述,人们按照“革命”与“非革命”(而当时流行的逻辑,所谓“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与此相应的还有“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反现实主义文学“的对立等等)将现代文学作家与作品一分为二:前者被称为“主流文学”,并具有几乎是唯一的合法地位;后者称为“支流”与“逆流”,甚至失去了合法性。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倾向甚至发展到了极端,连“革命文学”中的相当部分(如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中的一些代表作家作品)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的文学”而打入冷宫。面对这样的实质上的“文化专政”,我们这一代学者研究工作的起点,就不能不是在我们的老师们的带领与指导下,进行文学史研究上的“拨乱反正”,也即“颠覆”原有的“定论”,对所谓“支流”与“逆流”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价,而同时对置于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革命文学进行质疑,着重于揭示其被掩盖了的负面。对我们这些在大一统、等级制的社会与文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学者,这既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又是痛苦的自我清理的过程。但后来学术的发展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原先被称为“支流”与“逆流”的“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学,例如作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被称为“现代主义”
的作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偏于闲适、幽默风格的作品,等等,又被置于主导(类似于“主流”)的地位;而“革命文学”则似乎被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读者所遗忘,连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受到了怀疑,“革命”(与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成了“专制”的同义词,于是,鲁迅对革命与左联的支持都成了他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69的“局限性”的证明。———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理路却根本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仍旧是一方压抑另一方的等级叙述。应该说,对于这样的倾向,我们这一代学者大都是不满的,在我们所撰写的文学史著作(例如《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初版本与今年出版的修订本)中都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延安工农兵文学作了具体的分析:在指出其思想与艺术上的失误、不足的同时,也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但也无可讳言,由于这些年对革命文学的研究没有新的进展,我们在修订本中虽也作了一些尝试(如对《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的分析),总体上仍缺乏新意,成为整个文学史叙述中的薄弱环节。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几位年轻学者的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他们重新张扬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延安工农兵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有时甚至不惜用了一些极端的言词———他们的本意并非要回到“全盘肯定”的老路,事实上他们的历史叙述里仍然有批判性的分析,但作为一种叙述的策略,他们似乎有意要淡化这种批判性,而强调肯定性的方面。尽管这正是我所不赞同的,在我看来,在学术研究上采取“矫枉过正”的策略弊多利少,是不必要的;但我仍然赞赏他们为开掘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的被掩盖的价值所作的学术探索。例如孔庆东从人的内在生命欲求的角度讨论“革命”与“文学艺术”的相通;旷新年则从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的“现代性的复杂对比与矛盾”这一视角,探讨革命文学的性质与价值,指出“普罗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都是一种复杂的共生现象,它们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文学,是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城市的先锋文学创造了一种美学上的强烈震撼与冲击,有力地摧毁了传统的美学范畴和标准,开拓了现代审美新空间”,同时强调了左翼文学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李书磊关注的是1942年前后文学“走向民间”的趋向,延安文艺自不待说,在大后方的文人,例如闻一多的身上,也发现了他对“民间的、原始而蛮荒的东西”的“钦慕”,“对文人与文化的失望”,李书磊认为闻一多正是“由此出发进而向教授阶级及其背后的文化和社会体制宣战,参加实际斗争,终于成为牺牲于街头的民盟斗士”。
这就为四五十年代所发生的“非革命”的文人向“革命”及其文学皈依,提出了一个新的阐释角度。尽管现有的这些研究都还是开始,并没有充分展开,也许还会有新的缝隙,但毕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四)
几位作者还对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作了新的探索。
李书磊说,他的书较之以前的文学史增添了两个东西:“其一是加入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的内容”,“其二是在文学史中加重了文人生活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