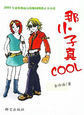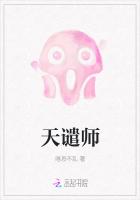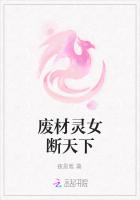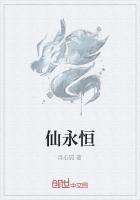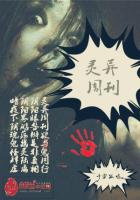这或许也是这三位作者的共同追求。孔庆东就专辟两章,描绘“乱世图景”,剪辑“文化镜头”:从1921这一“好斗的鸡年”所发生的地震,水、旱、火、雹灾与鼠疫,民变,兵乱,血战,到这一年前后的思想、学术、宗教、科技、艺术、教育……的重大事件与普通现象,诸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的论战,长城制造画片公司的开设,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的首演,昆曲传习所的开办,“壬戌学制“的颁布,文言教科书的废止,厦门大学的创立,报刊的迅速发展,广播电台的草创,“北京人”化石、“仰韶遗址”的发现,北京协和医院的正式命名,等等,都一一勾勒于作者笔下,他的目的是通过对时代文化生活、制度变迁的各个侧面的描述,揭示1921年前后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潮流”: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百废乍兴”,从而“呈现出一片既旺盛又混乱,既自觉又幼稚的‘乱世’局面”;作者分析说:“乱世是‘中心’缺席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文化)因此而得以“显示出令人向往的自由和巨大的创造力”,而文学(文化)上的这种“自由与潜力”又是“以乱世的民不聊生为代价的”。———作者这样的将时代文化、精神风貌的“全景式”扫描与文学景象的“特写式”的突现二者结合、相互映衬的写法,不仅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也标示着观念与方法的变更,如李书磊所说,“过去的文学史多将文学从思想文化史中抽取出来单独研究(顶多将文学史与政治史生硬地结合一下),这对于强调文学的专门性质、弄清文学史的细部情况是很必要的;但仅仅有那样一种文学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将文学放回社会精神潮流中的有机研究与描述”。
如果说孔庆东关注的是时代文化的“全景”,旷新年则是从他所研究的对象———3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特点出发,把对时代文化的关注集中于以杂志为中心的出版文化的研究与描述上。他认为,“五四时期普遍的‘同人刊物’现象是现代新知识分子崛起和启蒙话语扩展的明显标志。1928年杂志和报纸与大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71众的结合带来了政治化和商业化这种文学生产的变化。在这里,文学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五四文学断裂,转变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与商品生产,并且成为独立运作的力量”。旷新年事实上是以把“现代文学生产”作为把握与研究、描述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总纲”来看待与处理的。我以为这正是他的这部著作最有新意之处。而他由此引出的两个结论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学生产方式与过程”,讨论“抽象的文学性”,在文学史研究与描述中,必须重视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生产方式的研究与描述;同时应该重视的是文学的传播方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新文学发展到30年代,“新文学期刊和新文化书店(已经)构成了新文学独立的话语系统,广大的新文学作者和新文学读者通过新文学期刊和书店的媒介,结合成了新文学的共同体”,这样,“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文艺杂志(还有文学书店、出版社———引者加)将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现在还只是一个开始。
李书磊最为着力的,是对文人生活的描述。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追求,他说:“过去的文学史实际上只是作品的历史,对作家的生平只有极其简略的交代,谈不上对作家生活状况尤其是生活细节的关注与体察,因而就显得比较单调。所以我在这里试图学习中国纪传体史书的某些方法来写文学史。我想首先要树立一种观念,即所谓文学史不仅应该是作品的发表史,而且还应该是作家的生活史;了解与叙述作家的生活不单单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作家生活本身就应是文学史独立的对象与内容。只有文而不见人的文学史是不完全的,应该试验一种新的文学史的体例,使文人互见,将文学史写成文学界的历史,写成文学生活的历史。”———李书磊在这里提出的“学习中国纪传体史书”,似还可以扩大为对中国传统史书的体例与方法的自觉借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应该另作专门讨论;而他强调打破单一的作品研究的狭窄格局,也是富有启发性的。我想所应建立的是一个“作家—作品—读者”的三维研究空间,这同样也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的。而李书磊自己的写作试验也是成功的。他对1942年的陈独秀、郭沫若,以及沈从文、闻一多……的生活与精神风貌的描述,对昆明、延安两个文人群的精神生活的描述,对延安整风中丁玲、艾青诸人的心理的刻画,不但十分传神,而且对特定历史条件与环境中的人(知识者)的“千般委屈”有着精细的体察与理解。这与作者所采取的态度是27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有关系的;他强调,“回顾历史既须有一种公正评说的无情,亦须对前人有一种真正的同情,对他们具体而不可超越的历史环境有一种清醒的估计”。我对此特别有共鸣,因为我也曾设想,应把“设身处地”与“正视后果”作为文学史写作的两个基本原则,追求一种“冷峻”与“悲悯”相结合的文学史写作风格,与李书磊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五)
几位作者的写作姿态与所采取的写作策略也是值得注意的。
孔庆东如是说:“本书的某些章较多引用了作品的原文,有些章较多罗列了历史事件,目的就是尽量多地把原始景观‘摊开’。我欣赏博物馆的‘传播方式’,材料都摆在那儿,内行人自会看出草蛇灰线的轨迹;另外加上的解说,主要是照顾外行的,当然也可博内行的一笑。”
我又联想起洪子诚先生在他的《1956:百花时代》一书“前言”中的一段话:“‘历史’是可以被处理得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于是,本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对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人作出评价,越来越失去信心”,“虽说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作者觉得,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这里首先是对历史的叙述者(研究者)的质疑,或者说是对自身局限性的一种清醒的估量与认识———因为曾经有一度我们是十分自信的,以为有权对历史事件、人物作出权威性的,甚至是“终审判决”性的评价,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审判者”的角色;而且我们还坚信自己能够发现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历史必然性的阐释者的角色。现在却产生了怀疑:尽管仍不能完全避免评价(因为写什么与不写什么本身就包含了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73评价),但至少对评价的权威性发生了动摇,更毋庸说“判决”了;至于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某种必然的规律性,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我自己则是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可疑的命题。
由此而引发出的是历史研究、叙述的主要目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是通过历史的叙述与再阐释,对历史作出评价,并给读者提供某种规律性的认识,还是主要提供历史的事实,“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自己去领悟历史事实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有时甚至是难以言说的)内容。也许这是一时难以想清楚的,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洪子诚先生在谈到“供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况”的预设目的之后,还提出了一个目标:“能稍稍接近历史”,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历史的本来(原初)面目”?我个人认为是有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叙述是有一个客观的基础的,它是受客观存在着的“历史的本来(原初)面目”的制约的,因而不可能具有绝对的主观随意性;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历史的本来(原初)面目”又是后人可以趋近而无法完全把握、复原的,历史的叙述也总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的,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某种主观预设与意义阐释,所以旷新年在《作为制度的文学史》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1895、1928、1942这些年代出发,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逃脱了历史的预设?”这里所讨论的历史叙述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文学史研究与写作里的悖论,等等,都涉及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几代学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者之间,都是存在着意见的分歧的。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写作实验能引发出我们的这些思考,这本身也算是一个贡献吧。
由此产生的是文学史叙述策略的选择。这就是几位作者一再强调的,突出历史事实(原始材料)的描述,多侧面、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原始景观”,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广泛、开阔的想象与评价的空间。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对“历史细节”的突现。李书磊大概是注重“人”的描述的关系,在这方面有相当出色的运用。例如“曾经惊天动地”的陈独秀晚年竟因“暴食致病致死”这样的细节描述,确实是惊心动魄,“让人对历史诡异的戏剧性生出一种迷离的怅惘”。而郭沫若抱着自己书斋里的花瓶(准备作婵娟怀抱的道具)冒雨赶到北碚去看《屈原》演出的细节,却写出了此时已经欣然受命为“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仍然保留着“迹近可笑”的“少年般的天真和放任”的这一面,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更具体、真切地理解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是大有好处的。
而洪子诚的书里的一个细节运用更让人叹服于作者的眼光:这是1956年《文艺报》第1号刊登的由丁聪、叶浅予、米谷、华君武等十位著名漫画家创作的《万象更新图》,近百位作家按照他们的地位、创作的题材类别、当时正在从事的工作等情况分布在这占有4个16开版面的长卷上。这幅巨型漫画在当时的读者(包括我这样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是引起过强烈反响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被遗忘,以后年代出生的读者更是一无所知了。现在被洪子诚先生重新发掘出来,无论对历史的当事人,还是今天的读者都会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作者却提醒我们注意:“这幅漫画在无意中向人们提示了当时中国文坛的总体状况和格局”,例如左翼作家,特别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占据了新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中心位置;一个主要从事制定、执行文学政策,对文学领域进行领导和控制的阶层已在形成,等等。这里,所显示的是对于历史细节的敏感,以及发现与揭示细节背后隐藏着的意义的思想穿透力:在我看来,这正是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思维的特点与应有的基本素质。
关于对“历史细节”的重视,还可以再发表一点议论。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叙述的策略、方式,而且也包含了一种历史的观念与想象。如旷新年所说,“对于历史写作,是关心长时段,还是注重事件,是沉入日常生活,还是关注危机,这都蕴涵了特殊的历史想象”。我由此联想起作家李锐在读了《1948:天地玄黄》一书以后,给我的来信中的一段话:“说到历史,人们总是更看重朝代更换,更看重军事、经济、政治制度这样一些外在的事件。很少有人把内心里的精神和语言的挣扎、犹豫、死灭、新生,看成是历史的一部分。即使有思想史、文化史,也大都关死在‘制度’、‘国家’、‘民族’这样一些大字眼的框架里。读先生此书,让我看到情感、心灵、语言的历史;让我看到外在的历史,是如何变成带着体温的绝望、犹豫、彷徨和最终无奈的选择;如何变成半杯残酒,一盏孤灯,几行永远封存的回忆。”拙作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评价,但李锐先生的意见却很值得重视,比如他强调写“情感、心灵、语言的历史”就很有理论价值,对于文学史的写作,尤其重要。我很赞同李锐先生的这一意见:“语言的自觉”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中心问题”,一部百年中国文学史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一部“语言的挣扎,不断转向”的历史———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另作专题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前文所提及的对历史细节的重视,实际上就包含着对人的内在精神———情感、心灵……的关注,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这确实是意味着一种文学史的想象新的可能性与新的困惑275方式的。
最后还要说一点:前述对文学史的叙述者(研究者)的自我权威性的质疑,在叙述策略上,则表现为对叙述与评价本身的质疑,相对化处理。在这方面,洪子诚先生的著作是做得比较好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委婉曲折的叙述风格。而几位年轻的作者的一些论断则给人以太满、过于绝对的感觉———当然,痛快淋漓也是一种风格。
1998年12月16日夜在断断续续中写成276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我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自序》里的这段话:“本书的目标不是企图建立一个新型的范式。它不过是未来的新型文学史出现之前的一个‘热身’,为将来的文学史先期地展开各种可能性作一预备。”作为同代人,我对吴福辉这一自期里的“学术中间物”意识是非常理解与共鸣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长河里的一砖一木,过渡桥梁。因此,对本书意义和价值的考量,必须将其置于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情境和脉络里来讨论。
但这又是一个大题目,不是本文所能说清楚的;这里只能谈谈个人的一些观察与感受。2002年我在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了我们的学科发展的两大危机:一是“学术的体制化、商业化,权力与利益对学术的渗透,学术的腐败”造成的“表面繁荣下的学术泡沫化”,二是学术研究的技术化,“有可能走向脱离、回避现实,从而削弱其创造性、批判性品格”,而这恰恰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传统。我因此而谈到:“这些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聊感和荒谬感:我们的学术还有意义和价值吗?”———这恐怕是许多人共同的对学科发展的焦虑感。但我还是抱有谨慎的乐观,在发言里又谈到: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依然存在着“生命的、学术的沉潜”。我的结论是:“一方面是学术的腐败,另一面却是庄严的学术坚守:忽略任何一面,都会得不到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