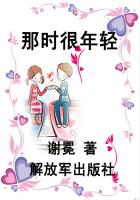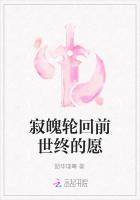语言并非根植于客观事物,而是根植于主体。现代汉语中的“分子”标记不同于其他形式标记,在它的背后,隐含着使用者对事物的政治判断,这种判断通过语言思维而表现出来,因而并不遵循语言学家GZipf所提出的经济原则,即对立中的无标记项是为了节值、省力。它所遵循的原则可以称作“帽子”原则,即取决于人们将事物分类的知识型,这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认知机制,是建立在一种政治心理学上的,由于阶级斗争的影响,那些人们在政治上力求疏远的事物往往被认为是异类的和可憎的,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通过“分子”标记来区分敌我。这使得人们一度谈“分子”而色变,产生出语言学上所说的“标记效应”。当一个人被称为“分子”时,他就不仅是一个“政治人”,被取消了一切个人的特征,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可以说,历次运动都是一场打倒“分子”的运动。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福柯谱系理论的显现,话语创造现实,权力通过“分子”话语的生产、积累、转换和流通过程,制造出各种阶级敌人之类“知识的对象”,从而使权力得以在压迫/反抗的结构式中顺利运转。
今天,许多“分子”称谓已经消失,但新的“分子”仍在不断产生,如走私分子、黑社会分子、盗版分子、盗猎分子、偷渡分子、绑架分子、不法分子、极端分子、异议分子、恐怖分子等。看来“分子”作为“人”的一种代用词,是很难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是异类,他似乎就不配再被称作“人”。“分子”的称谓意味着剥夺他的人格。即使在严谨的法律用语中,“分子”也都用来指有罪的“人”。据一篇未署名文章指出,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仍有40条59处使用了“犯罪分子”,19条24处使用了“首要分子”这样的政治用语,而不是使用“犯罪人”这样的法律用语。《从理性思维谈刑法中的“分子”改“人”》,《内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3期。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在被判有罪之前,虽然已经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承认了他的人格,但有罪的“人”仍然被称作“分子”。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是不称“分子”的,而是称为犯罪的外国人、间谍、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只有中国人犯罪才被称为“分子”。给人的印象是,洋人即使犯罪,在人格上似乎也要高国人一等。由此可见,在“分子”话语的使用上,国人的思维方式还依然停留在旧的知识型中,没有多少本质性的突破。
在现代中国,指称人的“分子”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类型。这个话语的产生与衍化,折射出中国的百年历史。最初,当“人”成为“分子”时,我们的先辈原本是为了表达倡导民主、反对专制的国民国家意识,以争取国人的权利和责任,反映了群的主体性的觉醒。但随后它却被用来表达政党出现后日益增强的阶级意识,成为互相攻诘的政治称谓,最终并成为人的政治身份标记,凸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可以说,20世纪中国人的解放是始于“分子”,也是终于“分子”。其间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国家或阶级群体意识的强化,最终必然会侵犯个人的人格。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在我们的话语中,只有当所有“分子”都重新变为“人”时,我们才能说真正恢复了人的权利和尊严。
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在尼采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看到:一个权威在说话——谁在说话?——你们可以宽恕人的傲慢,假如它是尽可能地抬高这种权威,以便在权威之下尽可能少地感觉到羞辱的话。因此——是上帝在说话!
人需要上帝作为绝对的法令,而不需要上诉法院作为“绝对权威”——或者说,如果人相信理性的权威,他就需要一种统一的形而上学,凭此权威才是合逻辑的。
假定对上帝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这一问题便会重新出现:“谁在说话?”——我的回答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出于动物生理学:是牧人本能在说话。它想成为主人,因此它会说:“你应如何如何!”——它将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个体,它仇恨离群者——它把对一切个体的恨都转移到离群者身上。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页502。
从尼采的话中,可以看到是权威在说话,首先是上帝的权威,然后是牧人的权威。牧人的形象来自希伯来的拯救思想,代表了一种俗世的统治。在福柯看来,这种“牧人权力”就是现代各种社会规训机构,它们支配着话语的生产和传播,使个人“通过意识与自我认识而束缚于他自己的认同”路易斯·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36。。福柯的理论似乎表明,话语都是某种机构或集体霸权的产物。在现代有关知识人的各种话语中,我们同样面临着“谁在说话”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有“牧人”的声音,还有“离群者”的声音。
说到知识人,不能不提到鲁迅的阐释。鲁迅一生中谈论知识人的文字不少,但大都是牵涉具体的人事,从总体上谈及知识人功能和特征的,恐怕就是那篇被记录者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马不停蹄地应邀作了许多演讲,这篇讲演就是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所作。开头即说: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
这话头起得有点意思,谁在骂知识阶级?谁在以此自豪?大概当时在场的人是知道的。不过,说到“打倒知识阶级”,我们也许就未必清楚了。其中透露出某种历史的消息,那就是在这篇讲演中,鲁迅隔着时空,与现代中国另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完成了一场对话。
话得从两年前说起。1925年12月1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又经《中国青年》于次年转载,广为传播。该文将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其中反动派智识阶级指买办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主要是高等知识者,包括华商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其中小知识阶级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富裕人员都属于半反革命。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知识人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尽管此文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以上内容全被删改,但毛泽东当时对知识人整体的看法,却为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这篇文章在当时就激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并在湘粤一带的墙上四处贴出标语,一时间引起知识界的传言和恐慌。时任《政治周报》编辑的共产党员李春涛随即在该刊发表《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支持毛的观点,指出每个知识人都必须参加农工运动,若他们“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就是甘愿为其殉葬,等于是被反动派所杀。一场争论由此爆发。1926年6月,《现代评论》首先发表牛荣声《开倒车》一文,认为假如把知识阶级打倒,这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1927年1月,该刊又发表张奚若《今日中国之所谓智识阶级》,继续予以辩驳,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及共同物质人生观”的智识阶级,用不着张皇其辞地去打倒他。但该刊标榜自由主义观点,也发表相反意见,同年2月,该刊发表宇文《打倒智识阶级》,却主张把那些有闲的知识者送到疯人院、闲人院去,“使他们不至太贫困,不再打扰我们”。同年9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则认为今后的知识者必须民众化、劳动化,让他们“没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直到1927年1月,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还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鲁迅是否十分清楚,无从考知。但时在北京的鲁迅是看到了牛荣声的文章,并在1926年7月1日《马上支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牛荣声此人寂寂无名,鲁迅将他夹在一堆政客名流中,语带讥诮,可见鲁迅是很反感他的言论的,并且可能还读过这方面的争论文章,所以在上海的演讲中才会拿此事来开头。
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谋过面,但两人之间却似乎有着一种奇特的关系。他们一个是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小知识者,一个是出身江浙没落士大夫家庭的大知识者。历史把两人置于同一时代,注定要让后人对他们的关系议论纷纷。余英时先生曾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否定意识的化身,其实鲁迅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更有资格当此称谓。毛一生于知识人中独独佩服鲁迅,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晚年他还说起:“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时,可能会回想起当年在北大受的屈辱,而鲁迅在谈知识阶级时,无疑也会联想起旧垒中各色人等的面孔。问题在于,要发现他们对知识人的某些共同看法,也许是容易的,但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他们的心果真是相通的吗?
这里,得先澄清一个事实。关于“知识阶级”一词的来源,鲁迅的说法有误,爱罗先珂的演讲是在1922年,而这个词最早则是出现于五四前夕,有李大钊的《青年与乡村》可以作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见《晨报》1919年2月20—23日。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是由此而发端,章太炎曾说:“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79年,页823。指的便是这件事。不过,鲁迅对此词本义的了解却是准确的,这个称谓原是指19世纪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反体制的俄罗斯平民知识人,他们最著名的主张就是“到民间去”。中国教育界引进这个俄文词,也就引进了俄国的民粹主义,当时知识人的目的,仍是在传播“现代的新文明”,以壮大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朱自清:《论气节》,载《知识与生活》第2期,1947年5月1日。可以说,现代知识人话语的产生,是当时学界中人借着十月革命的波及,向俄国寻来一种主体性的结果。而其中羼杂的民粹话语,也预设了后来知识人分化的因素。
五四以后,新文化人发生分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人话语。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坚持主体性的诉求,主张通过知识人的参政议政,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改良。1922年5月,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自由主义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胡适后来所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这一周》(短评),1923年1月。,可说是代表了这一派的观点。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知识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必须依附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申明,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对他们来说,知识者只是附属于各阶级的一个客体。1922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同一时期,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在组织的话语中,知识阶级完全成为一个“他者”。于是,在20年代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左派知识人写文章贬斥知识阶级,自由主义知识人却以此自豪。毛的文章就是产生于这种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