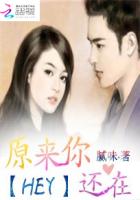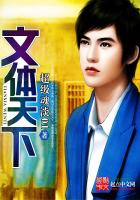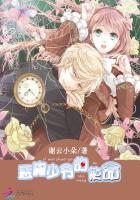按照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话语的社会生产是通过排斥程序来运作的,说话主体必须满足某些权力条件,即掌握所谓的话语权,比如权威的作者,或控制了媒体的社团等等。在阐释、在说话的不过是某种权力意志,而不是主体。因此,在《什么是作者?》的结尾,福柯才会宣称,“谁在说话”这个问题必须改成“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吗”,但也许应当说,只要是群体的发言,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吗。在现代史上,两种有关知识人的话语虽然互相对立,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即都是在以一个群体的名义发言,代表的是某种“整体利益”,依托于某种现代规训机制,或是大学,或是组织,即福柯所说的“话语社团”(societiesofdiscourse)。也就是说,这两种话语都是由权力关系所决定并由权力关系所构成的,它们实质上都是“牧人”的话语,是集体霸权的产物。
应当承认,福柯对主体的解构揭示了知识的本质,打开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对于现代大多数话语的分析是很有效的,尤其是那些代表权力规训机构的主导话语。然而,福柯没有设想任何非霸权形式的主体性,这使他的理论无法解释历史上一些反权力的话语。正如德里达所说:“我相信在经验的与哲学和科学的话语的某种层面上,假如没有主体这一概念会寸步难行。问题是要知道它来自何处和如何动作。”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页499。在现代话语世界里,除了牧人的话语外,有没有一种非霸权的话语呢?当然有的。在尼采的话里,这一非霸权的主体就存在于一个在场的他者,即离群者的形象身上。当说话者不是牧人,而是离群者,代表的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就是一个不再受制于权力的独立主体。换言之,如果说机构的话语都是一种权力话语,那么自由个人的话语则是一种反话语。
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个“离群者”。他一生最憎恶的两个东西就是权威与奴性,二者都与他的“立人”思想相悖。早年的鲁迅曾深受尼采的影响,确立起“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人生观,并且终生未变。“人”是他的目的,这注定了他要从牧人与羊群的世界中出走。所以,鲁迅的知识人观念与当时的两派都不同,完全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话语。在他的话语中,主体始终是独立的,从来没有对任何权力的屈从,也没有对任何整体利益的诉求(包括对知识群体),而是常常处于一种对权力的紧张。像福柯一样,权力是鲁迅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权力关系的揭示构成了他的话语世界。在这篇讲演中,他便是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来考察知识阶级:“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鲁迅1927年摄于厦门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权力往往代表整体利益,甚至是民族利益,它不能容忍一切自由的思想,因为“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与福柯不同,鲁迅把自己的主体性投放到话语中,因而形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权力与知识观念,即权力与思想并非互相包含,而是互相对立的关系。
这种情况下,“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从权力关系入手,鲁迅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真的知识阶级的唯一特征就是反抗权力,这种反抗的主体不是群体,而是自由的个人,所以他没有任何功利心,他反抗牧人,也不想做牧人,因而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在此后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继续发挥这一权力观点。真的知识阶级在这里置换成文艺家,同样被赋予了离群者的形象:
从前的社会也的确没有人想过什么,又没有人开过口。且看动物中的猴子,它们自有它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God那么玄妙)罢了!那里会有自由思想?后来,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你吃我吞,渐渐扩大起来,所谓大国,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国,内部情形就复杂得多,夹着许多不同的思想,许多不同的问题。这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像尼采一样,鲁迅对权力的追溯,也是从上帝的存在到世俗权威的形成。对他来说,任何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不道德的。通过权力分析,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区别,就不仅是社会角色的不同,而且也是权力者与离群者的不同。政治家要维护整体利益,势必仇恨使社会分离的文艺家。“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文艺在本质上是反抗现实的,真的知识阶级也如此。在鲁迅的话语中,知识人的性质、功能类似于文学家,以反抗现状为其特征,并通过反抗建立起自我的主体性。知识人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不再是知识人,而是智囊幕僚,是“冒充的知识阶级”。鲁迅有关权力与知识冲突的观点,属于福柯所批评的启蒙主义话语,但就其反对权力扩张和不断质疑现实而言,他其实更接近西方文学家、思想家包括福柯对现代知识人的角色定义。
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五四以后不同知识人主张宪政或接近民众的两大诉求中,鲁迅最终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主张宪政其实是向权力靠拢,接近民众则是向无权者靠拢。1925年,他在《华盖集·通讯》中曾说:“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那原因,就是他在这篇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知识人往往无视民众,依附权力。他借外国某些知识人一旦地位增高,便摇身一变,“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深刻地批判了中国知识人的根性。这一认识,显然也是来自他的个人经验。在此之前,鲁迅曾与《现代评论》的陈源等人展开了一场笔战。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是胡适,他们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标榜自由主义立场,但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陈源等人却公开站在权力者一边,著文攻击学生和支持他们的教师,鲁迅本人也因此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这使他对此类知识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他把他们比作领头的山羊,脖子上挂着小铃铎,带领羊群到他们应去的地方(《一点比喻》)。因此,当看到《现代评论》上牛荣声的文章时,他才会对文中以上等知识者自居的口气,掩饰不住憎恶,顺便讽刺了一句。
明白了他的思想逻辑,就会了解后来他对胡适等人在《新月》上鼓吹宪政、法治和人权嗤之以鼻,就并非如有人所言,是因为1927年后他的思想改变,要“用一个专政取代另一个专政”,而是因为促使他反抗的仍然是权力,即一切维持现状的力量。早年鲁迅就曾出于“立人”思想,反对过立宪国会的主张,后来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他更加不相信任何制度的建设。他著文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觉醒,而不是为了乞求政府接受改良。在他看来,专制制度下的宪政根本就是空谈,那不过是一种维系现状的“政治”,其目的只是“挥泪以维持治安”(《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与民众的真正解放无关。今人往往说鲁迅是文化决定论者,在政治问题上只有批判没有建构,但对一个专制的政权,鲁迅实在看不出如何宪政,如何法制,又有什么建设性意见可言。鲁迅的批判揭示出了自由主义掩盖下的权力本身。事实上,当初的人权运动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捞够了话语资本后,自由主义知识人终于获得权力者的理解,于是“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的界限》),一个个争当牧人去了。也正是这些知识人,在30年代民族主义高涨时又出来呼唤独裁者,甚至提出:“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式的独裁”(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他们如此渴望规训,以至于达到需要压迫的地步。这表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话语确是受制于权力,他们必然要把一个领袖或对领袖的需要投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对被压迫者进行规训。鲁迅所深恶痛绝的是,中国知识人大都是“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常以社会良心自居,其实却充满奴性和“官魂”,永远站在当下权力一边,心心念念想爬到牧人的位置。在中国,要想有“真的知识阶级”,何其难矣。
当时有人骂知识阶级,有人以此自豪。对于以知识人身份而自豪的自由主义者,鲁迅同样也骂了,而且骂得厉害,那么对“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他会举双手赞成吗?在这篇演讲中,他的回答是不,并提出“真的知识阶级”与之抗衡。在知识阶级必须接近民众方面,鲁迅与中共确有相契之处,这也是毛泽东将他引为同调的地方。但这只是表面的相似,鲁迅始终是一个自觉的知识者,他关心民众是基于民众的屈从权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四文化人中,唯有鲁迅从未对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赞过一词,而是猛烈批判群氓的国民性。到了1925年,他还认为“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若搞思想革命,还得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通讯》。,可见他对真正的知识人期许甚高。他的接近民众,始终是出于对民众的同情,而不是追随民众,更不是充当民众的代表。这与正在进行劳工革命,要求“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烂于一时的五四衣衫”瞿秋白:《请脱弃“五四”的衣衫》,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页333、306。的中共是不同的。这一点毛泽东也早已看出来,1939年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他就说:“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郁之:《大书小识又四则》,载《读书》1992年第5期。实际上,在如何看待知识人方面,鲁迅与毛泽东也是大相径庭的。对于知识人,鲁迅是从权力关系进行分析,提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毛泽东则是从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将其归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鲁迅赋予知识人以主体性,要对民众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则是将知识人视作一个依附性的客体,只有投靠劳工大众才有出路;鲁迅的知识人观念是自律的,主体有反思能力,毛泽东的知识人观念则是他律的,他们没有反思能力,只能由外部力量加以改造。由于鲁迅始终坚持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使得他与忽视民众的自由派知识人以及神化民众的左派知识人都截然不同,而显得茕茕孑立。
鲁迅后期接受了阶级论,别人这么说,他也这样认为。他不仅在30年代加入左联,甚至还说过:“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但是,这只是别人的曲解和他自己的误会。作《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时,鲁迅已经四十六岁,一个人到了这年龄,他的世界观会有多少改变呢?晚年他写《阿金》,区区一个女仆的庸俗,就使得他“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足见他阶级立场的不坚定,一遇到民众的落后就暴露出启蒙立场。鲁迅的思想根底其实是反权力论,不是阶级论。在当时的知识人话语中,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是超阶级论,马克思主义者是阶级论,那么鲁迅则是反权力论,即反对任何权力的压迫。有些时候,反权力论与阶级论仿佛是很接近的,如同鲁迅所说的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阶级论并不反对一切权力,相反倒是要夺取权力,维护权力。因此,在鲁迅晚年,当左联的周扬们试图以组织的名义,对他挥舞鞭子和指挥刀时,他立刻斥之为“奴隶总管”,其憎恶甚至超过对当政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表明他的阶级论最终还是让位于反权力论。
说到底,毛泽东与鲁迅不一样,也缘于他们自身的角色不同。鲁迅是一个文学家,必须保持个性独立,虽然他也谈到过“遵命”,也加入过群体,但他始终是自主的个人,也从未放弃对任何权力的反抗。而毛则不同,他是一个政治家,要维护组织的统一和整体利益。作为政治家,毛始终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对知识人的身份加以定义,如在抗战时期,他把知识人都划入“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在1957年,他又把他们都划入“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无论策略怎样改变,毛的那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比喻,才是真正道出了在他的话语中知识人的真实地位。在他看来,知识人虽是可以利用的力量,但绝不是独立的实体,他是不允许知识人闹独立性的,因此,当王实味想学鲁迅,在延安写出《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尽管比起鲁迅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观点更加温和,但却仍被看成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讽刺的是,王实味死的时候,也正是鲁迅开始被神化的时候。自此,知识人从延安时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脱裤子、割尾巴”,再到“文革”时的全面被打入另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终于一步步实现了毛在1925年就提出的设想。而大多数知识人也在不断的身份认同过程中,通过自我认识而彻底丧失了自我,沦为福柯所说的“听话的身体”。
1949年以后,鲁迅完全被塑造成神,成为权力/知识机制的一个符号,而多数知识人却受尽凌辱。大惑不解的他们心头遂产生了一个著名的现代之谜: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近年透露的一条材料终于揭开了谜底。1957年毛泽东曾针对罗稷南的这个问题,郑重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毛泽东深知,鲁迅的精神实质就是反任何权力。鲁迅骨头最硬,这一对鲁迅最准确的赞誉出自毛泽东,而不是知识人,并非无因。这两个未曾谋面的相知,经过数次的互相打量、观察和对话,早已看透了对方。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不同,更是牧人与离群者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