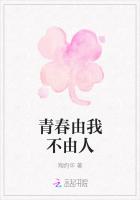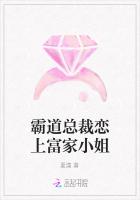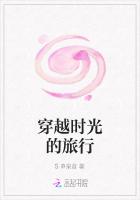张问陶与崔旭既是师生又为诗友,师生二人常常对烛而坐,谈诗论艺,好不惬意。本诗即为师生二人谈诗论诗之佳作。张问陶在诗中十分真诚地提出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即“诗到真空悟境多”。此处是以禅喻诗。虚空无常既是诗人之真性,也是自然界万物之真性。由于在澄明无蔽的境界中,人返回到了本真,获得了清净无染的自性,把握到了生命。自然万物也就朗现出它们本来生机活泼、自由兴作的飞跃生命。在已复其真的诗人那里,即自然万物之真,便见自然万物之性。正如王维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87“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88只有在“人闲”、“夜静”、“林空”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也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由于心境之特别虚静,诗人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禅与诗用心所在虽有不同,但求悟是相同的,均须了悟,不悟不进。所谓至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时。诗歌创作必须具有真实的“性灵”和意境,如此,方能在诗歌创作中,左右逢源,开拓出广阔的局面。张问陶对于崔旭诗的意境曾有褒扬,言其“诗境已稳成极矣,此后惟须练识,识见一高,则笔墨羽化,才是真通人。”89门生崔旭的才情为船山所赏。崔旭在《念堂诗话》中云:“庚申乡试,旭出张船山夫子房,辛酉春闱前,以诗谒见,展阅数首,遂纳于怀,喜曰:‘吾又得一诗友。’题赠二律,云‘直胜崔黄叶’,90书卷首语曰:‘此老船之崔不雕也。’传示同好吴谷人、赵味辛、戴金溪、王熙甫诸先生,各有题赠。后命旭题《船山诗草》,又云:‘呼我崔黄叶。’即为此也。”崔旭所为诗“一主于严,思深而律细,无嚣凌洿夸之习。”91崔晓林与梅成栋尝同佐陶梁纂《国朝畿辅诗钞》六十卷,陶梁采二人诗合刊之,序云:晓林之诗“醇古淡泊,味之弥永,譬之精金百炼,宝光内含。”92船山认为自己与崔旭相比,不过是虚得浮名,于是诚恳地说:“爱君饥走尚清歌”。船山认为佳句是从“饥走”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真实的感受而得来的,也是从自已切身的体验及具体的事实中得出的。宋时史达祖有“烟蓑散响惊诗思,还被乱鸥飞去,秀句难续”93之词,言烟蓑可引惊诗思。张问陶的“虚堂静比舟藏壑,俗雾纷如虎渡河。风雨打窗相对久,关情难忘旧烟蓑。”赞扬念堂诗虽以“雾霭”、“烟蓑”等这类司空见见惯的寻常物入诗,却能达猛虎渡河之效。对照崔旭的诗歌创作,船山师所评可谓中的。《津门百咏》是崔旭以天津民风食俗为题写成的,他在《津门百咏》中这样吟咏津门银鱼94:“一湾卫水好家居,出网冰鲜玉不如。正是雪寒霜冻候,晶盘新味荐银鱼。”诗中用了“冰鲜”、“玉”、“新”、“雪寒霜冻”几词,勾勒出冬初时节,银鱼上市,成为津人盘中的一道风景。天津泥塑也早已有名。崔旭有诗“泥人昔说漉州好,可似天津样样工”,赞天津泥塑做工考究。天津的造酒业亦甚为发达95。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大直沽除了酿造高粱干酒外,还有玫瑰酒、“五加皮”等色酒。这三大名酒,远近闻名,崔旭在《津门百咏》中咏道:“名酒同称大直沽,香如琥珀白如酥。”琥珀酒香醇醉人,民间有“十年琥珀香,一次醉死人”之说。崔旭用琥珀说明大直沽酒的酒香四溢,又以“酥”形容酒的色泽,让人垂涎欲滴。用语简单却鲜活生动,勾起人们开怀痛饮的欲望,大有不喝不快,一醉方休的感觉。
《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96
少作重翻只汗颜,此中我我却相关。
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删诗
一字真如博浪椎,僧敲毕竟异僧推。
灵针未乞天孙巧,仔细云衣漫改为。改诗
欲写天真得句迟,我心何必妄言之。
眼前风景床头笔,境过终难补旧诗。补诗
改罢长吟未忍抛,乌焉悔命俗胥钞。
六州难铸他人错,何苦庖丁不治庖。钞诗
说法何妨偶见身,须眉好在是他人。
浮云已过休重问,只当空花堕转轮。代作
新奇无力斗诗豪,几度雷同韵始牢。
香草美人三致意,苦心安敢望《离骚》。复语
无功岁月强编年,旧梦如云尚了然。
谩语谰言聊自赏,快心原不在流传。编年
南船北马意踟蹰,到处应留记事珠。
也拟一年分一集,浪游踪迹恐模糊。分集
秉烛新装十卷诗,针光线影夜参差。
一函故纸难留赠,终望人知胜我知。装诗
年来我渐悔雕虫,才劳精神气转雄。
招亦不来麾不去,有声终夜在空中。祭诗
《船山诗草》中有许多以“月日”为题写作的诗歌。《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即为翻检这类诗歌后有感而作。自题中分别以删诗、改诗、补诗、钞诗、代作、复语、编年、分集、装诗、祭诗为旨,言及诗歌创作的诸多方面。对于诗歌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三、四、六几首中。
少作重翻只汗颜,此中我我却相关。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
托尔斯泰说:“没有任何天才的增添可以象删节那样使作品更加完美。”97张问陶一生诗歌创作逾4000,但传世仅3000余首,其中许多都是经他亲手删定的。《自题十绝句》开篇即谈删诗的原则。张问陶仍然坚持诗歌创作应该是诗人自我性情的真实表露,步人后尘者的拾人牙慧之作,不是自我感情的自然流露,应该汗颜。诚然,诗是真实性情的呈现,诗人在吟咏之际,内心的性情随之毫无隐藏地表现出来。但是并非有真情境就是好诗,真正的好诗还要具备“善”的要素。孟郊在《懊恼》一诗里,愤激地说:“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所谓恶诗,或谲怪,或俚俗。如果是恶诗,尽管其情境真实,也要忍痛割爱,一律删除。“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表现了张问陶论诗重情之真,也重情之善和美,是对袁枚尤重情之真的补救。
一字真如博浪椎,僧敲毕竟异僧推。灵针未乞天孙巧,仔细云衣漫改为。
贾岛和韩愈改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改为:敲)月下门”,成就了“推敲”佳话。遣词造句细推敲,能使诗歌生辉增彩。张问陶反对镂金错彩,对语言粗糙同样持否定态度。“潦草诗多句易忘”,98无疑是对随便堆砌词语的批评。诗歌是高度凝练的文字,悉心推敲,仔细斟酌,诗歌的语言才能更为精密,表达更为确切。张问陶不反对语言的推敲和锤炼,“僧敲毕竟异僧推”,赞贾岛推敲之功。做诗无定法,改诗亦然。如同赵翼《删改旧诗作》所言:“笑同古炼师,烧丹穷昏昼。一火又一火,层层去粗垢。及夫将烧成,所成仅如豆。未知此豆许,果否得长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作家最大的本领是善于删改。”女娲补天,引七星针将根根丝锦缝合成七彩云衣,而在霓裳云衣的精心缝制过程中,改制拼合是不可缺少的工序。张问陶以此强调锤炼的重要性。
欲写天真得句迟,我心何必妄言之。眼前风景床头笔,境过终难补旧诗。
诗是从心中流淌出来的。诗歌创作要真实可靠,反对妄言绮语,排斥夸张虚饰。张问陶常以“天真”论诗,“每从游戏得天真”,99“闲中戏墨多天真”。100此“天真”近于李贽的“童真”,是一种原生态的本真。那么,天真之句何处来?从张问陶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驴背诗情古,天涯破锦囊。”101“天海诗情驴背得,关山青色雨中来。”102作诗是触目即景,即景会心,但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03。虽然青山依旧在,却无奈长恨春寻无觅处。原来耳闻目见、心有所感而发于章句的一切,有如滚滚长江东逝水。即令当时所作确有缺憾,以后勉强增补,亦如烹茶之“调和水”,104难保其原汁原味。正如清李福《重阳日风雨》所言:“重阳七字足千古,断句不劳后人补。”105
改罢长吟未忍抛,乌焉悔命俗胥钞。六州难铸他人错,何苦庖丁不治庖。
诗歌毕竟是自己辛苦写就的,一俟修改完稿,要抛却总有些于心不忍。依依不舍之下,交由胥吏誊录钞写,留待保存。古代胥吏司钞诗之职,106对此张问陶是持有异议的。因为俗吏本不懂诗,交由钞诗,则难免以讹传讹,甚至“乌焉成马”107。诗人慨叹:庖丁尚且不治庖,何苦要尸祝越俎代庖呢。六州铸错,108与他人何干!诗人写诗后由俗胥代而钞之,实乃失职之举。这应该是张问陶提出的批评或自警。笔者认为,此处有讨论文学鉴赏中的共鸣问题的迹象,但受论诗诗体式所限,但凭此无从得出确论。
新奇无力斗诗豪,几度雷同韵始牢。香草美人三致意,苦心安敢望《离骚》。
元和时期,诗歌又出现了第二次高潮,以韩愈和白居易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及元白诗派,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窄天地。在这两大派以外,自树一帜的有柳宗元和刘禹锡。刘梦得在诗歌创作上,注意不断改革创新,曾把古代乐府诗《杨柳枝》翻改成类似“七绝”的《杨柳枝词》,在当时有“诗豪”之目。109“诗豪”之“豪”,足见刘禹锡的风格与地位。《离骚》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的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离骚》香草美人的象征体系、回环往复“三致意”的抒情方式,110已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艺术传统,令他人苦心经营也难望其项背。刘禹锡的创新精神和屈原《离骚》中深深的忧愤情思,分别与张问陶主创新、重真情的论诗主张相契,故予以高度评价。
在接下来的几首诗里,“南船北马意踟蹰,到处应留记事珠。”说明了诗歌是诗人生活踪迹的真实记录。“漫语谰言聊自赏,快心原不在流传。”指出了真正的诗人,作诗只为怡情养志之需,并不在乎流传与否。张问陶一生南船北马,足迹半人寰,“逢山记一诗”111。写诗几乎是张问陶生活的全部,“君我游尘海,除诗百不能。”112吟诗作唱几乎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
“少作重翻只汗颜,此中我我却相关。”“欲写天真得句迟,我心何必妄言之。”及“眼前风景床头笔,境过终难补旧诗。”“南船北马意踟蹰,到处应留记事珠。”都是说要根据自己的认识体会,自己的生活感受,抒发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张问陶的《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题图琴隖论诗图》、《题朱少仙同年诗题后》、《冬夜饮酒偶然作》以及《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等一系列论诗诗、论画诗无不贯穿着其“性灵说”的诗学观。
论诗组诗之外,张问陶尚有大量的论诗单句散见于《船山诗草》中,构成了其诗歌理论不可分割的整体,将在本文第四章予以分析。
1、《古诗源》卷十二。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95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