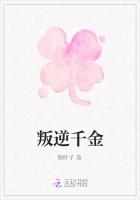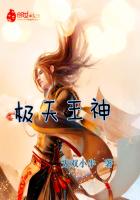张问陶对诗歌理论的阐述,虽然有不少是散见于零星的诗句中,但毕竟尚有《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题屠琴隖论诗图》等十几首论诗组诗集中反映其诗学观点。而论历代作家和作品,则既没有像杜甫、元遗山那样以一组论诗诗将历代作家择要而评,也没有像他自己在阐述诗歌理论时那样采用论诗组诗与零星诗句相结合的方式。虽然也有论诗诗专论杜甫、苏轼等诗人,但最常用的方式是在感怀、偶作、题赠、酬唱诗中兼及对诗人诗作的品鉴。要在船山存世的三千余首诗歌中将其对历代作家的批评一一检出,工作之繁琐不言而喻。这大概也是学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进行研究的原因之一。袁枚的性灵说存在着创作实绩在理论之下的客观不足,而张问陶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他的“性灵”说是长期诗歌创作实践的结晶,其独抒性灵的诗学思想又指导着他的诗歌创作,对历代作家的批评就很好地贯彻了他的“性灵”说主张。张问陶的性灵说,对当时弥漫于诗坛的各种不正之风都进行了批评,同时又汲取了他们的有益的素养,使他的“性灵”说合而不流,独立不倚,自有新意,又更加成熟和全面,这点从他对历代作家的批评中可略见一斑。因而研究他对历代作家的批评,有助于全面、客观地把握其“性灵”说,其重要性和价值并不逊于他对诗歌理论的阐述。张问陶对历代作家的批评,上起屈原,下迄清代嘉庆诗坛诗人,人数逾千,笔者在全面梳理了《船山诗草》后,惟择其尤要者而论。
张问陶论先秦、两汉作家
张问陶论先秦两汉作家十位,分别为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汉初杰出的散文家、辞赋家贾谊,两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杨雄、枚乘、邹阳,诗人苏武、李陵,辞赋家诗人张衡。张问陶对先秦两汉作家的评价有轻重之分。例如他对屈原、贾谊、苏武、李陵、张衡的评价,多结合他们的生平遭际而论,或赞扬其人格,或哀伤其遭遇,进而到对作品的批评,张问陶对他们的人品和作品都评价极高。“不得志”为张问陶和所论诗人之间的理解构建了桥梁,心灵上的趋同使他找到了“借他人文字,浇己之块垒”的由起。从感叹他们的悲惨遭遇来反照自己的命运多舛,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对杨雄、枚乘、邹阳等,则颇有微词,批评他们词赋背离了经世致用的原则。对用笔最多的宋玉和司马相如二人,则采用二分法,结合自己的性灵说思想,较为客观地论其优长和不足。
写遍兰枝与竹枝,《楚骚》哀怨有微词。
情含楚雨风流苦,怨写湘篁涕泪多。
(《春日感怀》诗草卷二)
(论屈原)
宋玉有怀仍忆楚。
(《独树店》诗草卷二)
泬寥千古赋悲哉,《九辩》空怜宋玉才。
(《上水遣怀》诗草补遗卷一)
江树春心伤宋玉。
(《春日有感》诗草补遗卷一)
不见宋玉《高唐赋》最工,巫山可有行云女。
(《青神舟中不得见峨眉山与亥白兄饮酒排闷》诗草卷八)
神女佐禹成大功,功与同律庚辰同。
不知宋玉是何物?敢造梦呓汙天宫!
(《壬子除夕与亥白兄神女庙祭诗作》诗草卷八)
细酌宜城酒,深怜宋玉才。
朝云词笔秀,落叶赋心哀。
文藻开秋气,江山哭楚材。
(《宜城》诗草补遗卷三)
(以上论宋玉)
贾生书可读,孤抱向谁论。
(《移居》诗草补遗卷一)
贾生吊古年殊少。
(《过湘水》诗草补遗卷一)
举世不逢孙伯乐,一生惟哭贾长沙。
(《春日感怀》诗草卷二)
西京人物多儒雅,经世终须让贾生。
(《怀古偶然作》诗草卷十四)
(以上论贾谊)
有才无抱负,我又薄相如。
(《丙辰冬日饮酒作》诗草卷十三)
击剑弹琴兴有余,萧萧风雨茂陵居。
君王只取凌云赋,不爱长杨《谏猎书》
(《读司马相如传》诗草补遗卷一)
才人多事马相如。
(《感事》诗草卷二十)
营求不事如廉贾,潦倒相如有病妻。
(《张家湾晓发》诗草补遗卷二)
相如多病更游梁。
(《独树店》诗草卷二)
莫将词赋求知遇,往日相如已倦游。
(《开封客夜感事》诗草卷二)
蜀人辞赋愧相如。
(《乞王伯雨竹醉小印》诗草补遗卷一)
珍重相如《谕蜀文》。
(《丙辰初冬乡思》诗草补遗卷五)
高车驷马惊乡里,只觉相如是俗人。
(《题复圆画册》诗草卷十七)
肯学相如西去日,高车驷马吓乡邻。
(《二月二十九日出都述怀》诗草卷六)
相如杂傭保,惭负《子虚》名。
(《移居》诗草补遗卷一)
(以上论司马相如)
扬马枚邹总盛名,鸿文无用即虚声。
(《怀古偶然作》诗草卷十四)
三月梁园淡似秋,可怜零落到枚邹。
(《开封客夜感事》诗草卷二)
(以上论扬雄、枚乘、邹阳、司马相如)
诗怜平子最苍凉。
(《早秋漫兴》诗草卷四)
(论张衡)
丁年诗思满河梁,秃节持归两鬓霜。
结发去帷儿塞北,墓门当日已荒凉。
穷兵封尽汉功臣,武帝开边气未驯。
百万平民都战死,赚回一个牧羊人。
(《苏武墓》补遗卷三)
(论苏武、李陵)
张问陶在当时有才子之目,作为相门之后,他立志“相业史重编”,十五岁时处次存诗,名之曰《壮志》,决心“三十立功名”,无奈一生不为重用。他有大量的言志诗,便是借自然界生物之有才不用来抒发自己有才难展之愁绪。如《四方铺》1诗云:“楚楚可怜松树子,有才无用只风尘。”借松树子的沦落风尘喻自己大才不用却“敝车羸马向风尘”2。他的《马耕》3诗借中原牛小用马助耕,路人怜惜骅骝流血不流汗,诗人则笑路人少见多怪,暗喻现实中的自己也如同骅骝一样大材小用。因为自己壮志难酬,张问陶在对历代作家进行批评时,往往多选取怀才不遇者或志向高洁之士而论。例如屈原就是其中的代表。
屈原志向高洁,其崇高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屈原在《离骚》里常以“兰”象征具有高尚品格的君子。如:“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佇”;“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张问陶对兰也情有独钟,作有咏《兰》诗二首,其二有“可怜百种沿江草,不及幽兰一箭香”之句,是对兰不同凡俗的赞扬,也是其自身清高人品的写照。他说屈原“写遍兰枝与竹枝”,既赞诗又赞人。对于《离骚》的创作缘由,古今各家说法不一。以哀怨说影响较大。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并加以发挥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李白《古风》亦云“哀怨起骚人”。张问陶“《楚骚》哀怨有微词”当承哀怨说而来。张问陶诗主性灵,其《蟋蟀吟》、《秋燕飞》4二首序揭示了“诗发乎情”的本质。云:“诗发乎情,情触于遇,哀乐殊致,比兴生焉。其人莫不有如泣如诉之情,抑郁于中而无端以自见。故一旦触于所遇,形诸吟咏,遂不觉其宛转附物,怊怅而切情焉。”张问陶重视性情之“真”,认为优秀的诗歌是表现真性情的,屈原诗歌是其悲剧性情的自然发抒。“诗人原是有情人”5,屈原一生对故国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离骚》成为千古之绝唱,可以用张问陶诗句“故国情难尽,奇诗性所耽”6来解释。一部《离骚》,寄托了屈原对自己个人身世的哀怨之情和对楚国现实政治的怨愤之情,是“好诗不过近人情”的佳作7。
“才气”是诗文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与生俱来的天分,是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素质。诗主“性灵”者大都重视诗人之“才”。尽管袁枚不否认诗歌创作中学识的作用,却更看重天分,甚至极端地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张问陶也看重天分,他说“才小诗多复”8,“才高逸气真”,意谓天分高的作家创作自具个性。张问陶可谓天生的诗人,他自己也有“除诗百不能”9之句,三十岁生日时作诗云:“未了一生诗酒债,匆匆无暇作神仙”10。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赞誉他“殿前指使,将门子弟。可惜宝刀,用杀牛二。”即谓其大才而小用。张问陶以其奇才,三十几年里创作了四千余首诗歌,删存传世者逾三千。
船山才高孤拔,对宋玉的才华却十分欣赏。其“伤宋玉”、“深怜宋玉才”、“空怜宋玉才”等句,对宋玉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怀才不遇而流离失所的悲哀处境,深表同情。《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他把个人的身世之悲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不幸遭遇。鲁迅《汉文学史纲》谓:“《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张问陶的《读〈桃花扇〉传奇偶题十绝句》其三,借咏史可法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以身殉职,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兴亡感叹与爱国之情。云:“生遇群奸死报君,裹尸惟藉一江云,梅花岭上衣冠冷,凄绝前朝阁部坟。”故而“《九辩》空怜宋玉才”,也是船山自己怀才不遇的自况。
《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句,还刻画了秋景的种种凄凉寂寞,并将其和自身的惆怅失意、冷落孤独之情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张问陶评宋玉“文藻开秋气”,即赞其开辟了文学创作中悲秋的主题,同时也体现了张问陶以“气”论诗的特点11。船山以“情”论诗,也以“气”论诗。其《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12,把“情”与“气”并举,认为诗歌创作中“气”与“情”缺一不可。诗人作诗要凭真气,“偶凭真气作真诗,无端落纸成诗文”13。有真气则见诗人之真性情,诗人有真气,落纸成真诗。而秋气是随心性的,愁字心上秋。心中有愁情,文中有秋气。宋玉心中有忧国之情,诉诸笔端,文中便有“秋气”。
张问陶主张以“常语”入诗,如他赞姚元之“奇篇能磊落,淡语亦丰神”14。但对于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而锤炼语言也不排斥,其“僧敲尤恐胜僧推”15,即肯定了贾岛的推敲之功。《高唐赋》、《神女赋》以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委婉曲折的文笔,状貌传神,肆意铺陈,曲终奏雅,略陈讽谏,开汉大赋之先河,体现了宋玉的才气和性灵。“泬寥千古赋悲哉”、“落叶赋心哀”,张问陶指出了宋玉赋的悲愤深沉的风格特征,又赞其用笔精致,曰:“朝云词笔秀”,“《高唐赋》最工”。但是对《神女赋》的内容张问陶则予以斥责。张问陶在坚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原则之下,不偏废儒家之所谓“性”。其论诗重情真,也重情之善之美。他有不少描写儿女私情的诗歌,虽然是对闺房之乐的表现,却都写得至纯至洁,格调很高。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体态闲雅,含情脉脉,来去恍惚,《神女赋》为历来论者所赞许。但船山认为宋玉《神女赋》臆造了楚襄王梦遇巫山神女千古风流之事,这样的作品并不严肃,失其雅正,斥为“敢作妄语汙天宫”。船山对宋玉之作取二分法,实事求是而自具新见,有出人意表之处。
贾谊是古代文人中怀才不遇者的一个典型。文帝虽赞赏贾谊的博学,但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是把贾谊当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饱学多才的贾谊空有抱负,不得施展,其生平遭际让张问陶也心生同感,故赋诗《过湘水》对贾谊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贾生吊古年殊少”16,是对年轻的贾谊无辜遭贬的深切同情。感时伤事,慨叹“举世不逢孙伯乐,一生惟哭贾长沙。”“贾生书可读,孤抱向谁论”,这里不仅是痛惜贾生的不平遭遇,也是张问陶苦不得志,怀才不遇的自况。是借贾谊的不幸身世来抒发自己有志难展的愤慨之情。贾谊的悲剧,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自曹丕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文学和文学创作者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抒情性和“文以载道”的社会功用两者之间的争论、尝试和抉择。清初顾炎武注重经世致用,开清代汉学之风。但到了沈德潜则过于强调文学干预政治的作用,流入诗教论。袁枚倡性灵说以救弊,却又重在追求表现个人性情感受,而流入浮滑、空疏。性灵派殿军张问陶认为文学的本质是抒情,但也不应放弃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他提出“一代真诗笔,空言定扫除”17,“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18,主张文学的审美功能,又重视文学要关注现实人生。贾谊多次上疏,议论时政。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其关心时政,积极用世的文艺观与张问陶强调文学要关注现实相凑,故张问陶赞云:“西京人物多儒雅,经世终须让贾生。”
汉赋被称为一代文学之盛,“汉赋四大家”及汉赋名家枚乘、邹阳等人,以其创作使得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汉大赋气势宏巨,结构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侈丽宏衍,追求形式美。对汉赋重形式的倾向,王充作了尖锐的批判。在《谴告》中,王充指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欲讽反劝”的事实,认为他们的作品文辞宏丽、意趣深博,“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补于世用,“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19也不能算是好作品。王充指出扬雄、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汉赋大家,虽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在思想方面其实盛名难符。张问陶强调文章经世致用,认为汉大赋虽极尽铺张扬厉,但缺乏思想而无益于人心世道,因此作出了“鸿文无用即虚声”的严肃批评。
张问陶的言志诗多有寄托,往往借物喻志,以表忧国忧民之情。张衡是在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并且取得重要成就。其《四愁诗》有政治上的寄托,20得《离骚》之神韵。张问陶引为“同调”,赞其诗歌具苍凉之美而感动人心,故有“诗怜平子最苍凉”之叹。
司马相如是船山的蜀中同乡21,石韫玉《刻船山诗草成书后》首句“文园遗稿叹丛残”22,把船山比作相如。船山论相如这位蜀中同乡时采取了二点论,既欣赏其才气,又批评其俗气。
船山主张诗歌创新,说“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李杜张王虽为诗国圣手,但我仍是我,何必刻画古人面目?船山主张诗歌的创新,故于相如情有独钟。相如凭着雄放的气魄和富赡的才华,勇于创新,锐意开拓,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高度评价了司马相如对汉赋变体创新的贡献,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越汉代”23。两汉时期巴蜀汉赋出现了“文章冠天下”的王褒、严君平和扬雄,深得赞誉。船山却认为相如辞赋在当时独标一世,无人企及,故评云“蜀人辞赋愧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