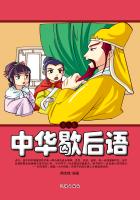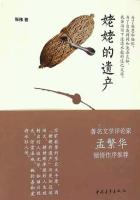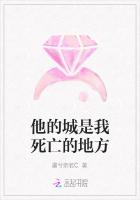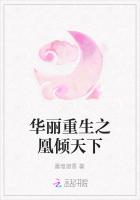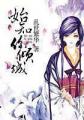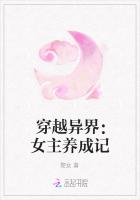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24、《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谕巴蜀檄》是汉武帝通西南夷时,派司马相如先后两次赴巴蜀,为安抚巴蜀百姓所作,收到良好的效果。后又写《难蜀父老》,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迅速达到了安定人心的目的。家园故国是张问陶魂牵梦绕的地方,嘉庆元年正月爆发的白莲教起义的烽火,于初冬燃至大巴山、终南山,清政府实行残酷的镇压。张问陶《岁暮杂感》诗“马革总疑非上策,重臣何用死沙场”,对清政府的镇压政策表示不满。他更担心战区蜀中父老的安危,将思乡忧虑之情化作《丙辰初冬乡思》诗,其中“珍重相如《谕蜀文》”一句寓意深刻,希望清政府能从安定大局的长远考虑,借鉴司马相如安抚巴蜀百姓之举,使人民安居乐业。此为张问陶民本思想的表现。
以文求知遇,是古代文人中颇为盛行的做法。张问陶认为诗歌是自我性情的真实流露,诗人摒弃杂念,方能得到真诗。因“尘缘逐处损天真”25,故不赞成相如以词赋26求知遇的俗气,予以警醒:“莫将词赋求知遇”。“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被传为千秋佳话。杜甫《醉时歌》赞曰:“相如逸才亲涤器”。李商隐有“君到临邛问酒垆”之句。尽管与相如相比,船山生计也好不到哪里:“恒数日不举火”、冬日无衣御寒,出门尝衣亥白兄之裘,乃其生活窘迫的真实写照。但张问陶毕竟是相门之后,贫困一生却不失清高与雅气。他难以认可相如的当垆典酒自谋衣食,哀叹“逸才”相如竟至沦落到身穿酒保之服,涤器市中。想象相如贫穷愁苦之状,黯然神伤中也未忘责其有愧于《子虚》赋作者之盛名。船山一生保持恬淡的心怀和潇洒、达观的人生态度,认为“身外浮名画足蛇”,故对相如的俗气多有微词。船山从京师回乡省亲之日,曾述怀一首,“肯学相如西去日,高车驷马吓乡邻”27?对相如表示批评。船山羡慕山中老猿的无拘无束,为此自号“蜀中老猿”,他十五岁立下“三十立功名”的远大抱负之时,也立下了“四十退山谷”的功成身退的志向。因而相如的“高车驷马惊乡里”,在船山眼里“只觉相如是俗人”28。
司马相如逸才超妙,张问陶以“才人”誉之。偏偏相如命运多舛,一生多病、多事,所谓“天忌才名罚肯轻”?29船山怜惜“相如多病更游梁”,伤叹“才人多事马相如”。船山曾读司马相如传,对相如壮志难酬,不为重用深表同情,指责武帝“君王只取凌云赋,不爱长楊《谏猎书》”。30
苏武,字子卿,《文选》载有《苏子卿诗四首》。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扣,匈奴多方诱降未遂,于是将他迁至北海边牧羊。《汉书·苏武传》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苏武牧羊的故事,传诵千古,成为坚贞不屈民族气节的文化象征。张问陶钦羡之余,作《苏武墓》以颂,“穷兵封尽汉功臣,武帝开边气未驯”,同时又批判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置民生于不顾,表现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情。“丁年诗思满河梁”,“河梁”指收在《文选》中的“苏李河梁生别诗”。今知其伪托,但已在古代发生很大的影响。其中有“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句。李陵是武将,而且是迫不得已屈降匈奴的“失节英雄”。与苏武相比,李陵无法抹去自惭形秽的耻辱之感,但他数奇不遇而终致屈降的人生悲剧,不仅使后代文人为之扼腕叹息,而且在司马迁写《史记》与班固修《汉书》时,就已经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张问陶至苏武墓,祭奠苏武十九年不屈,决不背叛祖国的气节。通过苏武壮年出使匈奴,归来已两鬓霜白,对武帝开边予以鞭挞。也没有忘记将关注的目光投到慷慨悲歌的李陵身上,在无形之中丰富发展了李陵的形象,使之具有若干文人气味了。对李陵的欷歔感叹,体现了张问陶悲天悯人之情怀。
屈原、宋玉、司马相如、贾谊、张衡,都是怀才不遇、志不得伸、孤抱难开者。论者多赋诗表达同情。如李白《太白楼》“贾生夭折平子愁”。张问陶空有一腔报国心,而壮志难酬的遭遇,与他们极为相似,所以,对他们寄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借屈原、宋玉、司马相如、贾谊的不幸命运和悲情愁绪,抒发自己的愁慨。肃然起敬于他们的才气和清高,而对其优秀的文学创作也加以推崇。
张问陶论魏晋六朝作家
张问陶率性自然,恃才傲物,其放荡不羁颇具魏晋风范。《船山诗草》涉及魏晋六朝人物130余人,引用人物佚事不下300个,大多见于《世说新语》和《晋书》。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竹林名士阮籍和东晋名相、文学家谢安,分别达17次和16之多,可见船山是把二人当作自己的楷模的。画家顾恺之、名僧支遁、军事家羊祜,各引15次,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崇敬之情。著名诗人陆机、陆云两兄弟,竹林名士王戎,东晋名士王子猷四人,各引11次,以示敬慕。名相王导、书圣王羲之、名士王恭,各引10次,自然也是船山希慕的人物。竹林名士刘伶、嵇康、山涛,东晋女诗人谢道韫,大诗人陶潜以及与其齐名的东晋诗人谢灵运,都多次出现在张问陶笔下,足见诗人对他们的尊重。仅出现过一次的魏晋人物还有很多。《船山诗草》歌吟魏晋人物,大多称赞他们傲世不俗或返归自然、崇尚精神自由的名士气质。如《怀古偶然作》赞王猛曰:“意气我推王景略”31。但他真正对魏晋文人及其创作进行评论的,是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陶渊明、谢脁,以及东晋女诗人谢道韫及庾信等人。
才如王粲奚论貌,奇似刘叉尚苦贫。
(《莲花寺宴上赠陈若畴》诗草补遗卷四)
流寓悲王粲。
(《送周伊人归豫章》诗草补遗卷一)
邺下才人健,西苑逸兴豪。
独怜公宴日,王粲亦青袍。
(《彰德》诗草卷二)
应刘七子半沉沦
(《端阳相州道中》诗草补遗卷二)
偶然书记学陈琳
(《早秋漫兴》诗草卷四)
(以上评建安七子)
自我属有生,寿夭何可必。
举杯祝长庚,聊以永今日。
故人喜无多,数止竹林七。
浮云亦偶合,良会尚真率。
同气爱已深,忘形情愈密。
披衣不巾袜,随意具梨栗。
开轩来清风,炎威忽如失。
青山归未能,尘网事难毕。
此地即醉乡,居之安且吉。
(《丙辰五月生日与亥白兄分韵得必字》诗草卷十三)
嵇阮多忧愤,山王少性灵。
妇言犹在耳,长醉不须醒。
(《刘伶墓》诗草补遗卷六)
樽酒难携向夜台,羊车荷锸亦堪哀。
人间到处皆宜醉,况是刘伶墓下来。
(《刘伶墓》诗草补遗卷一)
(以上评竹林七贤)
蓟门秋色澹幽州,鹤唳华亭忆首丘。
(《岁暮怀人作论诗绝句》诗草补遗卷一)
出山坡颍科同举,入洛机云屋两头。
(《武连月夜不寐寄怀》诗草卷五)
并马三千叠,联吟屋两头。
(《寄亥白》诗草卷六)
(以上评陆机、陆云)
荒鸡午夜起刘琨。(《春日有感》诗草补遗卷一)
拊床忽忆刘琨语,莫道荒鸡是恶声。(《重有感》诗草卷二)
(评刘琨)
林下尤逢谢女才。
(《妇翁林西崖先生作砚缘诗四首誌之》诗草卷四)
闺中玉暎张元妹,林下风清道韫诗。
(《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诗草卷五)
(以上评谢道韫)
好挽渊明共写真。
(《思误书图为未谷题》诗草卷十三)
(评陶渊明)
满眼青山小谢诗。
(《正月二十三日分韵得柳字》诗草补遗卷一)
(评谢脁)
久矣文章悲庾信。
(《早秋漫兴》诗草卷四)
一树枯槐怜庾信,十年秋柳泣桓温。
(《汉阳客舍题壁》诗草卷二)
文章悲庾信,嗤点亦流传。
(《枝江舟中与亥白饮酒作》诗草卷八)
一线枝江月,千年庾信居。
(《枝江野泊》诗草卷八)
记取临江宅,相留庾信传。
(《展叔先生移居》诗草补遗卷一)
势接海门秋,江声拥户流。
诛茅来庾信,蓐食去韩侯。
(《移居》诗草补遗卷一)
(以上评庾信)
汉末至魏初建安时期,当时的著名文人除建安七子外,32还有蔡琰、邯郸淳、杨修、丁仪、繁钦、路粹、荀纬、吴质等人,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人集团。由于聚集于魏都邺下(今河北临漳县),故又称“邺下集团”。他们和三曹在文学上是诗友,政治上是其宾幕。该文人群体在创作上反映现实,抒写自我怀抱,情文并茂,形成了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钟嵘《诗品》说建安文学“干之以风力”,能令“闻之者动心”。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评当时的风格是“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张问陶提倡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但爱“沉着痛快”甚于“优游不迫”。邺下文人集团诗歌内容充实,风格劲健,以“慷慨悲凉”为主要美学特征,张问陶赞云:“邺下才人健”。张问陶后期诗风与建安时期雄健之气有相通之处。曹操诗苍劲雄浑,沈德潜曾言其“时露霸气”。33刘师培也以“霸”气论船山创作。其《题张船山南台寺饮酒图》云:“遂宁公子文章伯,34壮年奇气横干镆。”
性灵派重诗才,张问陶也多次举出有诗才者以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才气绝伦35,名重千古,刘勰对其诗才大加赞扬。《文心雕龙·才略》篇赞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体性》篇又评云:“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评其:“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道出了王粲独标一世,乃诗才使之然。贵州人陈若畴是张问陶的诗友,其才气横溢,船山以“才如王粲”相评。但王粲有才无貌,因貌丑而被刘表所轻,表女别嫁其兄,故船山有“奚论貌”之叹。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36,促使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王粲尤具代表性。出身名门,偏偏生逢乱世,加之遭乱流寓的遭遇,王粲因此感物兴怀、忧世悲己,所以“自伤”便成了他的主要感情特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钟嵘《诗品》评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张问陶早期的《蟋蟀吟·秋燕飞》序云:“诗发乎情,情触于遇,哀乐殊致,比兴生焉”,指出了诗歌是诗人自我感情的真实表露,诗人的生活感受直接影响诗歌的创作,“流寓悲王粲”,道出了王粲诗歌悲慨的症结。
王粲的故乡,战国时曾为楚地。建安前期,他因避北方战乱,流寓荆州,经历了15年的困苦流离。其代表作《登楼赋》和《七哀诗》,前者为荆州登麦城城楼所作,后者则写于奔荆州的途中。《登楼赋》抒写怀乡之情与怀才不遇的沉痛,感情真挚感人,是古代抒情小赋的名篇,前人因此给予高度评价,视它为魏晋辞赋的登峰造极之作。《七哀诗》更是将怀乡之思、伤时之哀抒发得淋漓尽致。其二开篇即云:“荆蛮非吾乡,何为久滞留?方舟溯大江,日暮愁吾心”。张问陶曾寓居湖北汉阳八年。期间,全家困苦异常,“八口饥寒,至一日一粥且不继”。张问陶身为相门之后,同声同气的感受,当然更能体会出身名门的王粲十五年的羁旅之情、漂泊之苦。在送周东屏出任川陕之任时,喟然叹道:“流寓悲王粲”。虽然悲苦之情吐露得十分委婉,但自我的怅悒之感仍难以掩饰。《七哀诗》还描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借景抒情,托事达意,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张问陶的《宝鸡题壁》组诗描写了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后生灵涂炭的惨景,表达了与王粲《七哀诗》大体相同的思想感情。
建安七子生当天下分崩之际,前期处在汉末动乱中,目睹生民忧患,个人生活也颠渍不安。后期虽仕途顺利,但不幸建安二十二年,疾疫暴发,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七子中堕入不幸境地者过半。七子中应旸、刘桢才华纵横,尤其刘桢性卓傲倔强,诗直抒胸臆,不事雕琢,风格遒劲,慷慨磊落。曹丕《与吴质书》说他的文章“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妙绝时人”。《诗品》称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而评为上品。应刘二人的才华和磊落诗风都与张问陶相合,故对其不幸遭遇深表哀叹:“应刘七子半沉沦”。
陈琳、阮瑀擅章表书记,而琳尤健爽。曹丕《典论·论文》称:“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言陈琳、阮禹章表卓然特出,成为一代隽杰。《文心雕龙·章表》篇亦云:“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谓陈琳、阮瑀特以符檄标美名世。张问陶主张诗歌创作要创新,“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却并非简单地否定古人,要求学古而不泥古,“好古不泥真通人”。37“偶然书记学陈琳”,就是建议后人若写章表体,不妨向陈琳学习。
魏废帝曹芳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藐视礼法,言行怪异,狂放不羁。常集于竹林之下,相会悠游,酣歌纵酒,吟诗作赋。《丙辰五月生日与亥白兄分韵得必字》诗专论竹林七贤,张问陶以“同气”指出了竹林七贤因为性气相投,结为好友。“尚真率”、“忘形”、“披衣不巾袜,随意具梨栗”等,点出了七贤不拘礼法,生性放达,放浪形骸。“青山归未能,尘网事难毕。此地即醉乡,居之安且吉。”说明竹林七贤陷入虚华的尘网之中,壮志、理想都成了泡影。为免于卷进司马氏集团和曹魏王室两派夺权争战的漩涡,相继退隐山林,过着悠闲自得的闲逸生活。然而,七贤安居山林,纵情诗酒,却不过是表面的放达而已,最后不得不重新面对世人,这种极为矛盾的行为正是七贤内心最大的痛楚。张问陶的自身经历也颇能说明这一问题。1812年船山辞官后寓居苏州虎丘山塘斟酌桥边的乐天天随邻屋,次年夏与孙星衍会聚虎丘孙子祠,老友重逢,豪情尤昔,却仍难释忧国忧民之怀,感叹“薄有时名留辇下,都无长策治山东”38。
诗歌是自我性灵的真实流露。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抒写个人极度苦闷的心情和忧愤的诗歌增多了,形成了正始诗歌的独特风貌。阮籍和嵇康是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二人多直抒忧愤之情。如嵇康入狱后写有四言《幽愤诗》,叙述自己的品格、志趣和招祸的因由,直抒感愤,风调峻切。阮籍的《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体现了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钟嵘《诗品》评云:“《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张问陶评“嵇阮多忧愤”,肯定了二人多抒发忧愤之情,诗中饱蕴着真情郁气,乃感荡性灵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