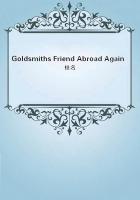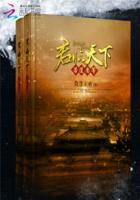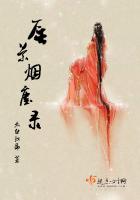在七贤当中,年纪最长和最轻的分别是山涛和王戎。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可是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了。所以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二人的相知非本志。至于王戎,乃七贤中最庸俗者。《晋书·王戎传》云: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性灵诗人张问陶,有意将山涛、王戎与嵇康、阮籍对举,以山、王之少性灵,反衬嵇、阮多率性之作。船山性格放达,颇似阮籍,其诗友李鼎元曾有诗曰:“船山阮籍流”39。船山对阮籍确也厚爱有加,在《题刘澄斋前辈寓斋》诗中,特提到“口不谈人阮嗣宗”。据《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这主要是由其时代与身世决定的。阮籍同情曹魏,不满于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李善《文选注》分析这种情况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阮诗寄托遥深、风格隐约曲折的特点,在张问陶诗中也多有体现。尤其他的言志诗,多借用一些艺术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故石韫玉《刻船山诗草成书后》有“寓言十九解人难”之评。
竹林七贤都能饮,惟以刘伶酒量尤著。传说他生活穷愁而又纵酒放达,酒量之大,举世无双。刘伶死后葬于河北徐水县,其墓至今尚存,后人还为其建立了《酒德亭》。李贺《将进酒》中写道:“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张问陶几次祭奠刘伶墓已不得知,但在《船山诗草》中,仅以《刘伶墓》为题的诗歌,就存有两篇。诗歌中所提刘伶荷锸与长醉不醒之事,《世说新语·任诞》篇和《晋书·刘伶传》皆有所记载40。刘伶荷锸、“死便埋我”,甚至醉酒后赤身裸体。阮籍、刘伶等人的行为举止在一般人眼里可谓放荡不羁,却是性灵诗人最看重的“真性情”。无独有偶,张问陶醉后曾大呼着李青莲的名字“锦衣玉带雪中眠”41,其放浪形骸不逊于刘伶。其实张问陶与刘伶等人的佯狂不羁的背后,透出的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叛。刘伶曾作《酒德颂》以刺世嫉恶,张问陶也有《骤雨》诗云:“大梦因诗觉,浮生借酒逃。”42明确说明自己嗜酒好饮,乃逃脱恶浊的现实。
故国情是《船山诗草》中永恒的话题,这是袁枚诗“情”所未曾涉及的领域。张问陶曾有诗云:“故国情难尽,奇诗性所耽”43。遂宁依山抱水,水碧山青,风光旖旎。还有那一笼一笼的翠竹掩映屋舍,人们就像是在画里出入。船山一生南船北马,驻足故乡遂宁的时日并不多。但每逢回乡,他都不放过这难得的饱览家乡自然风光的机会,每过一地,皆有题咏。可以说,遂宁的一山一水、—草一木无不寄寓着船山深深的眷爱之情。一旦离开家乡,船山的乡愁则绵绵不断。早在客居江汉时,船山一家朝不保夕,穷愁不堪,栖息于郊外水边一破旧竹楼里。诗人周围“坐看儿童皆楚语,几如贾岛客并州”44,触景生情,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经常独自“万里登楼怀故乡”45。回乡守岁的传统自古有之,岁暮在即,张问陶不得归故里,遂写诗寄怀。“蓟门秋色澹幽州,鹤唳华亭忆首丘”46一句,即借“二陆”兄弟被刑之时,不得再闻家乡鹤鸣47,来遥寄乡思。嘉庆元年丙辰,船山三十三岁,任翰林院检讨,闲居京师,乡愁绵绵,《丙辰初冬乡思》,云:“乡愁黯黯穿巫峡,归梦明明隔剑关。”48虽说船山《咏怀旧游》有“莫访秦淮半里桥,江南能使客魂销”之句,但江南的柔婉,到底抵不过浓浓的乡情,因而生出“丹粟香飘客更忧,梦牵故里望高楼”之叹。船山最后客死苏州,仍在忍受着乡愁的煎熬,可谓抱憾终生。
亲情是性灵诗表现的重要内容。《船山诗草》里有大量描写亲情的诗篇,尤以描写兄弟情最多。张顾鉴有三子二女,兄弟姐妹中,船山与亥白兄感情最笃。“亥白诗才超逸,与问陶有二难之目。”49无奈船山投身仕宦,兄弟间聚少离多。船山有诗云:“君昔游京华,我居沌水北今我客京华,君居沌水阴人生无百年,八载三离别。”50但是无论咫尺相处还是相隔天涯,船山、亥白或唱和或寄诗写情。几乎亥白每到一地,船山都要题诗送别。而船山所到之处,也总是不忘叙写兄弟间怀念之情。《船山诗草》中有多处提及自己和亥白兄的手足之情,每每以陆机、陆云兄弟的生死相依之情比之。船山滞留武连的某个月夜里,思念兄长难寐,然天各一方,不能相见,惟以诗抒发不能聚首之憾。诗人回忆起乾隆五十四年参加会试,自己与亥白兄结伴离开家乡,共赴科考之路,虽同时落第,却得兄弟联吟之乐。“出山坡颖科同举,入洛机云屋两头”,即以“二陆”指自己和亥白兄当年共赴科场之事。在年已不惑的亥白兄远去粤东之日,船山赋诗送行,劝兄长“远道萍逢莫久留”,“早晚同归慰白头。”亥白居粤,船山又写诗《寄亥白》,“并马三千叠,联吟屋两头”,再次以陆机、陆云兄弟同屋联吟作比,遥寄思兄之情。后来,船山为求仕途孤身一人独在异乡,没有了兄弟间的携手同行,生活上又捉襟见肘,故而借陆机“不鸣不跃”语,51表达自己不为重用,郁郁不得志的心绪。
遂宁张氏家族中女眷能诗者多。既有“三姊妹”诗人,又有“三妯娌”诗人。张问陶的续弦林佩环,弟媳杨继端,大姐张问端,四妹张筠,皆学识渊博,能诗善文,都有诗集留存。大姐张问端曾著有《淑征诗草》,弟媳杨继端著有《古雪夫人集》,林佩环有《林恭人集》。此外,堂妹张瑶缃也工诗,常与林佩环、杨继端等相唱和,诗载于《历代全蜀诗钞》。张问陶在《船山诗草》中赞其女性亲眷之才时,常以谢道韫并举。东晋女诗人谢道韫是一位出尘脱俗、超越凡流的旷世女才人,其识知精明,聪慧能辩,有咏絮之才。52谢氏才藻,卓绝名誉当时,时人以林下之风53称道其人其作。张问陶在《船山诗草》中并未直接称道谢道韫,而是以谢道韫来夸赞自己的女性亲眷,一是借以赞美才貌双全的续弦林佩环,一是用于称誉风华卓绝的四妹张筠。
张问陶原妻周氏早亡,续娶顺天宛平人林佩环(林韵徵),夫唱妇和,伉俪殊为情深。张问陶与林佩环姻缘天成。佩环出生之日,其父林西崖上任成都县令之初,有人手持一古砚求售,上有一玉符,符下有铭。林西崖奇之,赎而藏。二十年后张船山入赘林家,见古砚知乃高祖文端公赴千叟宴时,仁庙所赐之砚。夫妻二人皆以婚姻之结有宿缘。此乃船山《连理亭忆内》“玉符宝砚务前因,少小缠绵共一身”一句之来由。佩环不但貌美,且工书善画能诗。船山论诗主情真,不讳对儿女私情的真实描写。他在诗中对佩环的才貌赞不绝口,如“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54《砚缘诗四首》其四云:“袖中已遂襄阳癖,林下犹逢谢女才。娶妇也须无俗韵,生儿应免出凡材。”充分表现出对这位可为之画眉、可与之论诗谈画的佳人才女的高度欣赏和深切爱意,得遇知音的遂心之情流露不尽。而“林下犹逢谢女才”,以谢道韫来比拟和叹美佩环的才气惊人,所谓巾帼不让须眉也!
四妹张筠才华出众,适汉军高扬曾55,但因婆家虐待,年仅二十早逝。张问陶为此痛惜不已,特赋诗《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以追忆。“似闻垂死尚吞声,二十年人了一生”,描写了四妹忍气吞声,华年早逝,哀叹她生命的短促。“林下风清道韫诗”之句,称赞四妹才华与诗作堪与谢道蕴相比。“拜墓无儿天厄汝”,悲叹她死后的凄凉。“寄语孤魂休夜哭”,更怜她孤魂留居异地。所以痛切地呼唤她“登车从我共西征”,回到自己亲人身边。“那知已是千秋别”,从此与四妹再也睹面无缘,“日下重逢惟断冢”。“再来早慰庭帏望,一痛难抒骨肉情。”表达了痛失同胞骨肉的悲情。诗人在最后用“无数昏鸦乱哭声”一语,更点染出眼前悲凉凄清的图景,以衬托自己的哀思。每一句诗,都出自诗人肺腑,表现了兄妹骨肉同胞之情。袁枚的《祭妹文》以家常语对亡妹叙琐事、寄深情,文笔细腻生动,,情至笔随,哀婉动人,催人泪下,令人不忍卒读。张问陶的《哭四妹》更一字一句都是血,全诗哀怨缠绵,读之令人肠断、肝裂、心碎,为性灵说中至性至情的亲情表现。
赞扬女子的才气,是张问陶尊重女性的表现。不惟如此,他还主张男女平等,表现出可贵的民主意识。唐时蜀中才女薛涛多才多艺,声名倾动一时,虽有“女校书”之称56,却只能以歌伎兼清客的身份出入幕府。张问陶《九月一日回澜寺塔晚眺遂访薛涛井》诗中“秋花才女泪”,其实质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批评。而更能表现其民主意识的是《重过马嵬》诗57,云:“小殿玲珑锁夕曛,缭垣红坼冷春坟。香魂莫怨陈龙武,一死居然抵六军。儿女谁甘负好春,红闺几见可怜颦。三郎不合为天子,苦被江山误美人。”张问陶一反“美人误国”的说法,不但说美人无罪58,还肯定了美人力量之大可抵六军。破除了美人误国的传统偏见,洋溢着浓郁的民主意识。他还从性灵出发,批评唐明皇为了江山,辜负了美人,有违性情之真。船山所论,也是性灵说重男女之情的表现。他又劝杨玉环的亡魂莫怨陈龙武将军,将军请求皇上赐杀美人,出于浓浓的忧国之情。将军忧国,何错之有!张问陶此论亦其拳拳爱国心之流露。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济世安民、平治天下是他自幼以来的心愿。他十五岁时即有“三十立功名”之志59,科举及第后居京师近二十年里,虽俱为闲职,但强烈的参与愿望和忧患意识始终不曾消解。嘉庆六年,在他作京官闲置11年之后写道:“俯仰看浮世,雄心未肯灰”60。嘉庆十二年,他44岁时还说:“千波早破升沈想,百药难回少壮心”61。此热烈的入世情怀和济世报国的宏大抱负终生不泯,故对历代爱国文人多有褒扬。如“荒鸡午夜起刘琨”,就是对刘琨在胡人南侵,家国残破之时,及时振作,渴望建功立业,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的赞誉。因祖逖、刘琨“闻鸡起舞”62,后人常以鸡声比喻有志者及时奋发。张问陶说“莫道荒鸡是恶声”,赞刘琨诗感情深厚,充满积极进取的爱国热情,也借以况己,表明自己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
张问陶提倡诗歌的天真自然,反对雕琢,所谓“自磨碎墨写天真”63,“墨淋漓处见天真”64。要求以自然平淡的语言,表现描写对象的本真,传达诗人的真情实感。东晋诗人陶渊明率性真淳,其“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65,这也使得其诗情真语挚,摒离雕饰,近乎口语、平淡质直地传递着他内心的“萧散冲淡之趣”66。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用词最为简净、含蕴,却又至为丰美的诗人之一,故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赞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诗也正是船山所欣赏的“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67的典范,若同时代,船山定“挽渊明共写真”。
南朝齐诗人谢朓,其山水诗一扫玄言余习,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李白《宣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推崇:“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刘熙载《艺概》也说:“谢玄晖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赞其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以天真之心,写天真之景,得天真之境,谢脁可谓做得最好的诗人之一。张问陶论诗常常言简意赅,“满眼青山小谢诗”,将谢脁山水诗的清新流丽风格,点染如画。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真正流传千古的作品,往往是那些以其独特的审美内涵,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情感共鸣和心灵愉悦之作。张问陶对此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其《乙卯春夏与穀人前辈饮酒诗》云:“下笔不求惊俗眼,闭门同忘是官身。奇文传世原无口,公论凭心自有人”68。然而,在诗歌鉴赏中,由于受时代的影响以及鉴赏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等制约,难免对同一作品有不同的评价。北周文学家庾信,天才勃发,捴历代之美,兼诸家之长,炼成一己独特风格,掩映往古,独标当世。其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之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然漫为轻薄者嗤点。隋代与唐初学者,不少人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69。自杜甫起,一些史学家、文学家,不仅对庾信的同情多于指责,而且对他后期的作品亦推崇备至。杜甫《戏为六绝句》开篇事敌也不无微词,但更多地表现了宽容或同情的态度,对其后期诗赋创作更是极尽推崇。
庾信、杜甫、张问陶,平生颇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创作兼有表陈时代的史诗性质。73杜甫《咏怀古迹》,是诗人寓居夔州时所写。明写庾信遭乱流离,暗拟自己流寓的遭际,借古喻今,抒发自己暮年流落的怀抱。张问陶少年时代即随全家寓居江汉,过着忧衣虑食的贫困生活。从二十一岁首次由江汉而北上京师,到三十五岁的十余年里,南船北马,关河跋涉,三四次辗转于湖北、京师、巴蜀间。或因经济的困窘,或因旅途的劳顿,或因科场的失利,或因奔父丧的悲痛,使他备受折磨,心力憔悴。张问陶夜宿汉阳客舍,题壁“一树枯槐怜庾信,十年秋柳泣桓温”,将庾信与桓温并举,74通过桓温攀枝执条,泫然泪下,张问陶捕捉到了一代枭雄桓温壮志未酬的英雄泪,也慨叹庾信羁留北地的故园之思。这跃然纸上的真性情,感伤其遭遇,重现其悲怆,与庾信、杜甫可谓气息相通,千古知音。他对庾信的批评与杜甫一脉相承也情在意中。
枝江地处长江中游,属三峡之末,荆江之首。江陵位于荆江之滨。庾信遇侯景之乱,遁归江陵,暂居庾家故居,即江陵城北三里宋玉宅。75唐张说《过庾信宅》76云:“兰成(庚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直接点明了宋玉旧宅里走出的新词人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在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宋玉相比拟。张问陶寄迹江汉时与兄张问安常泛舟江上,对酒当歌。野泊枝江,透过一线江月,江陵古城的庾信旧宅隐约可见。“一线枝江月,千年庾信居。”“记取临江宅,相留庾信传。”“势接海门秋,江声拥户流。诛茅来庾信,蓐食去韩侯。”张问陶虽未对庾信和宋玉创作予以比较,却通过上述诗句描写了庾家故居,感同身受,亲切怀念,揭示出宋玉旧宅因庾信暂居而愈增其光辉的故实。这与张说“兰成(庚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