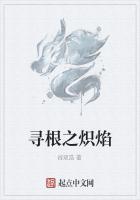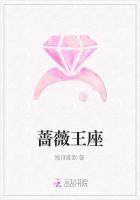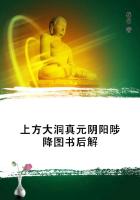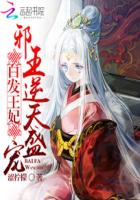侯景之乱,是庾信人生的重大转折。三十六岁,正值人生可大书的壮年时期。但是,国破家亡后,子山不得不做出了无奈的选择;北仕后,一方面感念北周朝廷知遇之恩,另一方面终觉有负故国。六朝时期的社会对忠义鲜为倡举,77庾信仕北在当时于一般人而言不足为奇,但是庾信成长在“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78的家风世德下,难免造成道德上的洁癖。这使得庾信几于位极人臣,但内心一直充满了痛苦与耻辱。这种人生的尴尬,使他晚年所作,内容上起明显变化,多抒发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和人事维艰的情怀。如《哀江南赋》、《枯树赋》等,有意承担心灵上的哀愁与无奈,自伤遭遇,慨身世而痛家国。风格也转为萧瑟苍凉,忧深愤激。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论述庾氏北朝时期的作品时,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79,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之精神特质。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亦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家族、时代、环境,铸成一位情辞俱胜、文律双美的诗人。庾信后期的创作,笔势凌云,才思纵横,写出了对国破家亡之痛的悲剧性感受,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等的感性显现。其发自内心的性灵之作,自然会引发读者心灵上的共鸣而流传百世。故张问陶言:“文章悲庾信,嗤点亦流传”,指出了庾信作品具悲情特点,又赞其虽遭嗤点仍魅力自在。
张问陶论唐代作家
张问陶对唐代诗人,从初唐、盛唐、中唐到晚唐,都有论及。共评唐代诗人九位:初唐陈子昂,盛唐杜甫、李白、王维、苏晋,中唐孟郊、李贺、卢仝,晚唐杜牧。或论其生平,或评其诗歌创作成就和艺术特点,或既论生平又评创作。他所选评的唐代诗人,或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如盛唐诗坛上鼎足而立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或创作上独标一时、卓然于世,如“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或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如以险怪著称的卢仝、开奇诡幽冷诗风的李贺,于晚唐浮靡诗风中创俊爽雄丽诗风的杜牧。当然着墨最多的是有着“诗史”之誉的杜甫。
陈公读书处,立马怅临歧。
暝色来东蜀,江声走大弥。
诗推前辈好,山爱故乡奇。
望望金华远,虚名迥自疑。
(《射洪》诗草补遗卷二)
(评陈子昂)
烟笼雉堞影参差,历落轮蹄度陇迟。
关笑楼兰兴筑日,民伤天宝乱离时。
年丰不下丁男泪,县小犹传子美诗。
瀍水一湾山四合,暮蝉声里柳丝丝。
(《新安》诗草补遗卷二)
潦倒徒怀灞上游,老来诗笔遍夔州。
东屯秔稻三年熟,西阁云山万里愁。
鸡栅水筒随竖子,短衣雄剑谒诸候。
移家我亦成都客,落日空登白帝城。
(《夔州怀少陵》诗草补遗卷三)
君不见杜陵流寓依峨岷,苦搜佳句悲沉沦。
草堂当日劳裴冕,更起祠堂累后人。
(《和王铁夫移居诗兼赠同门何工部道生阑士》诗草卷十)
万间广厦存虚愿,何日能酬杜老诗。
(《立秋日屋漏不寐》诗草卷四)
足茧荒山有杜陵,饥驱自笑客何能。
(《感事》诗草补遗卷一)
已分多愁如杜老,还闻得谤似欧阳。
(《赠相士乔君》诗草补遗卷三)
杜甫《秦州》作,天真协古风。
(《早秋夜雨寄怀毕展叔先生》诗草卷二)
三复杜陵诗,此笔竟难搁。
(《入剑阁》诗草卷三)
狂到杜陵甘作客。
(《春日感怀》诗草卷二)
杜陵诗境在,寂寞古今情。
(《盐亭》诗草卷二)
地擘雍梁山自好,诗留李杜我何题。
(《登华阴庙万寿阁望岳同亥白兄作》诗草卷三)
误我浮名才李杜。
(《中秋写怀》诗草卷十七)
山村花柳怅归期,好句何如杜拾遗。
(《赠杨荔裳观察即送其之川北道任》诗草卷十)
(以上评杜甫)
锦衣玉带雪中眠,醉后诗魂欲上天。
十二万年无此乐,大呼前辈李青莲。
(《醉后口占》诗草卷五)
爱我猖狂呼李白,看君光气夺齐桓。
(《过阳湖怀稚存》诗草卷十九)
逃禅入道翻多事,合买扁舟泛五湖。
(《踌蹰》诗草卷十三)
莫讶上书狂欲死,东山李白是乡人。
(《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诗草卷十)
(以上评李白)
右丞颇好道,苏晋欲逃禅。
诗酒皆余事,山林有少年。
(《题画》诗草卷十三)(评王维、苏晋)
寄语穷愁孟东野,新诗休作不平鸣。
(《击筑吟》诗草卷二)
穷如冬野例工诗。
(《春日感怀》诗草卷二)
(以上评孟郊)
游戏韩门气不酸,不为岛瘦不郊寒。
诗人婢仆何妨丑,只作妖童艳女看。
(《玉川子像为陈闻之题》诗草卷十三)
(评卢仝)
别有《罪言》吟咏外,谈兵愁煞杜司勋。
(《小游仙馆排闷杂诗》诗草卷十五)
(评杜牧)
小杜谈兵笔有霜。
上帝居然召长吉,
不真夭折非才鬼。
(《怀古偶然作》诗草卷十四)
(评杜牧、李贺)
遂宁英才辈出,人文荟萃。初唐诗人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诗坛千古绝响。位于射洪县城北23公里处的金华山上的读书堂,或称陈公学堂,是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后改为陈子昂读书台。80历代追索先贤遗风,来此凭吊者众多。“诗圣”杜甫在绵阳时,曾作诗为梓州(今四川三台)上任的李使君送行,嘱其代为祭奠陈子昂,诗的最后四句曰:“遇害陈公陨,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81,为陈子昂的不幸遭遇流下同情之泪。宝应元年(762),陈子昂蒙冤去世已62年。时年仲冬,杜甫扶杖往梓州城东60里的射洪金华山玉京观,访陈子昂读书台,写下《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又访射洪县北东武山陈子昂故宅,作《陈拾遗故宅》,以示悼念。杜甫极力赞扬陈氏人格的忠义,对这位前辈甚为景仰,高度称赞其绝世诗才:“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而且他们俩又同官拾遗,对陈子昂不幸的身世遭遇更是同情。其感情之深,可谓千古知己。白居易在《初授拾遗》诗里,即把陈子昂与杜甫并题:“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船山与周氏完婚后,曾居京师岳父家,到卢沟桥一带漫游,作有《卢沟》诗:“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透过乾隆盛世的表象,敏感的船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沉闷和对人才的压抑。《律诗三百首》将其与《登幽州台歌》并论,评云:“大有四顾茫然,寂寞孤独之感,可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并读。”82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得湖北巡抚吴垣(号树堂)千金相助,张顾鉴一家八口乘舟从汉阳出发,溯长江西上,首次踏上返乡之路,五月初抵达魂牵梦绕的故乡遂宁。次年夏初,船山到川北射洪县、潼川府(今四川三台)、盐亭县等地游历。登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作有《射洪》一诗。援引诗人的诗句来论诗人,是张问陶论诗诗常用的方式。“立马怅临歧”即化用了陈子昂《感遇》诗“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一句。《感遇》诗,是陈子昂感奋之作,主要抒写诗人平生遭际及因之触发的感想。对于《感遇》诗,历来毁誉不一。赞扬者誉其为“古体之祖”83,“非当世词人所及”84。反对者言其“蹈袭汉魏”85,“尤多拙率之病”86。“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是陈子昂仕途不得志时,借助古代传说故事,以求解脱痛苦,消除苦闷。船山立马读书台时,恰功名淹滞之际,又赋孤鸾之恨87,吟咏子昂“临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诗句,深深地感受到了先辈心中的伤感,引发了对自己坎坷之路的惆怅。此情此景,颇似当年杜甫凭吊子昂。
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的诗人是陈子昂。其始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成为开一代诗风的“百代文宗”。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在唐诗革新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唐代诗歌的开创者,他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更广义的精神上,开启了盛唐整整一代诗人,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张问陶诗才横绝一时,被誉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其弃旧图新的诗风追求,不因袭、不摹仿,独开门户的创新精神,得到诗界及诗论者的赞许和褒扬,张维屏《听松庐诗话》说:“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贡献而言,陈、张是殊途同归的。陈子昂的文学成就令船山无比景仰,对照子昂,他深为徒得虚名而恍惚不安。所以,其“诗推前辈好,虚名迥自疑”88,并非矫情,乃肺腑之言。
一般来说,对作家的批评,从用笔多少可反映批评者所持的态度。在历代作家中,杜甫是张问陶用笔较多的一位。专论杜甫的诗歌有《夔州怀少陵》、《新安》两首,兼论杜甫或杜诗的还有十余首。船山概论杜甫的生平和创作,又对其每个时期(长安时期除外)的创作情况都有所涉及,且重点论其漂泊流寓之作,这是以前的批评者们所少有做到的。杜甫是历代诗人中颇受张问陶推崇的对象,以性灵之眼读杜诗,他所感知的诗人形象,性情真纯,个性疏狂,漂泊流寓,“足茧荒山”。在他的笔下,忧国忧民的诗人杜甫,神形毕现。而在杜甫身上,又依稀可见船山的身影及其感喟。在此,我们循杜甫足迹,看张问陶是如何论杜的。
杜甫的一生,东西漂泊,生于河南巩县,死于湘江船上,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他都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作。故有“杜陵诗卷是图经”89之誉。张问陶对杜甫在所经之地的诗歌创作情况都有介绍,其中,以杜甫流寓秦蜀之作、《新安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为批评的重点。
安史之乱时,杜甫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写成组诗“三吏”、“三别”。《新安吏》为其第一首诗。一千年后,张问陶途经河南,至洛阳西“瀍水一湾山四合”的新安县,赋诗《新安》,追忆诗人杜甫当年的足迹。时光荏苒,千年已过,“年丰不下丁男泪”的新安,今日已是“暮蝉声里柳丝丝”。而“县小犹传子美诗”之“犹”字,更见杜甫在新安百姓心中的不朽地位,以及《新安吏》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杜甫《新安吏》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对于点选中男,诗人是同情和怜悯的。但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他又不能反对这场平叛战争,故忍泪劝慰人民走上前线。所以,怀着这样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诗人在揭露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张问陶的“民伤天宝乱离时”,对人民的流离失所,寄予深深的同情和怜悯,直陈导致“年丰不下丁男泪”的深层原因,是朝廷的昏庸无能,其批判的锋芒不减杜诗。
杜甫自认“诗是吾家事”90,并说“直取性情真”91。其为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保持了一种“真”的本色。可以说,杜甫是以整个生命的燃烧来完成自己的诗歌创作的。船山认为,杜甫之情志早融化在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中。杜诗饱含了诗人的真切感受,读其诗可感受到诗人的心跳,听到诗人发自灵魂的声音──真性情。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之真──好像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他的“畏人嫌我真”,“直取性情真”,非直接论诗,然可知其诗之尚性情也。92杜甫秦州之作,便是多“直取性情真”的诗句。乾元元年(758年),杜甫因上疏救房琯获罪,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遇饥乱,7月弃官客秦州。93这段岁月里,诗人“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94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然而诗人人在江湖,心存魏阙。几个月的秦州流寓,创作诗歌百余首,不少诗章感时即事,关注平叛,评论朝政得失,关心不幸者。
张问陶论诗主性灵,又强调关心现实。他说:“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95将写“天真”与关注“时务”并举,强调重视民间疾苦、世上疮痍,将其体察于心。船山在其诗歌创作实践中,终其一生地贯穿了这一思想。《船山诗草》中有大量抒写壮志豪情,渴望建功立业的诗歌,以及为百姓疾苦、民间疮痍奔走呼号的《宝鸡县题壁》、《拾杨稊》、《采桑曲》等含有深刻历史内容,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诗歌,多是从“关心在时务”的典范之作。张问陶一生为了生计,六次跋涉秦中,所作诗篇无一语蹈袭前人,皆为性情之作。《张问陶年谱》作者胡传淮先生评其《七盘岭》诗:“写尽栈道奇险,句句出人之意外,语语入人之意中,少陵由秦州入蜀诸诗以后,无敢作者。”96钱钟联《清诗精华录》说:“张问陶《船山诗草》中的秦中风光,不仅在题材的广阔上,远超前代,而且在‘诗之缒幽凿险’,状写‘难写之景’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为祖国古典诗歌宝库中的山水诗增添了新的明珠。”张问陶有不少反映人性美的诗作,他以“天真”评杜甫秦州诗,亦寓其独到之感悟,其中含有善与美的因素。我们说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力量,不单纯取决于他对苦难的直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以儒家的仁义之怀,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用以呼唤和启沃人们的良知。从体制上看,少陵秦州之作,多古风遗韵,所以,张问陶言其“天真协古风。”
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多有论述。但是杜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因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有“诗史”之称。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自秦度陇入蜀时写的《剑门》,乃此类诗歌的代表作。该诗前半部分描写了“剑门关”之险自然天成,后半部分据当时并吞与割据的局势,杜甫料定蜀中难免再度发生战乱,故“临风默惆怅”。从张问陶《入剑阁》“三复杜陵诗,此笔竟难搁”诗句中可知,与杜甫一样忧国忧民的诗人,也在为身处封建末世中的百姓的安危而忧虑不已。
公元759年12月,杜甫由甘肃颠沛流离到了成都,靠了友人尹裴冕等人的帮助,在城西浣花溪畔搭建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上元二年(761)秋,一场狂风袭卷了草堂屋顶的茅草。接着秋霖夜雨,天寒屋漏,杜甫一家无处安身,处境狼狈。他推己及人,联想到天下无数像自己一样流亡失所的“寒士”,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达了对民众疾苦的关切之情。诗歌语言深处的潜台词应该是诗人的个人性话语,换句话说,隐藏于整个诗歌意象系统中的是诗人本身,是抒情主角形象背后的事件。如果没有南船北马的生活体验,如果不是多次得到师友的慷慨解囊,“敝车羸马向风尘”的困穷生活方得以缓解,船山便无法因屋漏不寐联想到杜甫草堂,进而到“草堂当日劳裴冕,更起祠堂累后人。”同样,如果船山不忧国忧民,或者他关心社稷民生的志向已酬,也不会生发出“万间广厦存虚愿,何日能酬杜老诗”的感叹。可以说,张问陶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发现了自己,于是便有了《立秋日屋漏不寐》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