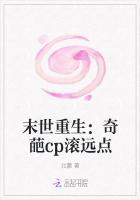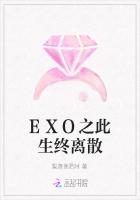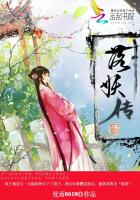大历元年(766年)春晚,五十五岁的杜甫迁徙夔州(奉节县)。期间,杜甫共创作400多首“夔州诗”,占杜诗的七分之二强。“夔州诗”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恰如张问陶《夔州怀少陵》诗所言“老来诗笔遍夔州”。杜甫在夔州度过了晚景岁月,因夔州都督的照顾,诗人在白帝城附近的草堂村过着稳定而较优裕的田园生活。但是杜甫并不安于生活的稳定,其胸有万里愁绪,怀抱伤时忧民之心。这种心境被张问陶描述为“东屯粳稻三年熟,97西阁云山万里愁。”张问陶非凭空下此断语。杜甫寓居夔州,生活稳定,但老病孤愁,壮志未酬,惟有以手中之笔去排遣心中愁苦。故其夔州诗,多感时伤世之作。如《秋兴》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清凄的秋声,暮年多病的苦况,关心国家命运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至于移寓西阁时所作的《阁夜》,更是千缕愁绪弥漫在字里行间。“野哭千家闻战伐”,“卧龙跃马终黄土”等句,简直可以使人触摸到诗人那颗极其凄苦的心。《登高》,则是杜甫风烛残年之时,独自登高时所作。诗中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处不秋。风、猿、燕、木、江、病、鬓、酒,共融一体,同表一愁。透过所见秋江景色,诗人将多少寂寞心事都写在了诗里。张问陶一生仕途失意,辗转流徙,家贫多病,但难忘家国之思。他体味到了杜甫在国家残破、长年漂泊、老病孤愁时的忧伤和抑郁,感受到了诗人虽老衰而忧国之情弥深,其“无力正乾坤”的痛苦也愈重。正因为张问陶对于杜甫的多愁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在《赠相士乔君》诗里,说乔相士“多愁如杜老”,也才写得出“潦倒徒怀灞上游”,“移家我亦成都客,落日空登白帝城”98的诗句。
苏轼《与王定国书》曰:“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杜诗渊博丰富,而苏轼特拈君臣之义,反复申说,这或许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但经后世无限引申,一味附会,将感情深沉、执着率真、有血有肉的诗人杜甫扭曲为一个神情庄重、谨守纲常、令人敬畏的圣人。张问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杜陵诗境在,寂寞古今情。”认为杜诗之所以感人,在于其出于天性,真切地抒写了古今一般同的寂寞之情。有人说诗人总是寂寞的,杜甫更是寂寞的典型。“寂寞”一词在杜诗中随处可见,如“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99“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100“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101“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102更有甚者,杜诗中的枫林凋伤、孤城落日、孤雁飘零、孤舟独泊所潜隐着透心的寂寞和悲凉。寂寞到渊谷往往可以完成大业而流传千古,正是因为这种附骨的寂寞,时时撞击着杜甫的苦闷与凄楚,使他创作出了大量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船山游盐亭时,类似当年杜甫的心情和飘零的处境,重经故地,103心境相同,与杜甫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后来,梁启超也从情感的角度来分析杜诗,以“情圣”取代“诗圣”的称号来推戴杜甫。104其与张问陶可谓同出一辙。
杜甫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其推己及人、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任何人学杜若无此胸襟则失其根本。张问陶自然深明其理,一部《船山诗草》,充满对时局的关注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其所怀有的人道情怀和民本思想,与杜甫是暗合的。尤其《宝鸡题壁》组诗,不乏担当“诗史”之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张船山先生事略》曰:“《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诵殆遍。”顾翰在《船山诗草补遗序》中称:“以为李白、少陵复出也”,意谓船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而船山诗歌中流淌着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文关怀,则与少陵诗是一脉相承的。船山积极关注变幻时局,忠实记录历史,大胆揭露现实社会尖锐矛盾斗争,也是继承了杜甫的“诗史”精神。
另外,张问陶与杜甫在诗歌艺术上也存在不少共同点。船山诗歌风格变化与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有多人指出其近体诗有“空灵而沉郁”的特点,105即由前期狂放转向后期沉郁。其前后期诗风的转换近于杜甫沉郁顿挫及“庾信文章老更成”之风。再如船山诗学思想全部通过论诗诗表达,既源于自然天成之主张,亦不能排除有意规摹和发展杜甫《戏为六绝句》创制之用意。船山还有相当数量的诗,直接化用杜甫诗句或意境。如《无题四首》之二尾联:“白衣狡狯成苍狗,忍看浮云变态殊”,取自杜诗:“天上秦云如白衣,忽然变化成苍狗”。《自题勾漏山房》尾联:“金函旧录忘焚草,清夜犹防玉女窥”,源于杜诗“避人焚谏草”。正如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寄心庵诗话》所言:“船山太守为蜀产,其诗以放翁门径,上攀少陵,取其雄快之作,而芟其剽滑之篇,斯太守之真诗见矣。”船山论诗主张“好古不泥真通人”,作诗应向古人学习,但不可拘泥古人之法,要推陈出新,表现出自我性灵。其《登华阴庙万寿阁望岳同亥白兄作》写道:“地擘雍梁山自好,诗留李杜我何题?”反映出对两位诗坛巨擘服膺其才却不愿重复的心态,106此为得其真精神也。杜甫提倡“转益多师”和“别裁伪体”,其诗歌创作“别开异径”,在盛唐诗中走出一条新路子。杜诗造语皆工,得句皆奇,佳句俯拾即是。张问陶以“好句何如杜拾遗”说杜甫,论之极是。
杜甫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107谈到自己的家世时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代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张问陶在精神上趋向于李白,但在言行上又更近于杜甫之“腐儒”。虽然他没有像杜甫那样以“儒”自称,但沐浴在“家风贫尚守”、“相业史重编”的流风美德下,耳濡目染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传统人格模式。他所受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杜甫。尽管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化,彼此外在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但他们的诗都是真性情的抒写。船山从儒家入世思想出发,而又不为儒学所限,结合自己的时代和亲身生活实践,去阅读杜诗,感悟杜诗精神,也真正读懂了杜诗。船山诗也写出了人生真情、真性、真阅历,反映社会时弊、民生疾苦,而又率性自然,真正继承了杜诗的精髓,堪称杜甫千古知音。
张问陶身处乾嘉之际,诗学受时代风气和传统儒学之熏陶,也受到故乡巴蜀文化的浸润,更由于其亲身体验治世与乱离的特殊经历、刚直不阿的秉性气质,使他与诗圣杜甫有着自然的心灵契合。他自觉地学习仿效杜诗,受到杜甫的多方面影响。但他的学杜不是追求表面形式,而是融杜甫精神于诗论诗作之中,故此天然无痕,人不易察。这应归之于作者深沉的崇杜爱杜之情,也与其相同的人生际遇和不慕名利密切相关。船山一生虽过着“饥来百事非”,“人谁足稻粱”的贫困生活,却怀着“隐轮匡时略”、“慷慨对中原”的雄心,高唱“英雄不下穷途泪”。而且他个性孤傲率真,足迹遍人寰,逢山赠一诗。凡此皆与杜甫相似。故《感事》诗里,以“足茧荒山有杜陵,饥驱自笑客何能”,赞杜甫漂泊流寓,一生恒饥,仍坦然自笑,贫困不移的精神。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曾有“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之叹,注意到了杜甫较少被人关注的一面——疏狂。108而张问陶《春日感怀》里说“狂到杜陵甘作客”,恰如金圣叹《杜诗解》所评杜甫《去蜀》是:“勉强收泪语,正复更痛。”109萧散疏狂之极的杜甫却“甘作客”,正复不得不甘。这是壮志难酬的失望、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内心隐痛与惋叹。张问陶一生南船北马,从其“人谁爱远游”之句,可观其无奈之情。所以他更能理解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的苦痛和忧伤。
李白是蜀地走出来的伟大诗人。作为蜀中同乡,张问陶本该对其大肆赞扬,但是遍检《船山诗草》,论李白的诗句却只有寥寥几处,且对他的诗歌创作情况只字未提,全部是关于李白的性情、气质、爱好的评析。如“狂”、“谪仙”、“嗜饮”等。不过,我们并不能凭此表象断定船山不喜李白。因为无论是从性情气质还是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上,船山与李白都有着诸多的相似。
自贺知章的“天上谪仙人”后,后人便以“谪仙”称李白。这不仅因为李白好道家神仙之术,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气质。李白多奇思,好幻想,常兴逸天外,将诗写得如此超凡脱俗、鸟瞰大地。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说李白诗“以自然为宗”,至为确切。“自然”,是李白文学观的核心。他的诗歌创作纲领,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110。“天然”,有时又叫“天真”、“清真”,都是自然之义。其表现在内容方面,是直抒真情,不事矫伪;表现在形式方面,则是自然天成,不假雕饰。这两个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在李白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其诗作的总特色。由于以自然为宗,李白对诗歌创作中伪饰之风深恶痛绝,他借庄子寓言,对丧失“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式的所谓创作,给予了辛辣的嘲讽。111性灵诗人张问陶也以“天真”论诗,《出江口》诗中有“人生贵自然,即景皆可恋”之句,揭示了其贵自然的人生观和追求自然天真的文学观。他说“偶然淡语得天真”,112“雕文镂采太纷然”,主张“毋绮语”、“尚清歌”113,甚至说“谩语谰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丰神”114。这正是对李白诗歌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张问陶的古体诗,以雄豪奔放、酣畅淋漓的抒情方式,形成了急风骤雨般的强烈气势,洋溢着雄健之气。最能体现这种创作特色的首推他的山水纪游诗。其山水纪游诗侧重于描写阔大、壮伟的自然景观,尤其是诗人一般不对景物作静态的审美观照,而是以汪洋恣肆的笔调,挥洒出一种奔腾、回旋的动势,创造出一种雄奇、奔放,气势磅礴的壮美境界。例如:“悬流争赴壑,轰若万马嘶。疲骡盘涧底,怒浪吞腰围。急瀑奔大石,突兀来元龟”。115大笔挥洒,把急瀑、怒浪、深壑写得惊心动魄,声势浩大。诗歌境界阔大,气势雄健奔放。这也正是李白山水诗的一大特色。张问陶还善于化用李白的诗句,揉进自己的作品。象“一奁孤月满轮秋”、“欲寄愁心蟾影阔”116,分别化用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117、“我寄愁心与明月”118。可见,他是有意识地把李白作为学习对象的。所以,人们在评价张问陶的古体诗时,往往与李白的诗相提并论,说其“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119,“欲歌欲泣,情见乎辞,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120
如前所述,张问陶的积极入世可与杜甫同日而语,但其心理状态始终是倾向于浪漫的李白和豪放型的苏轼。船山的清高孤傲、豪迈洒脱和无拘无束,都与李白如出一辙。所以,醉眠雪中,口里还在“大呼前辈李青莲”。他尝自言狂如李白:“莫讶上书狂欲死,东山李白是乡人。”他在当时也着实赢得了狂名。知交洪亮吉“爱我猖狂呼李白”,门生崔旭在《念堂诗话》中对他也有一段评价:“船山夫子,或目为才子,为狂士。乃有识之才子、狂士也。”准确道出了他的性格特征。在生活情趣上,除了热爱林泉丘壑、喜欢结交朋友等与李白接近外,张问陶还有一点与李白惊人地相似—耽于饮酒,尝自言“平生嗜酒耽枯吟”121。他的诗作中有大量的饮酒诗。“夜深鬼问开天事,大醉摇头笑不知”122,何等豪逸、洒脱,颇得李白饮酒诗的神韵。“我生三十年,年年游醉乡。不知百年中,当倾几万觞”123,比之李白的“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124的纵情豪饮,毫不逊色。李白解金龟换酒,张问陶亦曾“宫袍雕裘抵酒缗”,其豪爽不羁不让李白。而船山“几曾长揖谒公卿,宾刺过门懒送迎”125、“挥手风尘傲五候”126中表现出的蔑视权贵,又颇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气节。船山一生善诗嗜饮,有人以耽诗癖酒讥之,却不解其借酒浇愁,赋诗排闷。其《断酒》之二云:“一日不醉不可,千日不饮何妨。胸中自有真意,错被人呼酒狂”127。《丙辰初冬乡思》自言:“酒失无心空自悔,诗狂有托恐人删。”128船山借酒排忧、逢饮必醉,酒酣赋诗的背后,是对世俗的强烈蔑视与反叛,这与李白借酒解愁,慷慨悲歌,抒发心中郁闷是相通的。与封建社会大部分有志士人一样,张问陶一生都处于仕隐矛盾中。他重视功名事业,但身居廊庙,却心在山林,热切向往自由的生活。“神驹空其群,安能受羁勒”129,这句题画马诗,正是他自身的写照。好道、爱佛、嗜酒可以使人暂时解下面具、放浪形骸,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一句“苏晋长斋绣佛前,醉后往往爱逃禅”,反映苏晋既“长斋”又贪杯之特点。苏东坡在《谢苏自之惠酒》诗中评说杜陵《饮中八仙歌》云:“杜陵诗客尤可笑,罗列八仙参群仙。流涎露顶置不说,为问底处能逃禅?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长孤圆。”这里的“为问底处能逃禅”是说苏晋虽逃出禅来,但试问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张问陶则认为与其逃禅入道,不如向李白学习“合买扁舟泛五湖”130,反映了旷达的人生观。
自然环境孕育文化精神,教化传统熏陶文化精髓,这是“文化生态学”的有益的观点。自然风貌对作家的审美趣味有很大影响,同一地域的作家,容易产生相近的审美观。古人早已意识到了这点,如沈德潜尝谓:“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处之地”。蜀地雄奇壮丽的山川,陶冶了蜀人豪放的性情,形成了一种审美心理积淀。蜀人喜好浪漫奇诡,富于奇特想象。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正是古巴蜀人“发散式”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蜀人这种发散型思维方式必然在文学上倾向于浪漫主义,富于文采和想象力,易于形成富于激情、向慕奇幻的文化心理,并因此形成了巴蜀文学一向具有的雄豪阔大的境界。从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的创作上,我们很容易辨别出一种相同的气韵。那么,张问陶作为蜀地的诗人,性情、气质、爱好诸多方面接近于李白,在创作风格上与李白有相近之处,也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