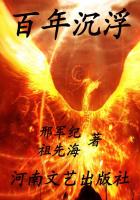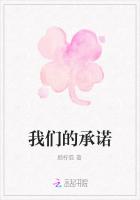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九日,船山怀着对尔谀我诈的封建官场的憎恶和无力解莱州灾民于水火之中的愧疚,愤而辞官。从此远离“鱼龙怪幻”的官场,重整“诗狂”头衔。
张问陶洁己爱民,但忧民而谋道无策,忧贫而谋食无方。在其位却难谋其政,抽身而出又常常自我谴责,乃至忧愤成疾。辞官离郡,本应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但是“老屋生前破”,“无田可归耕。”船山携女将妻来到向往已久“能使客魂销”的江南,侨寓苏州虎丘。虽然每日亲临翠堤碧水,沐浴在晓风杨柳中,但身在异乡为异客,思乡之心尤笃。苏州两年多,靠卖字画和亲友接济维持生计,衣食尚且无着,更无旅资成行,贫病交加中客死苏州。船山英年早逝,文坛齐悲。袁洁痛哭:“人间留大笔,海内失仙才”36。门生崔旭闻得恩师病逝噩耗,故地重经,眼前物是人非,悲从心来,“忍泪立多时”37。与船山骨肉情深的亥白兄接到船山门生姚元之来信,起初对船山已殁尚冀是讹传,当从季弟文莱信中得以证实后,簌然泪下,悲痛之中,作《七月廿八日得旂山季弟书,知船山仲弟确耗》,恸哭:“最怜旅殡留玄墓,何以高堂慰老亲。犹有春前音问在,一回展看一沾巾。”38白发高堂每日都在盼子归蜀,船山客死他乡的噩耗,作为兄长的问安不知如何启齿告知老母。其哀惋欲绝,催人断肠。诗友吴锡麒《哭张船山三首》质问上苍:“如此惊才仅中寿,问天何苦更生才。”船山生前曾有诗叹“大材难用皆天数”,却未曾料,惊才如他,竟遭天妒。《张问陶年谱》39作者胡传淮先生有感于船山在封建官场的卓尔不群,仿船山《潍县道中》赞曰:“百年多少莱夷长,忍俊惟有张问陶”,当是对二百年前的蜀中同乡张问陶磊落人生的充分肯定。
张问陶的性格与思想
张问陶天性多情,所谓“造物偏赋尔多情”。他为人耿介亢爽,胸不藏私;志行高洁,有一颗赤子之心;还聪明机智、幽默风趣。
天真至性用情极深
张问陶天真而至情,不媚上,不欺下。对国家忠孝节义,对亲人至情至爱,对朋友视若骨肉。船山的淳朴而重情谊,源自家庭的直接影响。父亲张顾鉴乃谦谦君子,仁厚之士。自奉极简,但慷慨好施与。滇中罢郡后,寓九华山,困乏殊甚,然见义必为。尝访得座主许公家茅屋一楹,仅存九十二岁之嫂,五十余岁老妾,孙妇一,从孙女二,其孙以贫乏远出不归五年矣。张顾鉴命急足寻归,教之贸易,并为师置坟,户得资以养焉。母亲周儒人,贤良慈爱,自乾隆十五年与张顾鉴完婚后,至乾隆四十五年船山大母李氏卒,三十年里周李二人和睦相处。张顾鉴常年远在异地,周儒人体弱多病,却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重负,多次带着八口之家,南北迁移,历尽艰辛。父母的言传身教,船山在潜移默化中也成为有情有义之人。崔旭评船山师“于朝贵无献媚贡谀之言,于同列无含讥带讪之语,下至能诗之奴、卖饼之叟、久侍之老仆、工书之小吏,无不一往情深。”40船山诗歌内容广泛,但无论题材主题如何千变万化,不变的却是那人间真情。可以说,一部《船山诗草》纯然是船山的真性情之作,情贯终卷,未曾断绝。诗中流淌着缠绵悱恻的爱情、至真至纯的亲情、浓浓的乡情、情同手足的友情、感人肺腑的师生情、割不断的家国情、依依不尽的山水情、泣人泪下的主仆情。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船山诗草》41来解读其用情之深。
张问陶主张诗歌抒发性情,即使是家庭琐事,友朋交往,怀乡之情到了他的笔下都情真意切。他在乾隆四十三年所写的《壮志》42,直言其报国之志。诗云:
三十立功名,四十退山谷。
不见两鬓霜,英雄死亦足。
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
光气未腾天,魍魉抱之哭。
人生不得志,天地皆拳曲。
慷慨对中原,流年何太促。
落拓大布衣,许身非碌碌。
四十四万言,隐轸匡时略。
为天子大臣,上书继臣朔。
年仅十五岁的张问陶博览群书,才华横溢,恰少年气盛,志向宏远。他希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尔后功成身退。该诗直言其志,反复铺陈,层次清楚,不枯涩板滞,情韵自然。
张问陶论诗反对模拟,主张“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43而写“真阅历”贯穿于其山水诗中。遂宁到成都的必经之地有一小镇安居,镇旁有一条安居河,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农田肥沃。船山由遂宁赴成都,在这里小住时,写了一首即景小诗《初冬赴成都过安居题壁》,云“连山风竹远层层,隔水人家唤不应。一片斜阳波影碎,小船收网晒鱼鹰。”诗人由远到近写出了家乡农村的景色,诗中有画,颇富情趣。而《重庆》一诗,既描写了山城岁暮的景色,又写出了自己徘徊于仕途的情怀。诗云:“腊鼓冬冬岁又残,巴渝东望尽波澜。风林坐爱相思寺,云水遥怜不语滩。一字帆樯排岸直,满城灯火映江寒。西行便是还乡路,惭愧轻弹贡禹冠。”
张问陶现存诗歌3552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亲情之作,以写兄弟之情最多44,仅明确提及兄弟名字的就有167首,占全部诗歌的二十分之一。亥白一生坎坷悲苦,仕途不顺,终身求仕未得。作为长子长兄,养家奉母全赖他一人支撑,“以家庭之事,忧愁抑郁”45。船山长年南船北马,不能守在父母身边以尽孝道,尽管父亲教育他以国事为重,船山仍有愧于不能奉养双亲,故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了对亥白兄奉养高堂的感激之情,更抒发了兄弟间的骨肉情深。如“几时共醉涪江月,细数游踪语夜残。”船山因生活窘迫,曾独居孤寂的古寺。望一眼周围,四壁秋星,一丛霜菊,想到自己终日陷于尘嚣,温馨亲情久违。仕途的挫折,生活的窘迫,人生的诸多不如意,凭添愁思,船山更加怀念亲人,曾有诗云:“白发高堂游子梦,青山老屋故乡心”,抒发自己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之情。
遂宁,是船山时刻思念着的故乡。“船山”得名显然是为了纪念自己的故乡。在遂宁县西,有一山屏立,林木丰茂,风光秀丽,远视其形如覆舟,故遂宁人以“船山”名之。46至今民间还有传说,云:“船山山如船,船山诗如泉。船山与船山,人传山亦传。”人山同名,相得益彰。然而由于多年随父亲在外漂泊,直至二十二周岁,船山全家得张顾鉴友人相助47,乘舟踏上返乡路。入成都途中,离家尚远,思乡之情急切,船山作《晓行》表达其归心似箭:“人语梦频惊,辕铃动晓征。飞沙沈露气,残月带鸡声。客路逾千里,归心折五更。回怜江上宅,星汉近平明。”乍见故乡,多少次梦里亲近过的故土就在眼前,张问陶的心情该是复杂又充满激动的,恐怕不仅仅“欣喜若狂”四字了得。望一眼一贫如洗的老屋,随身所带惟有一钱不济的破旧砚台,对缓解家庭经济上的困窘无济于事,但这些不能削减归乡之喜。想到从今往后,全家可以同欢喜、共患难,尽享天伦之乐,父母兴致勃勃地点燃蜡烛,招呼家人围坐在一起,举杯共贺返乡成功。不过,杯中酒却是靠典当官衣抵现买得。其《初归遂宁作》描述了当时归家时的情景:“北马南船笑此身,归来已是廿年人。敝庐乍到翻疑客,破砚相随不救贫。风露惊心怜病鹤,关河回首叹劳薪。高堂秉烛团栾夜,剩脱乌衣付酒缗。”
船山回到故乡,游历了蜀地的山山水水,遍览遂宁城乡庙宇,所到之处,皆欣然提笔,赋诗纪游。乌尤山景色幽美,无论是三江春涨,还是烟雨秋波,都极富诗情画意。其《嘉定舟中》48赞美:“凌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湲抱郭流,绿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面看乌尤”。个中的诗情画意只有对故乡有着深情厚意的船山才能写得。1991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曾游乌尤山,连声赞叹此诗“写绝了,写绝了!”船山留下了大量题咏故乡之作。据《张问陶年谱》作者胡传淮49先生查检,清代所修四川府州县志中,三分之二的志书《艺文志》部分,都收录有张问陶的题诗。然而,深爱着故乡的船山一生都在忍受着乡愁的煎熬,“相思莫道天涯远,明月一轮共此秋。”船山盼望有朝一日能叶落归根,却因贫病交加,客死苏州,抱憾终生。
在张问陶的性情诗中,爱情诗、悼亡诗尤见其至情至性。张问陶一生娶过两个妻子。原配周氏,系名门千金,其祖父周煌为清代学者、文学家。官至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蜀中张氏与周氏为世家望族,清代四川人物官位最显著者,莫过于张鹏翮、周煌、卓秉恬三人而已。周氏之父周兴岱,周煌第二子,号东屏,官至晋左都御史。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船山第一次入京,奉父命与周氏完婚。婚后,一直住在岳父家。次年,名落孙山后带周氏回汉阳拜见父母。途中产下小女阿梅。从汉阳返回遂宁途中,周氏滞留在故乡涪州老家休养病体。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周氏卒于涪州,不久,小女阿梅也夭折。功名未成,又痛失妻女,船山命运不幸至甚。
继室林颀,字韵徵,号佩环,是真正与船山相伴终生的伴侣。林佩环是四川盐茶道林西厓的女儿,世传其天姿秀色,又工书善画,被誉为四川才女。佩环与船山相识时,正值船山功名淹留又赋孤鸾之恨,林西厓欣赏其博学多才,是个经世少见的奇才,毅然将爱女许配与他。为了表达对岳父的感激之情,船山作《丁未九月赘成都盐茶道署呈外舅林西厓先生》,有句“浑河九曲终千里,大鸟三年始一鸣。惭愧祁公能爱我,夜窗来听读书声。”知遇之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佩环不爱千金美少年,独喜轻狂穷书生,足见其独到的识见。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张船山与林佩环结为伉俪。婚后,夫妻吟诗作画,琴瑟相谐,表达彼此倾慕之心。林夫人出身名门,美丽多情,颇有大家闺秀之风范,船山对其美貌赞不绝口。《斑竹塘车中》50诗云:“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但教弄玉随萧史,未厌年年踏软尘。”该诗不拘礼法而抒情自然,不仅夸耀妻子的美丽,表现闺闱之乐,更大胆嘲弄理学,足见船山是十足的性情中人。新婚不久,船山再次入京应试,佩环则留在成都。两人新别,异地相思,彼时船山居于松筠庵,以诗寄托眷念之情。如闻到佩环小病时,作《得内子病中札》51诗,云:
同检红梅玉镜前,如何小别便经年。
飞鸿呼偶音常苦,栖凤将雏瘦可怜。
梦远枕偏云叶髻,寄愁买贵雁头笺。
开缄泪涴销魂句,药饵香浓手自煎。
“飞鸿呼偶音常苦”,道出了离鸾弧雁的哀痛,更有“栖凤将雏”的劳苦,因而益增加对夫人的怜爱。“梦远枕偏云叶髻,寄愁买贵雁头笺”,则写出了一种相思、两地闲愁之苦。“开缄泪涴销魂句”一语,将夫人的哀怨离愁,推向了又一境界,从而勾起了对夫人病情的忧思。离愁恻恻,萦纡于怀,哀怨动人。写离别之愁情,可谓如泣如诉。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七日,鹊桥相会之日,船山作《七夕忆内》52,“人间风露遥相忆,天上星河共此情”,“他家儿女无离恨,隔院微闻笑语声”。缠绵悱恻,情真意切。两人的情深意笃,才艺的吸引则是更深层的原因。佩环对有才子之称的船山自然由衷钦服,而船山对佩环的才艺也同样十分欣赏。他对妻子充满真诚的赞美之词,比之著名才女谢道韫:“袖中已遂襄阳癖,林下尤逢谢女才。”53还常常自叹不如,《内子以针线贴索诗为题长句》诗云:“一编尽有诗情味,夫婿才华恐不如”。曾描述了两人常常相互切磋,探讨诗书艺术:“学书且喜从吾好,觅句犹堪与妇谋。”54赏爱之情毫不掩饰。而才艺倾慕之外,更有着禀性的投合。二人同样淡泊名利,甘于清贫。船山《春日忆内》55云:“房帏何必讳钟情,窈窕人宜住锦城。一事感卿真慧解,知余心淡不沽名。”这高洁的情怀支撑着二人风雨同舟,历经沧桑,恩爱如初。
乾隆五十八年,船山三十岁,官至翰林院,接妻子来京师同住。京官翰林位尊人贵,但俸薪微薄,幸得夫妇彼此相依,并有一群诗友互相唱和,日子过得平安满足。诗友法式善生子,取名桂馨,佩环画桂一枝祝贺,船山写题画诗,云:“我有画眉妻,天与生花笔。临稿广寒宫,一枝写馨逸。”56诗工画好相得益彰。船山曾为妻子画像,佩环遂在画上戏题一诗:“爱君笔底有烟霞,自拔金钗付酒家。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57诗中表达了以嫁得船山为夫的自豪与快乐。船山依韵和诗:“妻梅许我癖烟霞,仿佛孤山处士家。画意诗情两清绝,夜窗同梦笔生花。”58好一对夜窗同梦、诗画清绝的佳偶,抒写着莺歌燕语的千古恋情,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
嘉庆十五年,船山四十七岁,迁山东莱州知府,携佩环一同前往。一年后,船山假病辞官。在前往苏州途中的临城驿上,逢佩环生日,回首人生,感慨唏嘘,功业未成,壮志东流,惟有夫妻情笃,可堪慰藉,而来日不多,犹须珍惜。船山欣然提笔为妻子作寿诗,云:“膝前雏凤鬓堆鸦,小婢齐簪寿字花。”“野店杯盘春酒熟,绿荫相对惜韶华。”59真可谓相依为命,伉俪情深。有意思的是有人在互联网上把张船山林佩环夫妇和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卓文君司马相如夫妇等并列于“中国古代十大知音夫妻排行榜”。
张问陶不仅对续弦佩环一往情深,就是对亡妻周氏也长期怀念。他的悼亡诗共有十三首,多抒发对亡妻的思念和人生无常的无奈和惘然。乾隆五十七年,船山携妻子佩环、女儿枝秀与兄亥白一起由成都返遂宁,途经涪州,触景生情,写诗悼念周氏及亡女阿梅:“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60周氏去世二十八个年头上,船山辞官离任途中,望着车中的妻女,回忆起前妻周氏与女儿阿梅相继谢世,船山苦笑:“舟中细弱谁还在,眼底河山我仅存。重补鸳巢如隔世,再来鸿爪又留痕。闺房也有沧桑感,可笑愚公计子孙。”61船山不愧深谙浮生梦,善把闺闱化沧桑。其闺情之作,表达了深切动人的伉俪之情,以其不同流俗的至情至性而广为人们推爱。
志行高洁、耿介亢爽、幽默诙谐、机敏过人
张问陶志行高洁,耿介亢爽62。他曾写过咏梅、咏兰诗,赞誉“自是不开开便好,清高从未合时宜”的梅花“最是人间极品花”63。而梅的“天生不合寻常格”,兰的独具神韵,正是他超凡脱俗的真实写照。张问陶诗歌中有一些属于游戏之作,是他幽默天性的真实袒露。遗憾的是除了《船山诗草》为世人常见外,有关船山的文字资料的记载世人知之甚少,故其风趣诙谐后世少有人知。其实,在清代笔记小说、野史中,对于船山的幽默天性有一些记录,而《船山删剩诗文钞》的《船山删剩文集》部分,涉笔有趣,尽显船山幽默本色。据《船山散记》64记载:某日船山游文昌阁,游毕回顾,见一名曰窝瓜者。船山默计此非佳名,不敢即以窝瓜相呼,乃询其姓。此人毅然自任曰:“我窝瓜刘也。”细审其状亦平平犹夫人耳。下楼途中遇一跛,冠白氊鸭尾帽,着油腻衣,面秽而肥,浮蹩而来,随从指曰:“此窝瓜刘也。”船山大疑,以为“窝瓜分矣,不然其瓜代瓜破瓜剖瓜副乎?何访一瓜而得两瓜也。”有感于一窝瓜之称而人乃争之如是,船山纪之以为争名者戒。文中作者以调侃的笔调对争名夺利者的行径予以讥刺,阅之妙趣横生,读者于不经意处得见船山天性中潜隐着的幽默与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