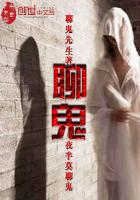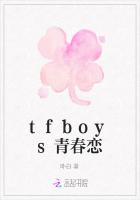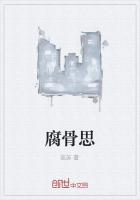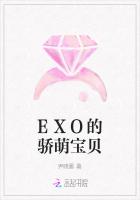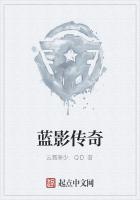船山为人做事但凭情之所至,嬉笑怒骂,毫不掩饰。妙批八股文,亦见其幽默本性。他任登州府主考时,曾以《伯夷叔齐》命题。因考文规定为“八股文”,有个考生便沿袭八股文法,用“伯”二股,“夷”二股,“叔”二股,“齐”二股。船山阅后,哑然失笑,于是批曰:“孤竹君,哭声悲,叫一声我的儿啊,我只道你在首阳山下做了饿杀鬼,谁知你被一个混帐东西做成了一味吃不得的大(炸)八块!”65这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讲过的某考官模仿纪晓岚批改学生作文的做法,以“一等放狗屁”;“二等狗放屁”;“三等放屁狗”划等加批三篇蹩脚文章可谓异曲同工。
张问陶还极为精明练达,具有超人的才智。《新世说》曾谓:“张仲冶以翰林出守莱州,时有剧盗,桀骜狡诈,供词累翻异。巡抚、方伯皆久不能定案,乃请张问陶讯之。张问陶仅三日,即将此案作结,而该盗又一一供出实情,终无翻异。巡抚及方伯亦为此大为惊服。”66张问陶的判词也写得情理交融。在一起顶凶卖命案的判词中,张问陶说理时辅以道德情感来褒贬案件的是非责任。对于将儿子卖于他人顶凶而险些酿成冤案的王桂林的责任认定连用4个比喻,说理十分形象。判词如下:“熏蚊虻以烧艾炷,恐坏罗帏,剔蚯蚓于兰根,虑伤香性,治恶僧须看佛面,挞疯狗还念主人”。判词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将“本府为爱护孝子心”的抽象思想,表达的形象可感而又便于理解和接受,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判词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怒斥了行凶之人,如“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又如,判词指出凶手屈培秋第一次行凶“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次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67船山精于律事,敏于听断,巧于折狱,其判牍堪称古代判词中的佳作。
儒家入世情怀为主,杂取释道思想
张问陶的思想比较复杂。他的思想中有儒家的积极入世,同时又吸收了道家的淡泊名利、超物绝虑,还兼受佛“得失过眼空”的影响。儒释道思想在船山一生中始终是相互依存、彼此消长,而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只是在一定时期,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有时又是佛老思想占据上风。船山一生作诗四千多,现传世三千余首,言志诗占有不少的比重。这些言志诗篇或闪耀着船山积极进取、忧国爱民、清白严正、穷不堕志的高风亮节;或寄托着船山黄尘已倦、归隐山林的隐逸思想;或抒发着船山对人生如梦,祸起红尘的感慨。
如同大多数深受儒家人文思想浸染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张问陶受时代风气和家世传统的影响,以儒家的“修齐治平”为主导思想。少年张问陶幼承庭训,聪慧异常。沐浴在“家风贫尚守”,“相业史重编”的流风美德下,耳濡目染的是儒家的传统人格模式。八岁随秀水(浙江嘉兴)马杏里师课读,努力学习,发奋进取。在父亲升授云南开化府以前,问陶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为人仁厚、责任心极重的张顾鉴让少年张问陶感受到了父爱如山,更教给了他为人做事的原则。后张顾鉴赴任云南途中,在洞庭湖舟中还不忘给问安、问陶写了一封家书68,告诫儿子“要做一个真诚仁爱之人,不可作刻薄寡恩之像”,“要恭敬待人,敬人人敬,爱人人爱”。勉励“两儿当存卧薪尝胆之心,励沉舟破釜之志,做映雪囊萤之事,学孝弟忠厚之人。”高祖“无财累子孙”的遗训,祖父和父亲的廉洁正直、安贫守道,在张问陶的思想、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乃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十五岁时写下了第一篇存诗《壮志》,怀着“隐轮匡时略”的雄心,抒发出“慷慨对中原”的激情。求取功名、事业奋发的气概跃然纸上。诗以言志,《壮志》以及稍后所写的一些诗篇,如《汉阳》、《寓目》、《杂感》等,已充分地表现出他青少年时期的气魄胸襟,流露出这位才华横溢、相门之后的少年渴望建功立业,承继世代官宦事业的恢弘之志。在困居江汉的岁月里,“六诏亲庭远,三巴归路长”。父子远离,乡愁惟苦,兼之过着“饥来百事非”,“人谁足稻粱”的贫困生活,苦不得志,感时伤事,船山曾慨叹“举世不逢孙伯乐,一生惟哭贾长沙”69。面对岁月流逝,功业未就,船山忧郁而焦虑:“人间少壮无多日,莫待秋霜染鬓丝”70。但纵然落寞和清贫,他仍以“梅好不妨同月瘦,泉清莫恨出山迟”71自勉,高唱:“镬屈龙伸指顾间,英雄不下穷途泪”。“伏枥长鸣万马惊,唾壶击缺气难平”72。充分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字里行间流露着力图披荆斩棘,开拓新境,奋然向上的雄心。真可谓匹夫不夺志,贫困不能移。“报国济世”作为其早期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他人生的目标。尽管张问陶已敏锐地感受到这个“盛世”时代的沉闷委靡和对个性的压抑,唱出了“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73这样先觉者的悲歌,但他此时毕竟才年仅21岁,对黑暗的吏治缺乏感性认识,所以他一面早生栖隐心,一面又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74的近乎悲剧精神的入世态度,昂扬着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进入仕途初期的思想,仍然是青年时代思想的延续。
张问陶是一个志行高洁之人,在世事浮沉的世俗社会中努力保持着率真的个性。他渴望保持人格独立与精神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庄子的自然人本精神对中国古代文人作用的结果。张问陶一生持有恬淡的心怀和潇洒、达观的人生态度,虽置身仕途,却与官宦人生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他有《感事为坡诗下一转语》75诗云:“无灾无难不公卿,才算平安过一生。细领痴聋真妙处,始知愚鲁即聪明”,个中隐然有着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相较于苏轼《洗儿戏作》一诗来说,船山对世态的认识则更理性、更透彻。所以,司马相如“高车驷马惊乡里”的人生取向,在张问陶看来“只觉相如是俗人。”张问陶曾赋诗感激续弦林佩环对自己个性的理解和尊重,“一事感卿真慧解,知余心淡不沽名”一句,意在彰示自己的志趣并不在对功名的追逐上。在他看来,“身外浮名画足蛇”,科举、致仕只是报国济民的途径和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十五岁时就已有了“三十立功名”的远大抱负,但与此同时也立下了“四十退山谷”的功成身退的志向。张问陶看来,若空有科名,而才能不为所用,这样的浮名何足道哉!与其“桄榔林外老闲散”,“不如樗櫟终天年”。久陷官场,才华不得施展,船山宁可选择守拙自藏之路。在《尘海》一诗中他慨叹“行藏可叹人谁解?得失宁教我自言。”船山真的能够远离尘嚣吗?《观我四首》中可以找到明确答案。
《观我四首》由生、老、病、死组成,其中生死二首最能表明他的心迹。
生
芒芒生面忽重开,堕地先号事可哀。
瞥眼韶华因梦远,累心缘影为谁来?
名沉青史终无色,祸起红尘定有胎。
白业丹元修补急,万牛身重首空回。
生面重开者,为有轮回故也,此开宗明义第一句。佛学理论本于三世轮回之说,瞥眼韶华忽远,累心缘影而来,万法因缘生,是非原妄有。前尘往事,非梦影而何?今生重来,只红尘造业!船山所嗟叹者,唯业重力微,虽急急修补,亦难销此无始劫来之甚重业力者也。
死
胶革全崩傀儡场,岐雷医命竟无方。
千秋许我留真气,百事催人到夕阳。
谁把黄金求骏骨,且余一垅傲生王。
涅槃羽化凭仙佛,为想归途尽渺茫。
用了一辈子的胶革皮囊,一日舍之!“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生我以前谁是我,我死以后我是谁?惜今生事业未竟,归途茫茫。涅槃成佛,羽化登仙,于自己又有何干?船山既不能遁入空门,更做不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他仍执着在一个“我”字,踯躅于生死苦海。大概还在寄望于下一个轮回,以成就未完事业吧。
张问陶的家乡西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发源地,自东汉张陵在西蜀大邑鹤鸣山修道创立道教,巴蜀便成为中华道教的圣地。至今被道教界尊为发祥地的张陵结庐传道的青城山,传为太上老君降生并布道《道德经》的汉唐古关青羊宫,道教最早的二十四教区的遗址等星罗棋布地坐落于巴山蜀水。张问陶曾亲游千年古观青羊宫,赋诗:“石坛风乱礼寒星,仿佛云车槛外停。常为吾家神故物,铜羊一角瘦通灵。”四川遂宁佛文化很盛行,遂宁境内禅林古刹众多。建于唐朝的佛教庙宇广德寺,位于遂宁城西三里许的卧龙山,曾主领川、黔、滇三百余山,被尊为“西来第一禅林”。与广德寺隔涪江相望的灵泉寺,位于遂宁城东灵泉山,被誉为灵泉圣境、西方圣境,几与南海普陀山齐名。相传灵泉山上有泉七眼,常年泉水不断。苏东坡曾于石壁题书“七泉”,今“泉”字业已剥落,“七”字仍依稀可见。在我国民间,历代相传着一位循声而至、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遂宁当地有一首千年相传的民谣:“观音菩萨三姊妹,同锅吃饭同修行。大姐修在灵泉寺,二姐修在广德寺,唯有三姐修得远,修在南海普陀山。”观音文化现象的产生,缘于人们真诚、善良和美好的愿望,无论观音存在与否,遂宁却实实在在被称作“观音故里”已有千年了。张问陶一生好游,足迹踏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名刹古观,且每到一处,必赋诗记之,如《灵泉寺僧楼》、《拜广德寺》等。张问陶为人率直,善于交友,高僧中与其关系佳者甚众,《船山诗草》中就有数量可观的与高僧间的唱和赠答诗。
据笔者查检,《船山诗草》中直接论佛或与佛有关的诗歌共有60多首,而且中年以后船山也的确好谈佛论道。他在家里筑了绣佛斋、宝莲精舍,还曾着过僧装,且别号宝莲亭主。在《绣佛斋》中云:“萧斋本无佛,乘醉偶逃禅,偏惹知诗婢,铜瓶供白莲。”76其《禅悦》诗之一云:“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77八万四千是印度最常用的数字,极言其多。方寸指心而言,学佛的法门虽多,归根结底还是方寸之地的心。其《元夜月下作僧装访沧湄》之一云:“儒衣不著著僧衣,今昔何曾有是非。觅我本来真面目,袈裟也化白云飞。”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他真的想了却尘缘了。然而,这些不过是表象而已。船山对佛门的态度,可参考陈其元《庸闲斋笔记》里所载他与洪亮吉同讥佛事的一则小插曲:
船山先生与洪稚存太史亮吉,皆为大兴朱文正相国门下士。相国好佛,尝于生朝诸弟子称觞之际,太史袖出一文上寿。相国固喜其文,亟命读之。太史亢声朗诵,洋洋千言,多讥佞佛事。诸人大惊,先生独大笑叫绝,相国大怒。坐是沦踬有年,先生不悔也。太史后以上成亲王书言事,诏下狱。狱急,亲友或对之哭,太史口占一绝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头颅好,须为朝廷吃一刀。”闻者皆破涕为笑。赖上圣明,卒得释还。
另外,船山在《道意》诗里,也道出了其心并不在空门和山水间。
我心妙处即天心,一筏宁愁孽海深。
但望人皆修性命,须知道不在山林。
龟龙蟠水朝神观,花鸟随风散法音。
火记无传仙药幻,烧丹何日变黄金?
由于佛教的观念是通过道教的范畴而被引进中国,并且,道教又得益于借取了佛教的建制与仪式,所以佛教与道教有相通相容之处。比如佛教的出世思想与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推重少思寡欲,清静无为。然而,庄子所标举的“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物我两忘”的理想人格境界在现实中是难以实践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终不能完全割断与尘世的牵连,这连庄子也无法做到。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至人”、“神人”,是以思维的至上性取代了现实的真实性,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同样,学佛,目的在于求解脱,度一切苦厄,这自然也是幻想。林语堂在论述关于佛教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时,说佛教一方面给中国士大夫心灵以滋养78;另一方面也在于在乱世时,能为士大夫提供避难所,具有“活命价值”。可以说,佛道两家在把知识分子从尘网中解脱出来这方面,是殊途同归的。
一般来说,当制度初建和社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时候,文人们的情绪便格外高涨;而一旦由盛转衰,也就向着标志着超脱的佛老精神境界转移。在天崩地解、战乱甫定的清初社会,儒家化曾经达到了高峰。但是随着“乾嘉盛世”以降,清王朝如同一个熟透了的瓜,蒂落瓜烂已指日可待。政治的黑暗、吏治的严酷、官场的积弊,理想的火种一点点地熄灭着,激情的涟漪一点点地破散着。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船山还奢望着为朝廷重用的话,随着久陷官场,才华不得施展,他宁可选择守拙自藏之路。所以中年船山已雄心不再,开始慕山谷、思道仙、想佛门,向往天外之思的归隐生活。其有句云:“已避名场避酒场,中年始觉爱春光”。嘉庆四年,与张问陶情同手足的好友洪亮吉因直陈时弊获罪流放,对他是又一沉重打击。船山耳闻目睹的是,德修而见弃,才高而不遇。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成了高尚者的墓志铭。基于此,他创作了大量厌倦功名、倾慕隐逸的诗篇。如《踌蹰》、《夏日即事》、《早秋慢兴》、《人日偶作》等,或表归隐之心,或赞隐居之趣,或写田园风光。这种超尘出世的人生归宿,也是诗人永远的向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