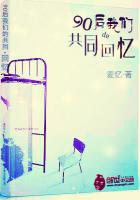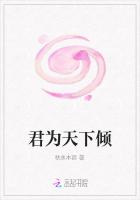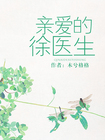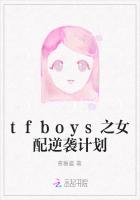性灵诗重写真性情,张问陶对苏轼的家国情、人民情、乡情、亲情都予以高度赞誉。自古以来,忠孝义节,被视为百行之冠冕。三苏父子关心朝政,父苏洵针对北宋贫弱现实,提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革新主张;弟苏辙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副相),亦多次上书,针砭朝政。但其身居廊庙不为重用,与船山闲居翰林院无异,故船山叹曰:“廊庙虚贤相”。兄苏轼关注朝政民生,政治上见解独到,怀着对国家的忠义,多次上书论朝政得失,不肯阿谀奉承,一生浮沉于残酷的党派之争中,宁遭放逐亦不改初衷。身陷囹圄,还高声吟唱着“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161其一意孤行,足见其忠孝心长。“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其《山谷集》里,论先生书法与人品的内在关系时,谓其“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逼近于“浩气贯长虹,忠义填骨髓”之境地。张问陶曾以东方朔上书四十四万言为楷模,立志“为天子大臣,上书继臣朔。”162他赞苏轼“忠孝真诚宁放逐”、“文章事小功名大,忠孝心长意气孤”、“忠孝古人情”等诗句,皆注目于其对国家的忠义之心、对黎民百姓的至情至义。此情此义,无人堪追。
张问陶也将苏轼对亲人的情义作为评论的内容。二苏兄弟不惟文学上珠联璧合,在政治上以及日常生活中也相依为命。他们以文采议论为华,以孝友谦慈为基,共同奏响了一曲千古悠悠手足情。可以说,从来兄弟埙篪之乐,未有过于二苏者。乌台诗案,苏轼原料难逃劫难,狱中写下绝笔,“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弟兄,又结来生未了因。”163诗中没有对死的恐惧,萦绕不散的惟有内心深处的对弟弟子由的留恋。船山常以二苏兄弟情深喻自己和亥白的手足之情。当亥白从南海郡再归眉州之日,他兴致勃勃地写下了《出江口》一诗,“前身果坡老,我必苏子由。”用东坡比亥白,以子由拟自己。苏轼对爱情更是一往情深。苏轼与妻子王弗感情甚笃,王弗每每红袖添香,伴夫君夜读,又随苏轼辛苦辗转。无奈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即病逝。幽冥隔世,生死相别已十年,苏轼仍哀思深切,以致幽梦还乡,字字泪垂地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船山原配周氏年仅二十早逝,他继娶林佩环后,夫妻“夜窗同梦笔生花”,却仍写下了多首悼亡诗追忆周氏。“世间甲子须臾过,半局残棋已廿春”,164写别鹄离群的悲凉,哀惋欲绝至极,情深不下《江城子》。
抒写乡愁,是张问陶性灵诗的重要内容。他曾几次借苏轼至死未得回归故里,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一是辞官后至常州瞻仰苏文忠公祠,吟诗“此中曾有未归人”165。一是在《东坡雪浪斋铭拓本为颐圆通政题》诗中,援引苏轼雪浪石铭166中的文字“蜀两孙”,来比自己和乡贤苏轼,叹“乡思谁谈蜀两孙”,“相招同有未归魂”。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因先后不容于改革派和守旧派,在仕途上几起几落,被贬达十余年之久。也曾因诗文获罪,“乌台诗案”甚至几丧性命。苏轼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然而,其旷达则更让人敬佩。在沉浮不定的人生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力。横遭贬谪也好,自请外放也罢,都没有使他颓唐丧志。不管身居何处,无论爵位高低,他都能随遇而安,有所作为。于是便有了西湖种柳、赤壁泛舟。黄州虽然嘈杂,但可以“长江绕郭知鱼美”,惠州尽管偏远,却能够“日啖荔枝三百颗”。道家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身上已表现为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据《东坡事类》记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诫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此语深为船山喜爱,他说自己“醉中颇爱东坡语,世上从无不好人。”苏轼的思想出入儒道,杂染佛禅,既能关注朝政民生,卓尔不群,又能随缘自适,达观处世。屡遭贬谪,宦海浮沉,终以融道、释诸家哲学以自救,逆境中泰然处之。庄子《齐物论》中“一生死,齐彭殇”,是说道家不被一切束缚,对于形而下的东西,能轻轻松松地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承载。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之句,表现出道家旷逸豁达的人生态度。受道家思想影响,张问陶也认为“彭殇一过总徒然”。嘉庆元年(1796)腊月十九日,张问陶与赵味辛、温谦山两舍人,方茶山、伊墨卿两位比部,温筼坡、洪稚存两位编修,集于洪亮吉的卷施阁,为东坡先生生日设祀,并摹东坡笠屐图,船山题长句为纪:“我为乡人夸坐客,公留生日醉狂奴。”第二天,彭田桥来访,宴席中,船山又绘一幅东坡先生像,并再次题诗“文光可止照峨岷,再拜先生画里身。”可见船山对东坡先生崇拜神往之情几欲沉迷,并以与东坡同乡而自豪。两年后(1798年),再题《东坡笠屐图》云:“纵横奇策才终累,忧患余生遇转安。”叹东坡居士天纵多能,为才所累,所幸其随遇而安,乐天知命。船山赏苏轼“看彻幽明”,誉为“坡仙”,甚至要“学制坡仙真一酒,167醉骑蝴蝶到华胥。”苏轼在幼子苏过满月时有《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张问陶读诗后,作《感事为坡诗下一转语》诗,云:“无灾无难不公卿,才算平安过一生。细领痴聋真妙处,始知愚鲁即聪明。”就诗歌本身而言,张问陶对世态的认识较苏轼更理性、更透彻。但他毕竟缺少苏轼悠然于俗世的气度,也就难逃其如大多数文人一样的悲剧一生。
遂宁张氏家族乃诗歌世家,后人有“一家男女尽能诗”之说168。张问陶对苏氏文学世家也赞誉有加,誉其“一门无俗物”。169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以诗词文章在北宋时称雄于文坛,文学史上称为“三苏”。一门父子共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之林,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而且三苏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优秀的思想家和经学家,他们在经学领域也造诣非常。巴蜀的《易》学,源远流长,独擅其美。“三苏”父子生活的眉山地区,士大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师”170。“三苏”父子锺巴山蜀水之灵气,集“蜀学”成就之精华,易学也成了苏氏一门的传家之学。苏辙诗曰:“家传《易》、《春秋》,未易相粃糠”,171正是对这一家学传统的独白。苏氏父子跻身于北宋蜀学主将之列,他们合力所著的《苏氏易传》172,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173张问陶说“《易》传家学妙”,概括出了易学乃苏氏一门的传家之学,并于其时引领风骚。苏轼的第三子苏过,在当时颇有声望,人以“小坡”称之。苏过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其文学造诣和成就酷肖苏轼,苏轼曾夸“过子诗似翁”174,“作文极峻壮,有家法”175。张问陶称誉其“健笔过先世”。176
苏轼的性格核心,乃是他的真率。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177此可作为对苏轼真率性格最好的评语了。苏轼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性灵。苏轼作品之中,或为即兴之作,或是心有不满而有感而发,都是顺乎天性的自然流露。他曾经对人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178“苏轼为人刚直,感情丰富,无论为诗为文,立言有体,不发空论,得之于心而出之于口,非为至情,即为至理。”179故无论欢娱或愁苦之语,自然皆能动人。苏轼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尝言:“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180他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提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81,“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182张问陶亦言:“丹青本游戏,挥洒定奇特。如何守斤斤,触手见淳饬。”183意谓艺术创作本来就是随心所欲,任性灵而为,当放笔挥洒,戒墨守陈规。这与苏轼的文学主张相契,故称道苏轼“文章嬉笑亦经纶”。苏轼诗歌的“自然天成”,得到性灵派副将赵翼的高度赞扬。《瓯北诗话》言:“坡诗有云:‘清诗要锻炼,方得铅中银。’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赵翼认为苏轼诗妙在不加锻炼,在心境空明的情况下,自然流露其感情,浑然天成,全不着力,所以“独绝”。184张问陶也论苏诗之“真”:“写真何处想髯苏”,“醉眼模糊易写真”,指出了苏诗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而同本性情之真。更论苏诗“真”之根源乃“《诗》逼长公真”。船山《蟋蟀吟》云:“《诗》三百篇,大抵贤人发愤之所为。”他认为苏诗天真无邪,真情不伪,乃继承了《诗》以道性情的传统。船山是论可谓精当。苏轼一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他将对国家、民族、百姓的至情,倾注于笔端,发出了“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之声185;写出了揭露统治者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而“惊尘见血留千载”的《荔枝叹》。其作品的笔力实不下于小杜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可以说,“《诗》逼长公真”,准确地道出了苏轼创作继承“诗以道性情”的传统,又与时代相结合的特点。这是船山独到的见解。
宋代以学问为诗,从书本中寻取创作材料,导致诗歌拘谨枯瘠。苏轼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将其化为诗料,诗歌便充满了勃勃生机,故能避免许多宋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诗可以作为张问陶的“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的注脚。而且苏轼的创作在跌宕起伏中,一任感情释放,把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诗已不见世人的拘谨。张问陶评云:“宋诗多拘儒,惟公有生气”,针砭了宋诗的死寂、缺乏活力,赞赏苏轼诗富有“生气”,具活泼灵动机巧之美,达到了超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苏轼潇洒多才,其坦荡胸襟,独绝文章,令人叹为观止。故姚莹说苏诗“妙语天成”186,赞其妙绝难以追寻。苏轼作诗磊落俊伟,最具气格。张问陶无意于以诗人自居,却有“本朝一大名家”之目。苏轼爱作文章,也无意于以诗文自见,为古今学士所不能及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其磊落天生,确实是学不来的,故船山赞其“诗才磊落难为继”。
东坡诗歌之外的影响,林语堂1908年写的《苏东坡传》187有明确的评价。称苏东坡是:“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放任不羁,又随缘自适,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其实,约在林语堂之前百年,张问陶就充分肯定了苏轼的地位和影响。如既赞其“文光可止照峨岷”,“公之灵光满天地”,又言“岭海妙能恢壮志,韩苏好不在诗名”,说苏轼不惟以诗有名于世,也因其恢宏之志而名垂千秋。诗句“乡人自昔夸汉京,我今一笑皆平平。子云相如文士耳,安敢与公争大名”,则说杨雄、司马相如以词赋卓然于世,一直为蜀乡人夸耀。但是,二人知名仅在词赋,只能以文士相称。张问陶该诗亦在力证:苏公之大名,岂一般文士所能争焉!而“因公爱眉州,便觉眉州好”之句,更有爱屋及乌之意。然而苏轼的魅力并不惟于此。他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其处世精神,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他懂得一切须当顺其自然,因为与世俗一直保持着一定距离,所以能处在悲观与执着的此消彼长的平衡中。此乃苏轼人高一筹的地方,也是张问陶竭尽全力,却终其一生无力企及之处,因而便对苏轼更是钦佩有加。
杜甫和苏轼俱为张问陶所推崇,诗句“东坡西阁188吾兼爱,欲就诗魂与唱酬”是为证。散见于《船山诗草》中的论杜甫的诗句并不少,但专为杜甫而作的诗篇却仅见两篇。张问陶不惜重墨,以九首诗歌专论苏轼,足见苏轼是历代诗人中至为张问陶推崇者。
元好问是我国文学史上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自金、元以后,文学批评家称他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工”189,比之于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陆(游)190,是集大成者。元遗山得到后世景仰,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忻州知州汪本直重修元遗山墓191,船山居京师任翰林院检讨,得知后欣然题五律二首以寄,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船山客观地评价了遗山之为人为文,论其忠心爱国,也评其文学创作成就,更衡量其诗学建树。
遗山是继苏、黄以后最负盛名的诗人,金元两代,就诗家地位而言,遗山位居第一,也无异议。昔遗山论诗有“诗到苏黄尽”之叹192,今船山以“名重苏黄后,金元笔一枝”誉遗山,并非溢美之词。遗山才华横溢,而其一生致力于诗学,尤得诗歌创作之旨趣。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揭其诗论主张。尤其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体作《论诗三十首》,篇幅更为宏大,内容更为丰富,影响更为深远,后代仿遗山论诗绝句者代不乏人,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巨匠地位。他在诗论史上的贡献,谢启昆极赞,其《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云:“慷慨论诗句有神,苏黄以后导迷津。不封沧海横流日,争识扶鳌立极人。”吴世常辑注《论诗绝句二十种》更赞其“立论之精当,非惟针对时弊,有起衰救弊之功,且亦影响后世非一代也。”193船山以诗论诗,是沿着戴复古重在阐述诗歌理论的路子而行。但在具体论历代作家时,其重视作家的品德,显然受到了元遗山的影响。而且遗山论诗贵自得,反模拟;主张自然天成,反对伪饰;主张真诚与雅正,都与船山的诗学观相合。船山推崇遗山之才,尤重其论诗,故一言以蔽之:“才高许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