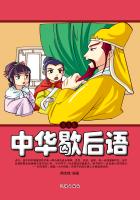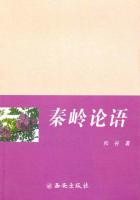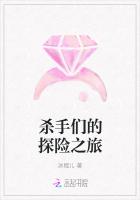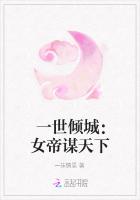元好问还是金代著名的史学家。金亡后,作为金朝元老,他以史事为己任,广泛搜集历史资料,以数百万字的《壬辰杂编》、《中州集》、《金源君臣言行录》等著述,保存金代文献和史实,成为研究金代文学、史学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后代学者修撰《金史》,多本其说。可以说,如果没有元好问,《金史》的内容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张问陶论元遗山在金史的地位不可或缺,总结为“史难因我废”。遗山尝任中央和地方官吏,尽心竭诚,关心国家兴亡、民生疾苦,政治声誉甚高。中年以后遭逢乱世,饱经忧患,将遗民之悲,故国之思,深寓在他的诗作之中。其丧乱诗继承了辽文学任情率真的传统,194以其诚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成为继杜甫之后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遗山是历史上的大不幸者,他不仅命运多蹇,还得不到当世的理解,诗人直至卒前仍心有余悸地嘱其弟子立墓碑只题“诗人元好问之墓”195七字,不言其它。关于元好问的气节问题,也一直是后世聚讼纷纭的焦点。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学者着力从文化角度为遗山辨白,认为元好问虽为崔立撰碑,但秉笔直书,没有歌功颂德,谈不上失节。上书耶律楚材,觐见忽必烈,保护人才,维护中原先进文化,这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应予以肯定。这一观点体现了当代学人名节观念的更新与进步196。难能可贵的是,近二百年前,张问陶已摆脱了封建名节观念,赞遗山“世乱能全节”。而对遗山未充分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真正价值,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政治品德下一断语,寄予理解和同情,叹其“忠亦畏人知”。
张问陶论清代作家
张问陶论诗主创新,明诗存在复古与摹拟之弊,故于明诗人未评一人。有清一代,诗人甚多,仅《船山诗草》中直接或间接提到的清代诗人就逾八百,但张问陶惟取乾嘉诗坛的诗人与诗作而论197,且态度明确,褒贬分明。贬斥者有以学为诗、以考据为诗的翁方纲之流,以及规摹唐人、持“诗教论”的沈德潜之辈;赞誉者有袁枚、赵翼、孙星衍、吴锡麒、毕沅、王昶、法式善等诗坛前辈,还有门生崔旭等人198;有洪亮吉、陈登泰、戴敦元、朱文治、郑大漠等同年,也有诗友、画友王学浩、吴鼒与黄易,还有四川举人彭田桥、朱紫坊名儒郑大谟等地方名人。重点论述了和他情同手足的洪亮吉以及性灵派主将袁枚199。
妃红俪白太纷纷,伸纸如攻合格文。
我爱君诗无管束,忽然儿女忽风云。
(《题邵屿春(葆祺)诗后》诗草卷十)
(评邵葆祺)
王郎袖得神仙笔,幻出云山风雨疾。
雄奇淡远无不宜,肯学倪黄拘一律。
(《栈中怀王椒畦》诗草卷三)
南海之大不如天,作诗何至夸登仙。
王郎下笔真神解,画出君诗满沧海。
(《题王椒畦画亥白兄过海图》诗草卷八)
输我三人齐下笔,性情图画性情诗。
夜雨泠泠画五连,王郎泼墨便天然。
(《题武连听雨图王椒畦作》诗草卷十)
妙诗奇画空余子,生作仙灵那能死。
(《椒畦病起与莳塘亥白携酒就松筠庵贺之即以送行》诗草卷十)
(以上评王学浩)
癯鹤临风意欲仙,斯人清净出天然。
文章不藉登科重,自我知名已十年。
(《赠同年陈户部琴山(登泰)》诗草卷五)
(评陈登泰)
敝衣汙更雅,乐讬见天真。
诗名甘我让,酒过与君同。
(《赠戴金溪比部同年》诗草卷十五)
(评戴敦元)
一月不相见,新诗陡胜人。
奇篇能磊落,淡语亦丰神。
志定原生慧,才高恐更贫。
聪明君自足,珍重葆天真。
(《题姚伯昂诗》诗草卷十六)
(评姚元之)
点笔何须画鬼神,破空奇语在能真。房帷写韵有传人。
(《题王铁夫(芑孙)楞伽山人诗初集》诗草卷五)
(评王铁夫)
大声疑卷怒涛来,愈我头风一卷开。
直使天惊真快事,能遭人骂是奇才。
(《题孙渊如前辈雨粟楼诗》诗草卷五)
(评孙星衍)
世间裘马皆年少,潦倒如予更有卿。
妙句怪多湖海气,相看原未拟儒生。
(《题彭田桥诗后》诗草卷二)
(评彭田桥)
高文随手似飞文,用尽奇书用典坟。
酒兴狂时惟让我,诗情豪处不如君。
闲游古寺题红叶,醉拓晴窗画白云。
自恨无权主吟社,骚坛封汝上将军。
(《送山尊归全椒》诗草补遗卷四)
(评吴鼒)
气盖岩疆心磊落,诗包全史论纵横。
(《题邲阳明府郑青墅同年诗集》诗草卷十五)
(评郑大谟)
东南名士推前辈,辇毂词人拜下风。
离亭举酒故交稀,话旧还携老布衣。
望阙情怀原恋恋,怜才心事最依依。
(《花朝赴陶然亭公饯王述庵前辈归故里》诗草卷十一)
(评王昶)
秀语标神韵,新城一瓣香。
声名在王后,端为老渔洋。
(《答杨米人明府》诗草卷十三)
(评杨米人)
诗中开悟境,象外写仙心。
迦叶此时笑,羚羊何处寻。
(《黄小松(易)作诗龛图寄法梧门祭酒为题一律》诗草卷十三)
(评黄小松)
清朝文网森严,文人大多埋头考据或堆砌典故,以至情采浅薄,文辞平庸。至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主张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从表面上看,一偏于宗唐,一偏于宗宋,其实在束缚个性上并无根本区别。张问陶不仅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荡涤有违诗道的各种不正诗风,还有意举出乾嘉诗坛许多抒写真情、诗风天真自然者进行品鉴。由于船山所论性情诗人甚多,限于篇幅,惟选具代表者以论,如邵葆祺、王学浩、陈登泰、戴敦元、姚元之、王芑孙等。
邵葆祺(生卒年不详),字寿民,号屿春,北京大兴人,进士,官吏部员外郎,有《桥东诗草》。因排行第五,人惯以邵五称之,船山将其比之“长爪郎玉川子”200。邵五与船山、亥白兄弟交往密切,诗酒唱和频仍。白莲教起义烽火燃至遂宁,邵五曾作诗吊悼牺牲的起义军,亦忧亥白之安危,船山依韵和诗《闻遂宁兵警邵五作诗相吊并寄怀亥白成都依韵酬谢》。邵五诗风接近船山,几乎难分彼此。船山《赠邵五》诗曾云:“君诗似我诗,几不辨尔汝。”无论是儿女之情,还是风云际会,只要不是外在强加的理性羁缚,而是发诸性灵的天真之作,都是船山所赞赏的。邵五诗无定法,不墨守成规,全然是“无管束”的率性之作,深得船山喜爱,云:“我爱君诗无管束,忽然儿女忽风云”。
作为画家,船山对当时的画家与画作也多有品评。清代画家兼诗人者众多,故船山论画又往往兼而论诗。清代中期,诗画领域视形式如敝屣,动辄言舒胸中意气,画坛上崛起了“扬州八怪”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他们强调抒发性灵,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极具性情。性灵画的画面简单,自得天机,在当时画坛独树一帜,富有新意,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在他们那里却有所削弱,王学浩等人倡导临摹救其弊。王学浩(1754-1832),字孟养,号椒畦,江苏昆山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后屡试不第。精画理,工书法,山水得王原祁正传,结构紧密,笔力苍劲。用墨能入绢素之骨,有霸悍之气。晚年又专用破毫,苍浑雄厚,脱尽窠臼,画风为之一变。王学浩亦能诗,光绪《昆山县志》载:时人比之李白、褚遂良,谓“白也诗无敌,褚公书绝伦。”著有《山南论画》、《易画轩诗录》、《灯窗杂记》、《毛诗说》、《翠碧山房稿》等。针对当时画坛性灵有余而传统技法不足之弊,王学浩《山南论画》有针对性地指出:“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但椒畦师法倪黄201,却非一味模仿,而是借鉴中又有创造,形成了或气苍骨劲、或随意点染的多样化的画风。故船山赞其“袖得神仙笔”,“雄奇淡远无不宜”。椒畦本不能诗,202与亥白相交后,在其影响下学习作诗。得亥白诗“语淡而味腴”203之真谛。椒畦诗语浅而意弥,是以船山又誉其“妙诗奇画”。王学浩为人恬澹旷适,绝意干禄,曾自序言:“年三十有八,一半性情以自见其身世。”204其诗一任性情而出,用墨也信手点染,生动传神,船山评其“性情图画性情诗”,又赞《武连听雨图》“泼墨便恬然”。
“天然”是一种浑然天成、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平淡”近乎天巧,属于“自然”的美学范畴,非一般人能及。船山推崇“天真”、“平淡”的艺术风格,认为“诗情画态总天成”205。其《莲花寺马器之宴上赠陈孝廉闻之若畴贵州人》诗云:“谩语谰言却近真,乱头粗服转丰神。”他也极力赞扬了天然之人、天真之作。
陈登泰(生卒年不详),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字子望,会稽人,著《拜石山房诗集》。《赠同年陈户部琴山(登泰)》曰:“癯鹤临风意欲仙,斯人清静出天然。文章不藉登科重,自我知名已十年。”言子望如瘦鹤临风,超然欲仙,以其脱尽世俗桎梏的自在状态,早富文名。
戴敦元(1773—1834),字金溪,浙江开化人,船山的亲家公。幼有异禀,十岁举神童,学政彭元瑞试以文,如老宿;面问经义,答如流。叹曰:“子异日必为国器!”年十五,举乡试。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历官道员、按察使、刑部主事,至刑部尚书。金溪“卒之日,笥无馀衣,囷无馀粟,庀其赀不及百金,廉洁盖性成云。”206善诗,有诗名,传诗数卷。《赠戴金溪比部同年》云:“敝衣汙更雅,乐讬见天真。诗名甘我让,酒过与君同。”张问陶赞扬他生活困窘,更见天真无邪之雅士情致。金溪诗歌成就不凡,乃至以“狂”得名的张船山也甘让诗名。
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竹叶亭主,别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船山庚申同年举人,嘉庆十年进士,历官河南学政,工部、刑部、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工书画。人们评其画风不染前人之法。有《竹叶亭杂诗稿》、《竹叶亭杂记》、《小红鹉馆集》等行世。姚元之继承了族翁姚鼐的诗文之法,以清丽之笔作淡语,略形貌而取神骨。张船山评云:“淡语亦丰神”。赞姚元之诗惟其精神内敛,全以淡语出之,亦具丰神远韵。检点姚元之诗作,船山是论可谓精当。姚元之有诗赞美千山207,他领悟了千山之灵性,用语极其简洁自然,却抓住了千山独特的群体英姿,道出了千山风光之秀丽、千峰之壮美,成为描写千山的绝唱。佛说“定能生慧”,所谓冰心不染尘,淡泊葆天真。船山认为“天真淡处能通慧”208,故寄语才气过人的姚元之一定要“珍重葆天真。”
王芑孙(1755—1817)清文学家、书法家。字念丰(一作沣),一字沤波,号惕甫,一号铁夫、云房,又号楞伽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官华亭教谕。工书逼刘墉,不期而合。吴门自明季以来,书家用笔,皆以清秀俊逸见长,至芑孙,始以遒厚浑古矫之,遂为三百年所未有。有“吴中尊宿”之誉。善诗,琴歌酒赋,为时望所推。著《楞伽山房集》、《渊雅堂集》。
王芑孙生性简傲,厌恶权贵,不肯从谀,人以为狂。妻曹贞秀(1762—?),字墨琴,安徽休宁人,工诗善画。王曹夫妇与船山交密,二人曾书写船山《论文八首》、《西征曲》八首合为一卷,赠与船山。王芑孙与曹贞秀夫妻唱和,留下了不少感情真挚的房闱诗。乾隆五十六年元月,船山居京师,与诗友洪亮吉、王芑孙、朱文翰等酬唱之际,闲暇作《题王芑孙楞伽山人诗初集》,欣言赞道:“房帷写韵有传人”。众所周知,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但在文学史上,除了民歌乐府诗抒情相对率真泼辣以外,大部分爱情诗比较讲究技巧的运用,在情感的表达上较为委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理学充斥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乾嘉诗坛,船山高扬性灵说个性解放的精神,在《春日忆内》诗中公开宣称:“房帏何必讳钟情”。他的爱情诗得性灵说之真谛,直写夫妻间的缠绵恩爱、情趣相投,反映了夫妻情深、伉俪之爱。《正始集》载船山夫妇“琴瑟谐和,得唱随之乐。”由于他的爱情诗有别于袁枚的泛情之作,包涵着人性真善美的崇高追求,在当时乃至今日仍广为流传。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张问陶主张无论是常语还是奇语,都要以表达诗人的真性情为标准。王芑孙为诗虽喜用奇语,但未失本真。船山赞曰:“破空奇语在能真”。
船山论诗重“气骨”奇高之作,故对孙星衍、吴鼒、彭田桥、郑大谟等人的诗歌予以好评。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一字季逑,号渊如,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榜眼,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方志学家。历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治经学,精诗文,与洪亮吉齐名,时称“孙洪”。晚年先后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南京钟山书院等处。所著有《周易集解》、《尚书今古文注疏》、《孔子集语》、《续古文苑》、《问字堂文槁》、《孙渊如诗文集》等。孙渊如深究音训文字经史之学,阮元誉其为“本朝不可废之大家”。作为经学家的孙星衍亦精诗文,时文坛祭酒袁枚主持风雅,尝跋孙星衍诗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读足下之诗,天下奇才也。”可见其文坛地位之显。孙星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而考明典章制度,对义理有颇具创获性之见,却遭到了理学家的责难。孙星衍坚持自我遭人骂,船山却赞其超越时人,乃“使天惊”之“奇才”,表现了船山张扬个性和强烈的独立意识。船山曾连日饮于孙星衍寓斋,故作诗奉赠,赞其“醉中奇气飞三雅”209。孙氏人有豪气,其“雨粟楼”诗裹挟着诗人的雄健之气,酣畅淋漓,气势磅礴,船山赞其雄肆不馁,形容为疑似声卷怒涛而来。
吴鼒(1755―1821),清画家,字及之,一字山尊,号抑庵,一作仰庵,又号南禺山樵,晚号达园,安徽全椒人。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进士,官侍讲学士。以母老告归,主讲扬州书院。善书画,工诗文,亦擅楹对。著《夕蔡书屋集》,编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山尊归全椒之日,船山赋诗赠别。云:“高文随手似飞文,用尽奇书用典坟”。船山反对以学为诗,但并不排斥学识在诗歌中的积极作用。山尊诗才天就,学识广博,船山赞其引经据典,高妙之文得来全不费功夫。吴鼒为人狂放,落拓不群,诗作中有的主张尽醉为乐,有的揭露世态炎凉。山尊诗情之豪放,船山愧不能及,云:“诗情豪处不如君。”所恨自己不能主盟诗坛,不然定封吴氏为“上将军”。足见船山对其歆羡之心。
彭田桥(生卒年不详),名蕙支,四川丹陵人,古文家彭端淑胞侄。嘉庆五年举人,工诗,著有《鹤梦轩诗集》。乾隆四十八年,船山全家困居湖北汉阳,彭田桥穷困潦倒,投奔在湖南为官的亲戚以谋事,行至汉阳与船山相识,成为莫逆之交,船山曾作《南台痛饮图》赠田桥。彭田桥为人豪爽仗义,诗中也充溢着纵横的侠义之气,故船山赞云:“妙句怪多湖海气”。
郑大谟(生卒年不详),字显孝,号青墅,闽县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任河南泌阳知县。朱紫坊名儒,林则徐岳父。所著《青墅读史诗》十卷。船山赞其《青墅读史诗》,以磊落公心,纵横论全史,气势盖山河。《题邲阳明府郑青墅同年诗集》诗云:“气盖岩疆心磊落,诗包全史论纵横。”
张问陶主张诗歌要“天真”、“自然”,但诗歌的境界并非滞着于物象的逼真描摹,而应该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那样,得其神而会其心,创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空灵之象,即以“无迹”之境写“有迹”之象,这一点与王士禛的“神韵说”有一致之处。从中可见他吸收了“神韵”说的有益成分,将王士禛的“神韵”说的审美意境融入自己的诗歌理论,丰富了自己的性灵说。他在论黄易和杨米人诗歌创作时,便是借严沧浪以禅喻诗和王士禛的“神韵”说而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