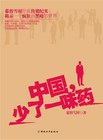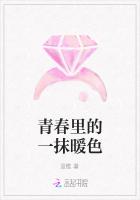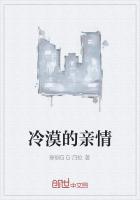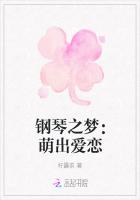张问陶诗论研究
及张问陶论袁枚、赵翼、洪亮吉1
清代中期的诗坛,充斥着“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又有宗唐派、宗宋派以及形形色色的羁缚才思、窒息情性、偏离诗之本质的诗学观念。袁枚继公安“三袁”之后,大力倡导“性灵”说以重新回归诗之本质。他认为诗歌是自我性情的表露,“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2“性情以外本无诗”3,甚至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4把“性灵”提到了创作最根本的位置。袁枚倡“性灵”说声势之大,乾嘉诗坛几乎少有人不受其影响,正如郭绍虞所述:“随园之诗论,虽建筑在性灵上面,却是千门万户,无所不至,他能‘笔阵横扫千人军’,在当时整个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张,都成为他的败鳞残甲。”5如舒位、郑板桥、黄景仁、洪亮吉、张问陶、赵翼、法式善6、宋湘7等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与袁枚是一致的,但又并非袁枚的影子,他们大都能够同中有异,合而不流,以其创作实践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与“格调派”、“肌理派”相抗衡的写“真性情”的诗派,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弥漫于诗坛的各种不正诗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但是,随着嘉庆二年袁枚去世,赵翼已耋髦之年,只有张问陶与舒位、孙原湘等人作为性灵派的后劲支撑着。所以王英志先生说嘉庆年间性灵说实质上“推张问陶为重镇,乃性灵派之殿军。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惟有张氏。”8
张问陶诗论兼与袁枚、赵翼比较
袁枚、赵翼、张问陶同主“性灵”,但无论是在诗歌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三家都同中有异,自成一家。赵翼重视“性灵”,主张创新,反对模拟古人,论诗主张与袁枚同调,9和袁枚一起共同影响了一代诗风。但其侧重点又非与袁枚雷同。赵翼重视诗歌以情感人的审美特征,他的“性灵”说的突出特点是“创新”。就论诗主张而言,张问陶深得性灵说的神髓,与袁枚、赵翼等互相呼应,故钱钟书先生说:“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宜以张船山代之。”10。但张问陶论诗主旨与诗歌创作一方面与袁、赵相通,一方面又合而不流,自具风格。当时已有人注目于此,如尚镕《三家诗话》云:“张船山之诗,多近袁赵体,亦能自出新意”。
张问陶性灵说的主要内涵是写真情、反模拟、求创新、诗中有“我”,又“博观约取,择善而从”11。其汲取了滋味说、神韵说等有益养分12,吸收了袁、赵性灵说的精髓而有所发展和创新,张问陶性灵说之完备程度不让袁、赵。如张问陶以“气”论诗、重视灵感,分别与赵翼和袁枚一致,但张问陶论述之丰富性,在论“气”和灵感时与“性灵”说结合之密切性上皆远超袁、赵13。另外,他还创造性地将“味”与“情”同时并举,从性灵说出发论述了“言情诗有味”。最难能可贵的是,张问陶论诗提倡“一代真诗笔,空言定扫除”14,“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15,“莫厌风尘俗,临民最有情”16,强调诗歌关注现实,深入生活,贴近百姓,公开标举“风雅”精神。其诗歌创作也多关注现实人生和下层人民的疾苦,尤其他后期的诗歌直接揭露现实,表现民生苦难,打破了以往那种认为性灵派只是抒写一己悲欢,表现个人才情的以偏概全的看法。这是张问陶对性灵说的突出贡献。他对性灵说的另一贡献则是与袁枚、赵翼遥相呼应,扩大了性灵派的地域影响,壮大了性灵派的创作队伍。所以,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小传》评曰:“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17
独抒性灵是张问陶诗歌理论的主旨
张问陶自十五岁写诗,以突出的创作实绩奠定了其在清诗坛上的地位。康发祥《伯山诗话》云:“自乾隆朝至嘉庆年间诗人如张船山者,诚不多观”。洪亮吉誉其为“长安第一”,特向袁枚推荐。其实,张问陶无意于以诗人自居,他写诗不过是心有所感,诉诸笔端,所谓“载酒供千日,逢山赠一诗”18。张问陶在诗中多次说过自己作诗不过是遣兴、消磨时光而已。如《秋斋遣兴杂诗》言:“挥洒丹青手,如吟遣兴诗。”《写诗》又说自己“闲吟冷醉昼迟迟,消遣流光笔一枝”19。而“钱癖诗名一梦过,何须开匣日摩挲”20,则表达了自己无意于诗名。基于此,张问陶没有像袁枚那样标榜自己主“性灵”说,他写诗全然是“蹑月穿云任所之”21。但他却以亢直的性格,恃才傲上的风骨,弃旧图新的诗风追求,不因袭、不摹仿,独开门户的进取精神,使其诗歌得到了当时乃至后世的称赞。张维屏称“先生官未昌而诗则大昌,年未永而名将愈永。”22已见的《清诗铎》、《湖海诗传》、《晚晴簃诗汇》、《清诗纪事》、《清诗精华录》等全国性的选本,无一不选张问陶的诗。而地方选本中孙桐生的《国朝全蜀诗钞》竟选张问陶的诗作五卷,共五百首以上。但生于袁枚之后,却是张问陶的尴尬。因为创作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时人有责其诗学随园者。所以,张问陶不得不公开申明自己的创作主张了。1794年6月,他特作《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诗,公开宣言:“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明确提出“性灵”一词,自此以后,《船山诗草》中大量采用“性灵”一词评诗、论诗。如:
愧我性灵终是我。
(《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诗草卷十一)
剩此手中诗数卷,墨光都借性灵传。
(《秋日》诗草卷十)
仗他才子玲珑笔,浓抹山川写性灵。
(《题子靖长河修禊图》诗草卷十)
五花八樄因人妙,也似谈诗主性灵。
(《壬戌初春小游仙馆读书道兴》诗草卷十六)
照影别开清净相,传神难得性灵诗。
(《梅花》诗草卷十)
同无青白眼,各有性灵诗。
(《冬日闲居》诗草补遗卷四)
笔墨有性灵。
(《戊辰日依竹堂感怀》诗草卷十七)
百年身世一浮萍,几盏醇醪养性灵。
(《五月初九日雨夜枕上作》诗草卷十三)
性灵偶向诗中写,名字宁防海外传。
(《朴宗善购诗作一绝句志之》诗草补遗卷四)23
此皆标举“性灵”论诗。张问陶论诗“性情”与“性灵”是通用的。但是“性情”一词提出的时间早于“性灵”、使用频率也高于“性灵”。早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就在《蟋蟀吟》、《秋燕飞》二首中使用了“情”,曰:“诗发乎情,情触乎遇,哀乐殊致,比兴生焉。”这是张问陶最早论述诗歌创作的诗篇。尽管后来与诗友唱和时,也谈到过诗歌创作的有关问题,但他自觉而全面地论诗是在乾隆末期:1793年2月创作的论诗组诗《论文八首》,针对学问诗的汩没性灵,批驳道:“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是年寄诗袁枚,之后袁张诗书往来,谈诗论诗。1794年2月张问陶创作的《论诗十二绝句》,更多处标举“性情”,如“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24旗帜鲜明地提出“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25,“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26后来又写了大量探讨诗学理论的组诗、论诗单句,皆以“性情”论诗。他晚年所作的《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又进一步重申:“诗人原是有情人”。《题法时帆(式善)前辈诗龛向往图》诗还批评了“不斗性灵斗机巧”的不良诗风。张问陶所说的“性情”、“性灵”,都指人的自然情感,指人不加矫饰、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在论诗重“真性情”上,张问陶与袁枚和赵翼是“同调”27,不过张问陶所论既有情之真,又有情之善、情之美。他标举的“性情”有真性情,还有奇情、深情、故国情。今人苏仲翔先生《论诗绝句》云:“船山仲则两相当,瓶水烟霞抗雁行。郁怒情深同一往,少时吟味老难忘。”黄仲则诗歌的最大特点是用情极深,无论是缠绵悱恻还是抑郁愤慨之情,都写得回肠荡气,如泣如诉,令人欲歌欲泣。故洪亮吉评其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28。正是在专意用情上,船山仲则具有相似之处。但张诗不像黄诗以写个人身世之感为主,所以情绪也没有黄氏的感伤,张诗更多注目于广泛的人情,隐藏着一股雄健之气。但在情的深度与力度上,则是“船山仲则两相当”,连张问陶自己也说“我诗情深颇近人”。《船山诗草》中涉及到“性情”的诗句主要如下:
诗人骨死性情生,时发幽光夺明月。
(《拜讷旃先生墓》诗草补遗卷一)
留佛看今古,笼诗写性情。
(《潼川夏日游琴泉寺同遂宁李明府作》诗草卷二)
冷眼看空《游侠传》,热肠涌出性情诗。
(《赠徐寿徵》诗草卷十一)
难测天心姑任运,既来人世可无情?
(《怀人书屋遣兴》诗草卷五)
笔墨供游戏,山川写性情。
(《江安舟中遣怀》诗草卷八)
言情诗有味,排闷酒无灵。
(《寄怀亥白兄寿门弟》诗草卷十一)
莫厌风尘俗,临民最有情。
(《答杨米人明府(瑛旭)》诗草卷十三)
我诗情深颇近人,小巫何必皆通神。
(《寄答吕叔讷广文代简》诗草卷十七)
小摘鹍弦写性情。
(《题蕉园方伯小卷》诗草卷十九)
场屋青灯写性情。
(《明宋忠烈公硃卷册公裔孙湘属题》诗草卷十五)
驴背诗情古,天涯破锦囊。
(《十九日驴背作》诗草卷三)
诗情合在疲驴背,青笠红衫忆灞桥。
(《雪夜》诗草补遗卷一)
天海诗情驴背得,关山青色雨中来。
(《芦沟》诗草卷二)
世缘空处性情真。
(《赠沧湄》诗草卷五)
潦草投诗气不驯,疏狂容我性情真。
(《赠杨荔裳观察即送其之川北道任》诗草卷十)
抛散前身借此身,须眉全改性情真。
(《李仙像》诗草卷二十)
诗逢离别情难尽,事近猖狂意最真。
(《六士筵上赠歌者才宾》诗草卷六)
我醉猖狂神不怒,人能痛饮诗方真。
(《壬子除夕与亥白兄神女庙祭诗作》诗草卷八)
真极情难隐,神来句必仙。
(《有笔》诗草卷十三)
奇情真过我,大敌仅逢君。
(《读周倬云近诗题赠》诗草卷十六)
奇情敢道破天悭,为纪穷愁不忍删。
(《自题诗草》诗草补遗卷一)
乍动奇情忘笔砚,妙无成格碍心胸。
(《高西园指画山中雪意题画作于雍正乙卯》诗草卷十四)
故国情难尽,奇诗性所耽。
(《壬子正月二日出江桥门即目》诗草卷七)
袁枚、赵翼、张问陶都以“性情”论诗。袁枚最重性情之真,所谓“性情得其真”29,“情以真而愈笃”30。他认为“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31。赵翼也重真性情,并常以此作为评诗论诗的标准。赵翼于《瓯北诗话》中评历代诗人十大家,之所以选中本朝吴梅村,也在于吴氏的真性情,称他“感怆时事,俯仰身世,缠绵凄惋,情余于文,则较青丘意味深厚也”32。又赞吴梅村《过淮阴有感》“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曰:“此数语俯仰身世,悲痛最深,实足千载不朽”33,认为具有永久的魅力,也是着眼于吴诗“自惭自悔”之真性情。张问陶也同样认为优秀的诗歌都是表现真性情的,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这里的“人情”即自然真实的感情)。他还在《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中提出:“自磨碎墨写天真”。此“天真”即发诸生命的本真,近于李贽之“童真”。“写天真”,也就是说诗歌写真景、表真意、达真情,而这些都要用真语来实现。为此,张问陶非常重视“淡语”、“真实话”、“情话”、“醉语”。他说:
闲愁似梦寻无迹,醉语如诗妙有神。
(《闰四月十九日雨后灯下得长句二首》诗草卷七)
尘缘且向闲中领,奇语都从醉后真。
(《庚申岁暮书怀》诗草卷十五)
即此眼前真实语,也通诗境也通禅。
(《除夜五鼓将入朝独坐口号》诗草卷十)
摇笔争夸绝妙词,那知情话即真诗。
声才脱口千人解,语不聱牙万古知。
(《和少仙》其三诗草补遗卷五)
奇篇能磊落,淡语亦丰神。
(《题姚伯昂诗》诗草卷十六)
张问陶言“淡语亦丰神”,“醉语如诗妙有神”,而再“绝妙”的词语也难抵“情话”。所谓“情话”,发自肺腑,不艰涩,不聱牙,极自然平易,也极简洁易懂,为所有人接受和使用,所以历代相传不止。还有酒后醉语,因其最为真实地反映了说话者的内在情感而“妙有神”。然而,张问陶所谓“天真之语”,又不同于袁枚的信口信心,而是力求平淡中见精神,其《题姚伯昂诗》云:“淡语亦丰神”,所谓“淡语”即在寻常、质朴的语言中凝聚着诗人的心血、智慧与艰辛,应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的返璞归真。如“僧敲尤恐胜僧推”,34就是张问陶对贾岛精于语言锤炼的赞扬。“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野趣天然的诗句,只会让人以为是妙手偶得,哪里还能见出贾岛当年月夜“推敲”之苦?分明是用尽了惨淡经营之功,却给人以信手拈来、轻松出之的错觉。这也正是张问陶所赞赏的“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35。追求百炼功纯之自然,张问陶则对一切有悖于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如“潦草诗多句易忘”36,批评了随便堆砌词语的做法;“何苦尖文寻恶韵,且随盐絮作陈言”,无疑是对偷偷“趁韵”及苦寻“恶韵”的厌恶;而“诗逢好韵尤须铸”37,则又对基于创作需要而在诗中用韵的肯定。
张问陶以“天真”论诗受道家文艺观的影响。道家反对机巧、虚假、伪装、浮华,崇尚淳朴和天真。庄子文艺观最突出的特点则是“贵真”,38“贵真”的观念由庄子提出,其前提是“法天”,“法天”的思想即是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由“道法自然”出发,老子的文艺观可定论为自然文艺观。“法天贵真”的观念运用于对语言艺术的要求,主要是在言辞表达上要合乎自然,主张“善者不辩,辩者不善”39,主张“大辩若讷,大巧若拙”,这也可以看作是对雕琢语言的反对。张问陶追求诗歌语言的平淡自然,批评“雕文镂采太纷然”,强调“毋绮语”、“尚清歌”,与道家的法天贵真文艺思想是一脉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