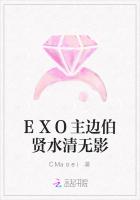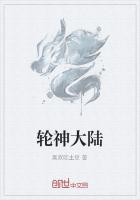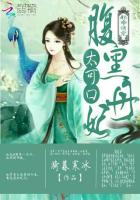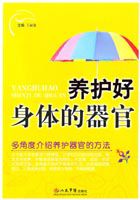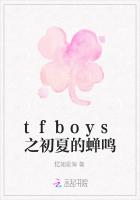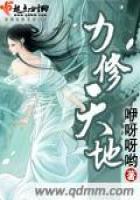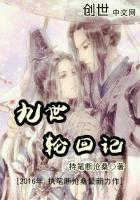若从性情的内涵和表达方式上分析,袁枚之性情,内涵非常丰富,举凡亲子之爱、友朋之谊、男女之思、羁旅之怀、身世之叹、离别之恨、山水之乐无不在其性情之中。与袁枚相比,张问陶更加丰富了情的内涵,他将情从爱情、友情、兄弟情扩大为山水情、师生情、主仆情、乡情、人民情、家国情,且无不一往情深。他强调性地说:“故国情难尽,奇诗性所耽。”“莫厌风尘俗,临民最有情”。在性情的表达方式与手段上,袁枚和张问陶又有不同。袁枚用摧毁一切的办法来撕毁假面具,从而直露性情,他对人性丑陋的破坏性、颠覆性强,但建设性不足;而张问陶则用人性的美和善使虚伪和丑陋相形见绌,无地自容。这与大多数人的审美趋向一致,所以张问陶更易被人们接受。钱钟书就指出了袁枚识见过人,但为取快一时而缺乏周密。40在诸多的情感中,袁枚尤为强调男女之情。他的“情之所先,莫如男女”41,表现了对名教纲常的强烈的叛离性,却又有些矫枉过正。表现男女之情本无可厚非,但他又最为看重和表现男女之情的“真”。所谓“真”,是先天个性之真,真的未必是美和善的。因为重性情之真,袁枚诗歌多有通脱不羁、寄情声色之处,诗的品格不高,故遭非议。张问陶也不讳言在诗歌中表现男女之情,其《春日忆内》诗云:“房帏何必讳钟情”,《斑竹塘车中》诗又以自来被鄙薄的香奁诗人的身份批评自以为是的理学家,宣称:“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揭示了诗歌的本质是抒写性情,拒做载道工具。但是张问陶的男女之情不同于理学家的“复性黜情”,又有别于袁枚的“离性背道”42。他是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这个中心之下,而不偏废儒家之所谓“性”,即要发乎情,止乎理,表现出比较中正淳美的士大夫“性情”。所以即便是儿女之情,在他的笔下也是那么至真、至纯、至美,乃至广为传誉。张问陶以性情论诗,渊源有自。清代遂宁张氏家族,有诗文流传至今者,多达50余人,是名副其实的“诗人世家”,人称“一家男女尽能诗”。而以性情论诗,是遂宁张氏家族的共性。高祖“文端论诗,以性情为主”,43祖父张勤望写诗也从性情出,无论喜悲之感,还是失落之情,皆溢于笔端。父亲张顾鉴与袁枚等人为少年诗友,同写性灵。而且,遂宁张氏家族世代为人磊落坦荡,这就使得他们笔下的真性情又兼有善和美的人格魅力。而这些对张问陶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又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虽然表现真性情是性灵诗人的共同主张,但像张问陶这样兼顾情之善和情之美,在性灵诗人中并不多见。另外,对于男女之情,张问陶显然比较现代与诗意,他有一首很有意思的诗,题为《题沈舫西琨太守观空观色图》:“人生竟无欲,块然其土木。有欲而无情,强行亦禽鹿。”这与他《美人篇》中提出的“美人亦人耳”的观点是一体两面。他的爱情诗没有明清时期一些个性解放者的偏激的言辞和极端纵欲放浪的形状,特别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和男女之间相慕平等的人性意识,所以拥有永久的生命力而历久不衰。
在论诗主性情上,袁、赵、张是一致的,但在对创作主体的论述上,三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尽管袁枚也把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力论诗44,但他更多地强调了创作主体性情气质的表现,多从主体的真情、个性、诗才等方面而论。赵翼则更多的是推崇诗人之才气和创造精神,所谓“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功夫上见”45。张问陶论创作主体,要求首先必须具备真情实感,所谓“诗人原是有情人”,“既来人世可无情”?“热肠涌出性情诗”。他也谈到诗才与创作的关系,如“才退诗皆偈”46,“才退方知搜句苦”47等。创造精神更是张问陶着力强调的。如“不成李杜不张王”、“我自用我法”等。他还要求诗人要具备深厚的学养,这皆与袁、赵二人相通,反映了其与袁、赵的暗合。但是,张问陶要求创作主体还要具备虚静和自由的心态,尤其要注意在现实生活中培育情感,这是袁、赵很少涉及的问题,是张问陶的创造与开拓。
主体心境的虚静和自由,即要求诗人之心要“空”,要“闲”,要摒弃杂念,摆脱一切桎梏,游出于尘俗烦嚣之外。为此,他有以下表述:
世缘空处性情真。
(《赠沧湄》诗草卷五)
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
(《论诗十二绝句》之十二)
云外心闲得句真。
(《二月二十九日出都述怀》诗草卷六)
势迫出奇谋,心空生妙悟。
(《甲寅上元时帆前辈招饮》诗草卷十一)
酒肠渐窄花应笑,诗境全空笔有神。
(《秋怀》诗草补遗卷四)
无儒无释况神仙,妙论凭空写自然。
(《偶理案上书帙各题一诗解闷》诗草卷十五)
凭空自写意中山。
(《作画自题》诗草补遗卷四)
江湖原自有闲人,更有闲人为写真。
(《题友人江乡小景》诗草卷十五)
诗到真空悟境多。
(《雨后与崔生旭论诗》诗草卷十六)
别有诗人闲肺腑,空灵不是转轮王。
(《论文八首》之八,诗草卷九)
诗歌创作的整个环节,从创作的发生、审美体验,到构思想象以及技巧法度的运用等等,都与虚静心态有关联。洪亮吉《北江诗话》云:“静者心多妙。体物之工,亦惟静者能之。”徐曾《而庵诗话》亦云:“做诗第一要心细气静”等等。袁枚也说过在闲、静的心境下,才能写出性灵。48张问陶非常注重“闲”、“空”,他所讲的“空”、“闲”与老庄的“虚静”说是同一种精神状态。49老庄的“虚静”说作为一种认识论,有唯心的一面,但作为创作构思过程的一种精神状态,却是必要的和符合实际的。它要求创作主体构思时必须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和影响创作的杂念,从而展开艺术想象,认识和把握描写对象,使文艺创作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只有心闲、心空,才能进入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等境界。50创作主体具有一个虚静无碍的闲适心胸,而后方可进入最佳的创作状态,在自在天然的状态下,在漫不经意之中自如挥洒,纯任性灵自然流出。也就是说创作主体是“闲人”,51摆脱了一切现实桎梏,获得了一种“空灵”的心境,方能达到性灵的自然流露,并真切地捕捉到万物之天机神韵(客体之性灵),达到主客体性灵的交融契合,从而产生性灵之作。
诗歌创作要求创作主体除了情感、性灵、天赋以外,也需要具有深厚的学养,即先天的才性与后天的学力不可偏废。张问陶也强调作诗要靠天分,他在一首《自题》小诗里谈到了才与诗的关系:“才小诗多复,身闲笔转忙。但留真意境,何用好文章。”认为诗人才小,创作难有特色。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才退诗皆偈,心空梦亦真。”52“才退方知搜句苦”53他又重视学力和性灵的培养。他曾书门生崔旭诗卷云:“诗境已稳成极矣,此后惟须练识,识见一高,则笔墨羽化,方是真通人。”54意在说明性情、性灵也有待于后天的培养、提高,先天的才性须以后天的学养来不断润泽,才会永葆其创造的活力。广博的学识,精湛的艺术修养正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必备条件。张问陶反对翁方纲雕章琢句、堆砌典故的“以学为诗”,又吸收了翁氏“肌理说”重学问的一面,认为读书有益于诗歌创作,云:“丈夫破万卷,寝馈千古事。”55但是不能死读书,要化学为才。他的《使事》一诗云:“书皆随笔化,心直与天谋”,“莫须矜獭祭,集腋要成裘”,56最能说明这一观点。洪亮吉论诗重学问,他评李白诗“天才卓越”,“领异标新”,“不肯作常语”实则是“非读破万卷者,不能为也”。57洪氏还曾劝张问陶多读书,张则劝洪少读书。58张问陶劝洪亮吉少读书,是因为洪是经学家,而“凡攻经学者,诗多晦滞”59,他担心洪亮吉的学识如翁方纲般制约了诗歌中性情的自由发挥。
从根本上说,诗之情思及意象来自创作主体“自我”的人生体验,源自客观现实生活。诗歌离开客观现实生活,离开主体“自我”的生活阅历,必然难以保证真实性。因此创作主体不能游移于现实之外,不能在古书中讨生活,即“未知当日事,枉读古人书”60。张问陶自觉而主动地培育“性灵”,培养性灵务求广深,即“烟霞养性灵”、61“宽闲养性灵”、62“醇醪养性灵”63“金石图书养性情”64等等。而临笔写诗,却自写性灵,绝去依傍,独出新意,不事模仿。张问陶的政治诗,是他诗歌中最具有社会现实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这类诗篇里,敢于面对社会现实,触及时事。特别是他敢于正面地揭露清朝的腐朽阴暗,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白莲教农民起义战争的情景。如他的《戊午二月九日出栈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的诗句“杀人敢恕民非盗,报国真愁将不儒。”“大帅连兵甘纵贼,生灵涂炭已三年。”“大贾随营缘我富,连村无寇是谁焚。”揭露了清军所到之处,尽情杀掠,善良无辜的人民遭受清军杀戮,大量的民房被清军焚毁,清军反借此以报军功,造成了长期的生灵涂炭。而军中将帅除大量劫掠民财外,更大肆借此从事经商盘剥。所以当清军镇压白莲教农民起义军之后,有些将帅竟成了屋榭栉毗、田连阡陌的大富。而千村万落的百姓则是:“荒寒驿路匆匆过,焦土连云万骨枯。”“连城闭后万山荒,忍弃郊原作战场。”“三川人满欲烹珠,曾问今年米价无。”“谁看鸿鹄犹扶耒,人佩刀鞬早卖牛。”经过清军的大肆劫掠、杀掳、焚烧、敲诈之后,米价昂贵,人民饥寒死亡,流离失所,广大农村呈现出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象。张问陶对此社会现实,悲愤于怀,不畏文罔的迫害,竟大胆地呼吐出自己的心声:“天如有意屠边徼,我忍无情哭故乡。”“风诗已废哀重写,不是伤心古战场。”这些忧伤的诗篇,饱含着诗人伤时忧民之情,是发自性灵的呐喊,似《离骚》的怨怼,有《哀郢》的凄婉。
张问陶如此强调诗歌的“情”,还因为“言情诗有味。”65他论诗多处谈到了“味”。如:“懒把深杯懒著书,自怜诗味太萧疏。”66“青林红树淡无尘,诗思无多味已真。”67“臭味能从淡处真”。68他论及“味”、“诗味”,又将“诗味”具体区分为“萧疏”、“真”、“淡”,而且还把“味真”与“味淡”并举,说味“淡”则“真”。例如红树绿林,不染纤尘,其味最真。张问陶的“味”与钟嵘的“滋味”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他的“味”更真实、具体、丰富。值得注意的是,张问陶的“言情诗有味”合并了陆机的“缘情”说和钟嵘的“滋味”说,把“味”与“真情”同时并举。张问陶认为诗歌要有“味”,就要“言情”。这是他对钟嵘“滋味”说的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借钟氏的“滋味”说丰富了自己写真情的“性灵”说的内涵。张问陶的性灵诗论是创作实践的结晶,他不仅以“味”论诗,也创作了大量的有“味”之诗。遂宁灵泉寺僧道嵘的评价颇能说明问题。道嵘在《船山诗草序》中化用钟嵘《诗品》的写法,云:“张公,名家子,有殊才。仗气爱奇,自致远大,人实贫羸而文采高丽。推其文体,不避危仄,皆由直寻。善自发诗端,感荡心灵,动无虚散,因物喻志,怀寄不浅,甚有悲凉之句,又巧构形似之言,无雕虫之功,而韵入歌唱,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至乎吟咏情性,羌无故实。言在耳目之内,寓目辄书,使人忘其鄙近。”
张问陶强调诗写性情,又不偏废灵感的作用,他将灵感与情并举,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此“灵光”与陆机所说的“应感”,沈约的“天机”,汤显祖的“自然灵气”等相似,近于今天所说的“灵感”。灵感是创造性思维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到来时,作家的精神高度亢奋,思维活动异常活跃,天机启动,作家无意识、潜意识中深层的积淀被搅动奔突而出,沉潜在作家意识底层的个性、气质、秉赋等就能充分显现出来。就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诗人得到灵感,就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甚至会失去理智,陷于迷狂。69
灵感是形成作家创作独创性的重要条件,写作中缺乏这种思维,就难以有新意,所以追求独抒自我的性灵派诗人对灵感非常感兴趣。性灵派主将袁枚十分重视才华与灵机,他说:“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70。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之四、之五专论灵感问题,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题屠琴隖论诗图》、《秋夜》等也对灵感进行了讨论。灵感是我国古代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陆机的《文赋》论述了灵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灵感的心理特征,指出艺术创作与“应感之会,通塞之纪”的灵感有密切关系。认为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具有突然产生又转瞬即去的特点。他把“应感”到来之时的思如风发,言若流泉,摇笔挥洒,骏利无状的情态写得非常精妙。但是陆机不能说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得感慨地说:“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71张问陶则解释了“灵光”到来时创作者的思维状态:“一片神光动魂魄”,“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魂魄动”生动地描绘了灵感出现后作家精神状态专注敏捷、亢奋紧张,达到入迷而忘我的那种冲动境地。霎时间灵机所触,情感奔放,诗思泉涌,无法遏止。“笔有灵光诗骤得”72,则进一步指出:借助于“灵光”,创作主体的性灵得以显现,诗心、诗情、诗思都无所矫饰,真性情随之自然倾泻,最能体现诗人灵机的诗句也自然而出,真率而充溢灵趣的性情文章便产生了。张问陶从性灵说出发,对灵感与创作的关系、灵感与饱含性情的文章的关系作了论述,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说明了灵感是性情之作产生的重要条件,灵感与“情文”具有不可分离性,借助于灵感,才能写出富有性情的文章。这是对陆机、沈约等“灵感”说的丰富和发展。而“灵来亦偶然,灵去复何惜”73,“聚如风雨散如烟”,74“神龙鳞爪破空来”75等诗句,对灵感的突发性、偶然性、瞬息性和模糊性特征的描述,比陆机等人也要全面、具体的多。
诗中有“我”,力求创新是张问陶诗歌理论的又一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