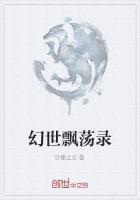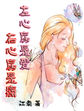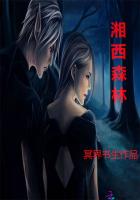诗歌的本质是诗人情感精神的自我表现,诗中必须有诗人的感受和体验,有诗人自我的个性,不可步人后尘,要“诗中有我”。“诗中有我”,写出自己的感情、个性,就能“生面别开”,诗歌便有特色,就能自成一家。“诗中有我”,他人读之,就能“见我性情,知我心态”76。吴乔《围炉诗话》强调性地提出了“诗中须有人”。朱庭珍对“诗中有我”分析得更加透彻。77提倡“诗中有我”,已成时代风气,当时性灵诗人更是加以强调。袁枚推重“作诗不可以无我”78,在《续诗品》中提出“著我”,追求表达独特个性。张问陶要求诗歌写出自我独特的感受,表现个性。其《论文八首》明确表示:“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而“此中我我却相关”、“写出此身真阅历”,更是特别地强调要表现自己的真性情,写出真实的生活感受。写出了自己的真阅历、真感受,诗便是纯然个人化的,是任何人也无法重复的。他在《冬夜饮酒偶然作》里,“我将用我法,独立绝推戴”、“悠悠三十年,自开一草昧”、“我面非子面,斯言殊可拜”等句,明确宣示:自己的创作,只依其性灵,言所欲言,放笔而写,无意依傍任何人,表明自己是不师承任何门户而生面独开。“自吐胸中所欲言,那从得失争千古”,“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79意谓应该自出机杼,独抒诗人“自我”之性灵。
在袁枚所处的清代中叶,文化传统对个体差异的消解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人们在对古籍字句的不厌其烦的考注中讨生活,在不越雷池半步的模仿中匍匐而行。袁枚承继了晚明思潮的个性观念,极力标举和张扬个性。其《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大声疾呼:“我亦自立者,爱独不爱同”!鲜明地表达了诗人自觉的个性意识。清代诗坛学唐、学宋之争颇为激烈,袁枚认为诗歌之间的差异,都是因诗人各自性情而成,反对将诗歌分唐界宋80,从而对模拟、复古、形式主义等不正诗风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张问陶同袁枚一样弘扬个性,崇尚创作的独创性,他说“愧我性灵终是我”,提出“诗中无我不如删”。而规模唐宋正是“诗中无我”的典型。为此,他以性灵为武器,对规唐模宋的风气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其《论诗十二绝句》之十说:“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题屠琴隖论诗图》又讥刺:“规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残花放几枝。郑婢萧奴门户好,出人头地恐无时。”矛头直接指向沈德潜、厉鹗等规唐模宋者。张问陶认为诗歌是诗人自我性情的表现,所以,效仿、步武古人是没有益处的。即使酷肖唐宋大家,仍不免寄人篱下,无以自立门户,出人头地。沈德潜的“诗教”论过分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诗中无“我”又有悖于“诗本性情”之本质,不利于文学的全面发展。袁枚认为“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81,他反对沈德潜将“温柔敦厚”的“诗教”绝对化,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82袁枚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抨击沈德潜的“诗教”论,为倡导“性灵说”廓清了道路。袁枚之后,张问陶也对沈德潜的“诗教”论提出批评。其《论诗十二绝句》之六云:“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显然是针对沈德潜诗教论的桎梏性灵而发。
乾隆以降,汉学日盛,影响到诗坛,形成了一股炫耀学问、以学为诗的逆流。袁枚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有《论诗绝句》讽刺翁方纲之流,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锺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翁方纲的掉书袋,不见主体的气质、情性、个性,失去了自我,与张问陶诗中有我的主张相悖,故予以坚决抵制。崔旭在《念堂诗话》中云:“船山师于近日名家中最喜宋荔裳(宋琬),最不喜翁覃溪(翁方纲)”。张问陶的《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等诗中,也确有许多诗句矛头直接指向翁方纲之类以学为诗者。如:
笺注争奇哪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
(《论文八首》)之五)83
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
(《论文八首》)之八)84
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
(《论诗十二绝句》之八)85
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
(《论诗十二绝句》之二)
考订实小技,何足立师道。
(《寄贵州学使洪稚存同年》诗草卷八)
胡为乎能平水土驱龙蛇,不能拓彼斤斤考订之心胸?
(《涂山》诗草卷八)
更有意味的是诗友王葑亭送其黄鲴鱼,船山赋诗致谢,以“黄鲴”为题,讽刺考订者,可谓一针见血。诗云:
鱼胃鱼肠名偶同,黄鲴黄骨语朦胧。
若供考订先生馔,又要争谈《正字通》。
(《谢葑亭给谏送黄鲴鱼》诗草补遗卷四)
诗本性情出,肌理派却讲究学问出处。船山此诗以幽默诙谐的笔触,讽刺了考订者不放过任何炫耀学问的机会,渗透于字里行间的是讽刺与批判的锋芒。肌理派以学为诗,从根本上有违诗本性情之特质。袁枚嘲讽其“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86,认为以考据为诗背离了诗歌的本质,毫无价值。他是从才性论的角度出发,论证了诗歌与考据学两者不能相兼。赵翼从其“诗写性情”的诗歌本体论出发,认为诗中不是不可以用典,而是说用典要有利于“性情”的抒发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显然,作为史学家和性灵派的主要作家的赵翼,对此有着较为正确的理解。87张问陶坚决反对以考据入诗、以学问为诗,反对饾饤古书。他对以学为诗的批判,与袁枚的立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张问陶是从性情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要表现诗人自我,表现真性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并指出了诗人同学者、诗歌同学术的区别所在:“笺注争奇那得奇,古人只是性情诗”,批判了考据为诗,更体现了鲜明的性灵思想。张问陶的创作实践也摆脱了考据文人们专从故纸堆中寻取创作材料的影响,以客观社会的真实现实存在作基础,通过自己的思想认识及深刻的生活感受,吐出内心深处的声音。在张问陶的各类诗篇里,无论是叙事言理,或托物寓志,或抒情写景,无不富有诗人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及浓郁的生活气息,都是感荡性灵之作。
“诗中有我”是诗歌创新的重要途径,论诗主性灵者都坚决主张创新。袁枚高举创新大旗88,而创新更是赵翼性灵说的核心。赵翼说诗人要“自成一家”89,独具风格,他的《论诗》诗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书怀》诗又云:“人心亦如面,意匠戛独造。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这种“意匠独造”、“自成一家”的创新意识是赵翼独抒性灵思想的核心。关于诗人的创新精神,张问陶比之袁、赵毫不逊色。因为张问陶的诗歌创作与袁枚有着共通之处,时人有谓其诗学随园者。张问陶特作《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诗二首,表明其独拔一队的创新精神。诗云:
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
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
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数行。
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90。
诗中的用语与袁枚《遣兴》诗相近,而“愧我性灵终是我”,又具体说明了自己不仅不学古人,对所心仪的袁枚也绝不依傍。其独立不倚的精神比袁枚的“独来独往”有过之而无不及91。客观而论,随园执诗坛牛耳几十年,张问陶不受随园影响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谁能有意学随园”中“有意”二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此不“有意”学随园,正体现出张问陶深悟了性灵说的精髓。故清人顾翰云:“脱尽古人窠臼,自成一家”92。而张问陶从诗歌理论到创作实践所体现出的鲜明的个性,其精神实质与袁枚等人也正相一致。
论诗主创新,势必要反泥古。为此,张问陶用了大量的诗句,表明自己对古人的态度。如:
文心要自争千古,何止随园一瓣香。
(《与王香圃饮酒作》其一,诗草补遗卷四)
谈心只觉易狂士,得句常疑复古人。
(《早秋漫兴》诗草卷四)
不抄古人书,我自用我法。
(《壬子除夕与亥白兄神女庙祭诗》诗草卷八)
未知当日事,枉读古人书。
(《丙辰冬日饮酒作》诗草卷十三)
独学常疑古,交游未喜新。
(《依竹堂初冬即事》诗草卷十七)
非时毕竟关何事,作典还应数自今。
(《闰花朝穀人前辈约同王香圃(麟生)倪米楼(稻孙)吴香竺(瑛)游陶然亭遇雪不果同集有正味斋分韵得今字》诗草补遗卷四)
诗但成今体,名宜让古人。
(《小句》诗草卷十九)
今人爱古人,莫被古人误。
(《题味辛古藤书屋图》诗草卷十一)
古虽可爱非今日,天不能寒有地炉。
(《怀人书屋遣兴》诗草卷五)
昨日之日今日又斩新,好古不泥真通人。
(《仓史造字图为渊如前辈题》诗草卷十一)
兴到何必仿古人,事过须教后人仿。
(《小除日与稚存松筠庵祭诗属子卿作图各题长歌纪之》诗草卷五)
甘心豢养非天马,蹑月穿云任所之。
(《和少仙》之三,诗草补遗卷五)
牙后慧难追雅乐。
(《庚申六月遣怀杂诗》诗草卷十五)
疑古是性灵诗人共同的特点,袁枚和赵翼都疑古。赵翼是史学家,其《后园居诗》公然揭露历代官修正史之作伪,发出了“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的惊世骇俗之论。张问陶也敢于疑古、善于疑古,他“独学常疑古”,“得句常疑复古人”,但是却并非盲目地追求否定古人。在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上,张问陶有着较为科学的认识。他不排斥向古人学习,但一定不能泥古,要古为今用,“好古不泥真通人”。张问陶自觉地把创新当作诗歌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说“昨日之日今日又斩新”,揭示了日趋于新是一种自然趋势。这种发展进化的观点与赵翼《论诗》中“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93“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94所揭示的“渐变性”是一种“天运”和“自然之势”的精神相通。要创新就要敢于独辟蹊径,大胆探索,为人所不敢为,勇于突破前人藩篱。谢榛、陆时雍和清代张晋本都指出了诗人应具有自开新路、大胆探索的艺术勇气95。叶燮坚持个性化,主张诗人必须有创新精神,敢于与陈陈相因、平庸无奇绝裂,疾呼:“昔人可创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96。张问陶则明确提出:“兴到何必仿古人,事过须教后人仿”,大有目空千古、敢为人先的胆量。乾嘉诗坛好古、信古、佞古而媚古之风日盛,张问陶认为“古虽可爱非今日”,警醒“今人爱古人”,“莫被古人误”。他反对脱离时代,一味地向后看,喊出了“万古无如眼前好,只有当前属我生”。这些诗句的时代针对性很强,是对当时诗坛上考据学派和规模唐宋者泯灭性灵而发。受考据学影响,乾嘉诗坛以古体诗为重,视近体诗为左道。张问陶在《小句》一诗中表示,自己“诗但吟今体,名宜让古人”。而他的诗歌创作确实“以近体为工”,不独守尺寸,见从己出,“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97
张问陶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的贡献
张问陶的诗歌无论是政治诗、怀古诗、写景诗、还是纪游诗、爱情诗,均摆脱了诗教论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思想,是“吟咏性情”的真实之作。但张问陶在抛别载道桎梏的同时,并没有连同社会责任一并丢掉,而是公开标举风雅精神,提倡“一代真诗笔,空言定扫除”,“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莫厌风尘俗,临民最有情”。公开标举风雅精神,这是袁枚、赵翼性灵说所少有的,是张问陶对性灵说的突出贡献。
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诗笔要触及众生疾苦,切中时病,不为空言,真实地反映时代风貌,故张问陶有诗云:“一代真诗笔,空言定扫除”。真正的诗人还应该是属于社会的,要有大众意识,深入生活,贴近下层人民,关注现实和民生疾苦,所以张问陶又提出:“莫厌风尘俗,临民最有情”。诗歌需要抒情,但诗人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为此,张问陶提出:“关心在时务,下笔惟天真”,把诗写“天真”与关注“时务”并举,也就是把“情”和“志”结合起来。张问陶不乏诗人纯真的性情,又有诗人面对现实的良知。他的诗将个人的性情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既有诗情,又有道性,而言志重于载道。如富有现实性及人民性的诗篇《采桑曲》,与杜甫的《石壕吏》具有同样的思想感情,读之令人掩卷而泣下!
《采桑曲》98
新蚕蠕蠕一寸长,千头簇簇穿翳桑。
天地生桑作蚕食,一日不食蚕已僵。
春来无雨桑林秃,少妇提筐向蚕哭.
温风如火逼人来,拥鼻空吟《采桑》曲.
吁磋乎!蚕不饥、人不寒。
蚕饥忽如此,叹君何处夸罗纨!
罗纨织千丝,丝丝耀金紫。
卖作贵人衣,衣成蚕尽死。
蚕死不复生,衣成不必称。
得值救饥寒,民乎犹有命。
陌上桑枯蚕亦病,谁能空手谈蚕政!
黄尘扑面风卷沙,倚墙矮树啼昏鸦。
忽忆朱门正歌舞,吴绫一曲争繁华。
吁嗟乎!吴绫一曲真豪举。
不知苇箔春蚕细如缕!
岂独春蚕细如缕!
君不见道旁饿杀采桑女。
《采桑曲》一诗,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达官贵人们,过着“朱门正歌舞”及“吴绫一曲争繁华”的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温风如火逼人来”,“黄尘扑面风卷沙”,“道旁饿杀采桑女”等画面,描写了采桑女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悲惨的命运。养蚕的艰辛经由诗人细腻的笔触和感伤的笔调,历历在目地再现出来。从采桑女带出整个苦难的时代,采桑女的遭遇正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张问陶诗歌中表现出的正是英国诗人T.S.Eliot所说的诗人的历史意识。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精神,其实质是“风雅”精神的回归。此是对儒家传统诗说的继承,与沈德潜的“格调”论有相通之处。只不过沈德潜坚持并力图恢复儒家诗学传统时,过分地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而流入刻板的“诗教”论,不免使诗歌沦为政治工具,则为张问陶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