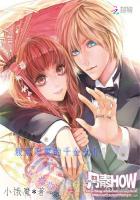袁枚、赵翼、张问陶因时代不同、各自生活遭遇与处境的不同,诗歌创作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关涉社会问题的诗篇在袁枚、赵翼笔下也出现过,但均不如张问陶写得深刻、沉郁。袁枚有不少反映民生疾苦,表现仁爱之心的诗歌,但由于生活在乾隆盛世,袁枚诗歌中没有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映,只是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讽刺贪官污吏的诗歌,表现出了风雅之怀99。而且最能表现袁枚个性和识见的也正是这些讽喻之作。赵翼也有《秤谷叹》、《书所见》、《忧旱》等关注现实的诗歌,不过赵翼更擅长于借古讽今,咏史感时。他的咏史诗对现实尖锐地讽刺,颇具思想力量。但从批判性、战斗性上看,讽喻、讽刺毕竟不如直接揭露。张问陶的一些诗歌,直接地表现出“关心在时务”的情感,以及抨击时弊的胆识,其对现实的直接揭露,为袁、赵二人所不能及。张问陶的这类诗歌是性灵诗中的上乘之作,历来论者多注目于此。与船山同一时期的钱泳尝赞云:“张船山太守集中有《宝鸡题壁诗》,长歌当哭,俱不可不读也”100。张维屏评船山诗,其《听松庐诗话》独具慧眼地指出:“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入,亦能清脱。”张问陶的深刻、沉郁决不是偶然的。在袁、赵、张之间,以张问陶的生活遭遇崎岖最多,起伏最大。他生活在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年代,又数次穷愁羁旅地奔波于江汉、蜀京路上,对乾嘉盛世面貌掩盖下的衰世的腐朽以及天灾与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或目睹、或亲历,这些扩大了他诗歌创作的视野,丰富了诗歌创作的源泉。他将这些广阔的社会现实,通过自己的深刻感受,摄入诗作里,写出了《拾杨稊》、《采桑曲》、《六月咏蝇》、《画鹰自题》、《巡视南城履任口占》、《安国寺饭厂》、《丁巳九月褒斜道中即事》、《壬申三月四日去郡口占》、《宝鸡题壁十八首》、《御夫赵才》、《佃户梁清》、《舆夫徐长子》、《卖饼李叟》等大量具有人民性、现实性的优秀诗篇。他的诗歌在广阔的社会性及真实的现实性方面,胜于瓯北诗,更为随园诗所不及。袁枚一生处于乾隆盛世,过早地过着舒适的随园生活,其诗艺术上虽有通脱明朗的优点,但又不免浮泛,所以他的创作实绩远在其理论建树之下,也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袁枚诗歌超出了封建文化重集体轻个人的樊篱,提倡不论男女老幼,人人都可展露自我之才情。这种人人都可以表现自我、表现个性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初步的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在他那里,儒家兼济天下的英雄情怀已趋微弱,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生存的关注,在表现个体生命的世界中,对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追寻。张问陶生活的时间比袁枚等人稍后一些,亲历或目睹了盛世下的千疮百孔,在诗歌揭露现实、追求民主的主题表现上,较袁枚直接和强烈。乾隆四十九年(1784),诗人21岁时就在《芦沟》诗中写道:“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无成局”是说社会政治与文化状态的萎靡,“是废才”则是自哀和自责。而向往自由的精神,常常借着飞动的意象呈现出来。像《出栈》诗所写“送险亭边一回首,万峰飞舞下陈仓”,《醉后口占》写“醉后诗魂欲上天”,都是渴望挣脱现实的羁绊,使人生获得自由,个性获得解放的真实写照。张问陶诗歌中所表现的精神的跃动不安,在袁枚诗中还较少看到,而到了龚自珍诗中,则又有更兀傲有力的表现。龚自珍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张问陶的《芦沟》诗与龚自珍写于道光19年(1839)出都途中《己亥杂诗》之“九州生气恃风雷”一首对读,虽有半个世纪之隔,仍可以看出两位思想敏锐的诗人的情愫以及彼此时代人文精神的一脉贯串。“从袁枚到黄景仁、张问陶,再到龚自珍,对自我的重视和精神扩张的欲望,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连贯发展的过程。”101而张问陶后期的诗歌,超越了只抒一己悲欢,紧扣时代的脉搏,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体才情的表现,而是集体个性解放的要求,这在乾嘉专制仍然酷烈的时代,恰恰具有进步意义。
诗人不应总注目于小我的欢喜悲愁,必须开阔视野,深度参与时代,和现实社会的脉动相结合,不断地以诗笔来记录历史,留下令后世动容的经典文本。由于张问陶能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个人生活的狭窄圈子,更多地注目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因而写出的性灵诗,具有更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内容,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价值。他诗歌中的强烈的现实意识、时代精神、乡土情怀等,得到了社会性的认同。张问陶的诗歌能在清诗史上独树一帜乃至流传至今,与其执着地追求诗歌与现实的结合有着直接关系。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的流弊到了张问陶的时代已日益显露出来,钱泳《履园丛话》针对袁枚性灵说与沈德潜格调说“判若水火”之论争,评云:“格律太严固不可,性灵太露亦是病”,102显然是不满于性灵说感情抒发浅率之弊。而张问陶在“性灵”中充盈着饱满的现实意识,他的诗具有一种劲健的风骨、壮美的气势,无疑是对袁枚“性灵”说浅率的补救,客观上为性灵说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钱仲联先生认为张问陶诗较之袁枚诗“有刚劲之骨而少滑易之习”103。朱文治为性灵派诗人,对船山诗推崇备至。其《书船山纪年诗后》云:“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亦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充分肯定了船山诗之超越随园诗,并指出二者的差异,可谓真能把握其实质,深刻而恰得其宜。张问陶主张诗歌直抒性情,但并非徒事性灵,他的诗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层人民的苦难以及社会政治风貌,既具有突出的个人特色,又具有浓郁的时代感。这不仅在性灵诗人中罕见,即使在乾嘉诗坛也少有。故康发祥《伯山诗话》云:“自乾隆朝至嘉庆年间诗人如张船山者,诚不多观”。
张问陶的另一贡献则是扩大了性灵说的地域影响,壮大了性灵派的作家队伍。王英志先生的《性灵派研究》一书指出,性灵派“从空间地域角度讲比较狭小,此派绝大多数为江南诗人,或客居于江南的诗人”。104张问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来往于湖北、京师和巴蜀之间,只是在晚年辞官后才客居苏州。船山笃于交友,所到之处,逢山赠诗,逢人交友。他在羁旅之路,结识和影响了许多诗人同写性灵。如与船山有莫逆之交的四川籍诗人彭田桥,结识于湖北,直到船山入京师后仍友情不减当年。船山居蜀期间,更带动了一大批四川诗人共写性灵。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中性灵诗人占据很大一部分,其中许多人与张问陶交往密切,酬唱频仍,诗友中甚至还有遂宁灵泉寺住持僧道嵘等佛门子弟。活跃在乾嘉诗坛的四川诗人大都在船山影响下,崇尚性灵,加之有数十位张氏家族诗人先后参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了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居京师期间,船山与活跃在乾嘉诗坛的著名诗人一百多位都有交往,他结交了洪亮吉、张莳塘、石韫玉、吴锡麒、赵怀玉等慷慨悲歌之士,又与李调元的堂弟鼎元、骥元志趣相投。朱庭珍在《筱园诗话》里,攻击张问陶是“恶俗叫嚣之魔”,说他“诱人入魔道”。朱庭珍对洪亮吉从研究经学转而写诗,并与张问陶结为酒朋诗侣深为不满,认为张拖人下水,实为罪魁。云:“洪稚存以经学考据专长”,“既入词馆,与张船山唱和甚密,颓然降格相从,放手为之,遂染叫嚣粗率恶习”105。“夫以稚存学问才力,俯视一世,一为张船山所累,遂染其习气,纵笔自恣,诗格扫地”。106同样杨芳灿兄弟(杨蓉裳、杨荔裳)与张问陶交往,也被斥为“华多实少,有腴词未剪,终累神骨之病”,导致“诗则品格不高”。朱氏所言从反面证明张问陶影响了一大批京师诗人共写性灵。
张问陶不仅以其性灵说理论和创作实践影响了一大批四川诗人和京师诗人同写性灵,还扩大了性灵说在海外的影响。韩国著名的文学家、外交家、诗人朴齐家,乾隆五十五年第二次入京师充使臣。时张问陶任翰林院检讨,朴齐家是韩国文院检讨,因工作上的关系,结识了张问陶并成为至交。后经张问陶引荐,他与袁枚、罗两峰、法式善等也成为诗友。朴齐家曾谈到过诗歌创作问题,云:“博及群书,发之以性情之真者哉!由是观之,文章之道,在于开其心志,广其耳目,不系于所学之时代也。”107这些见解明显受到张问陶等人诗歌理论的启发。嘉庆初年,韩国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尹仁泰,派往中国做使臣翻译,也与张问陶成为挚友。他曾亲笔为船山书屋题写匾额“怀人书屋”,以表达与张问陶多年交往的感遇之恩。二人归国时携张问陶亲书的诗草一卷,从此,郁陵岛上有了中国的性灵诗作108。
船山之才,引得四海骚人万般仰慕。有的士人写诗作文,愿化为妇人,甚至作妻妾侍奉他。清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中载:
船山先生诗才超妙,性格风流,四海骚人,靡不倾仰。秀水金筠泉(孝继),忽告其所亲,愿化作绝代丽姝,为船山执箕帚。又无锡马云隄(灿)赠诗云:‘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间才子妇,不辞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倾倒之心,爱才而兼钟情,可谓至矣。先生戏成二律以谢云:‘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痴情欲放颠。为告山妻须料理,典衣早蓄买花钱。’‘名流争现女郎身,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事苦窥臣。’亦词坛一则雅谑也。
有清一代,男风鼎盛。从这则文坛雅谑中,既可窥见乾隆盛世时男风仍盛,更见船山诗艺术魅力之大。年轻的文人学士对张问陶更仰慕之至。袁洁《蠡庄诗话》云:“余童年即仰四川张船山先生之才,见其字,读其诗,心窃慕之。辛未年,余由江左服阕来东,时先生仍莱州守,以为可常相见。比至而先生已引疾去,为之怅怅。后先生浪迹吴门,遂殁于苏。余哭以诗云:‘人间留大笔,海内失仙才’”。张问陶的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当时的诗坛,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丕烈嘉庆丁丑(1817年)秋识语云:“张船山遗稿二十卷,于嘉庆乙亥梓于吴中,一时为之纸贵”109,顾翰《船山诗草补遗·序》也称:“所作诗业已刊行,悬书林不胫而走”。张问陶曾经整整影响了一个时期的都下诗风。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诸老始喜言宋诗。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海上花列传》中,有不少人照船山诗意作诗。张恨水在《春明外史》里,让主人公杨杏园步和了张船山的八首《梅花》诗,引得人们纷纷寻找《船山诗草》来读。张问陶对当时的诗风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张问陶与洪亮吉以“气”论诗
比较及张问陶论洪亮吉110
袁枚的性灵说常以“才”论诗,极少涉及“气”。张问陶的性灵说强调诗人本色个性之时,则还标举“气”,进一步以“气”论诗。其《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云:“有情那可无真气”?将真情与真气并举,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观点。
偶凭真气作真诗,无端落纸成诗文。
(《寄答吕叔讷广文代简》诗草卷十七)
前身自拟老头陀,真气填胸信口呵。
(《题张莳塘诗卷时将归吴县即以志别》诗草卷四)
游戏韩门气不酸,不为岛瘦不郊寒。
(《玉川子像为陈闻之题》诗草卷十三)
年来我渐悔雕虫,才劳精神气转雄。
(《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诗草卷十三)
妙句怪多湖海气,相看原未拟儒生。
(《题彭田桥诗后》诗草卷二)
醉中奇气飞三雅。
(《累日陪邵二云前辈作诗奉赠》诗草补遗卷四)
有情那可无真气?
(《成都夏日与田桥饮酒杂诗》诗草卷七)
如我有奇气,与君俱少年。
(《题何阑士方雪斋诗集》诗草卷十)
笔有灵光诗骤得,胸无奇气酒空浇。
(《秋夜》诗草卷十一)
潦草投诗气不驯。
(《赠杨荔裳观察即送其之川北道任》诗草卷十)
胸有奇愁气自雄。
(《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诗草卷六)
无诗无酒气纵横。
(《怀稚存》诗草卷十五)
语不分明气不真,眼中多少伪诗人。
(《题朱少仙同年诗题后》诗草卷十一)
气盖岩疆心磊落,诗包全史论纵横。
(《题邲阳明府郑青墅同年诗集》诗草卷十五)
张问陶诗歌中呈现出刚劲雄健之气,其《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云:“诗多奇气为逢君。”说自己诗多“奇”气受洪亮吉影响。洪亮吉也认为船山诗与自己有更多的共同点:“我诗与君诗,识者不能别”111。张问陶和洪亮吉都是具奇气、有奇能、具奇才、怀奇情者,且同具狂放的个性。这使得他们都追求诗歌的气度与气势,或慷慨悲歌,或清刚超拔,或才气豪迈,或笔力雄健,诗中都表现出雄直刚健之气。王芑孙《题洪稚存张船山祭诗图》称:“两君诗力雄且厚”。具体而言,张问陶的诗豪气凌云,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洪亮吉之诗奇崛嵯峨,如激流回荡,气势非凡。所以,康发祥和张维屏都评北江诗“有真气,亦有奇气。”112吴嵩梁则说稚存诗有“珠光剑气”113。张问陶除了爱情诗写得比较柔婉而缠绵,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记游、咏怀诗则写得清刚而拔超,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阳刚之美。如《芦沟》、《过黄州》、《醉后口占》、《出栈》等诗中投射出来悲壮慷慨、雄直刚健的“霸气”。刘师培曾指出张问陶奇气自横,诗有霸气。其《题张船山南台寺饮酒图》云:“遂宁公子文章伯,壮年奇气横干镆。”张洪竟气于辇毂,对补救当时性灵派诗歌气质孱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晚清诗人金天羽注意到了这点,其《答樊山老人论诗书》云:“有清一代,诗体数变:渔洋(王士祯)神韵;仓山(袁枚)性灵;张(船山)洪(亮吉)竟气于辇毂;舒(位)王(昙)驰艳于江左”。
洪亮吉和张问陶不仅诗有奇气、雄气,还经常以“气”论诗。但“气”在二人那里有着不同的内涵。张问陶的气既有洪亮吉所言之刚正之气,也有洪氏少有涉及的先天之禀气。另外,张问陶的“有情那可无真气”,将气与情并举;洪亮吉则将气置于“性”、“情”之后。可见洪张对气的重视程度上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