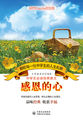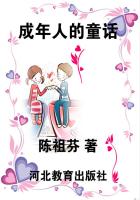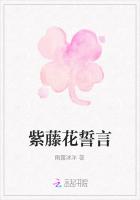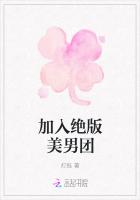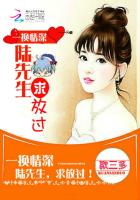洪亮吉论气最重“真气”,其举出诗文之有真气者,曰:“秦、汉以降,孔北海、刘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韩、高、岑诸人其尤者也。”其标举的“刘越石”曾被钟嵘评为“仗清刚之气”,“有清拔之气”114。可见洪氏所谓“真气”,是指诗中反映出的创作主体的内在刚正的气质。洪氏《庄达甫徵君春觉轩诗序》又举出“盛气”,云:“气不盛则无以举其辞”。其《论诗绝句》赞“岭南”诗派胜“江南”诗派而有“雄直气”:“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115洪氏鼓吹之“雄直气”,即阳刚之气。于阳刚之气之外,他又特别推崇“金石气”与“姜桂气”,116其《论诗截句》云:“偶然落墨见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此金石气与姜桂气与人品、节操相联系,指诗人具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人有坚贞崇高之正气,诗文必然反映其“金石气”;而有“姜桂气”,则诗的风格老辣,“下字造句坚致稳当”,易于感发人心。117这是他对“气”的新发挥。若结合《北江诗话》来分析,则更易明晰洪亮吉气之内涵。《北江诗话》的中心论旨是以下这段话:
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
且不论洪亮吉将“性”立于情之前,作为诗文之可传者的首要因素是否合理,但从洪氏把气置于性、情之后的第三位来看,其“气”是在性的规约下。而洪氏之“性”重高尚品质,则必然规定气之道德色彩,即正气,也就是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这更接近赵翼的观点。自曹丕将“气”用之于文学理论开始,后世关于“气”的论述不绝于典。清代对于“气”的讨论也非常广泛,如朱庭珍、方东树等人都对“气”进行过讨论。118赵翼也以“气”论诗,认为“气足”是写出佳作的重要关键。他论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但又指出“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原因在于“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于本朝赵氏虽推重吴梅村之诗,但又有不满:“若论其气稍衰飒,不如青丘(高启)之健举。”119此显然是着眼于“健气”立论的。可见,赵翼言“气”,特指“豪健之气”,一种真善、刚正的人格力量。
从张问陶言“气真”、“气不酸”、“气转雄”,可知其亦重“真气”与“雄气”。他多次论及“真气”:“前身自拟老头陀,真气填胸信口呵。”纯厚的真气填塞胸怀,诗便能任心而发,脱口成章。“语不分明气不真,眼中多少伪诗人”,则说明真气乃诗人创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倘不具备此气而强为诗,难成真正的诗人。“偶凭真气作真诗,无端落纸成诗文。”诗人有真气,落纸成文,即成真诗。他又举出“雄气”以论:“年来我渐悔雕虫,才劳精神气转雄。”雄气纵横,便见作家之真性情。此“真气”和“雄气”属于精神状态,受外界影响,如张问陶论洪亮吉“气自雄”,即因洪氏胸怀忧国忧民之奇愁所致。这里的气乃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与洪亮吉之刚正之气相通。
张问陶与洪亮吉同重刚正之气,是由个性气质所决定。洪张个性狷介清狂,洪北江质至直,甚至有些过明恩怨,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花和尚鲁智深称之,赞曰:“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张问陶诗友、画友、酒友甚多,而与北江尤为相得。二人能够成为忘年之交,与他们个性相同、情趣相投、志趣相近不无关系。在相交的日子里,张洪二人或唱和,或痛饮,或同讥佛事,120或放浪形骸。他们常常把盏高吟,痛饮夜半。一次,甚至醉卧雪中,与李白、刘伶神游。如此放浪不羁,难怪被风雅之士目为狂士。更有甚者,二人曾酒醉同跌入水中。洪亮吉《酒半移酌池上与张同年问陶皆失足堕水戏作一篇》,121记述了两人酒酣落水的憨态。
除了像洪亮吉一样重真气、雄气外,张问陶又强调抑塞磊落的“奇气”122、“霸气”、“江湖气”以及“秋气”。此气为生命本有的一种潜能,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这组气是孟子的浩然之气所难以涵盖的,更多地接受了道家之“气”,指有别于他人的个体之气。这种个体之气形成了每个人的不同的气质和个性,其运用于创作,是保证鲜明的创作个性的前提,故又相当于曹丕所谓的“文气”。此作家自然禀赋、个性气质,非后天所“养”之气。其不受外界制约:“无诗无酒气纵横”,由作家气质、情感等因素决定,不可力强而致:如宋玉“文藻开秋气”。船山“诗多秋气”123,即因两者遭遇坎坷,怀才不遇,郁寓于中所致。禀气有别,个性有别,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有了这种气,形诸笔墨,则纵横挥洒,机无滞碍。卢仝所独具之气,使他自成风格:“游戏韩门气不酸,不为岛瘦不郊寒。”张问陶以“气”论诗的特点,在论洪亮吉及其诗歌创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乾隆五十五年,27岁的张问陶和45岁的洪北江同年进士及第,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交往。相处日久,交谊弥深,因他们声名远播且交谊深切,世人以“洪张”并称124。又因他们诗名久负,被时人誉为“李杜”。船山则不无自负地夸曰:“旧时李杜愧齐名。”125说二人友情之深笃,李杜难敌。洪张声气相投,饮酒赋诗,唱和频仍。仅《船山诗草》中涉及洪亮吉的诗篇就达数十首之多,张问陶对洪亮吉的人品、诗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君诗六十又一首,我诗四百二十篇。
抱情各有适,众寡亦偶然。
同化奇光烛云汉,人能诋斥天能传。
(《小除日与稚存松筠庵祭诗各题长歌纪之》诗草卷五)
敢为险语真无敌。能洗名心更不群。
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
天涯梦绕卷施阁,尚忆狂谈坐夜分。
入关风雨暮匆匆,胸有奇愁气自雄。
(《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诗草卷六)
翰林昔未遇,名高神采王。
眼前真实语,入手见奇创。
五字作长城,骚坛踊名将。
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
(《题同年洪稚存卷施阁诗》诗草卷五)
无诗无酒气纵横,谁指伊吾问死生。
万里风沙悲独往,旧时李杜愧齐名。
(《怀稚存》诗草卷十五)
三年诗笔满黔中,
文奇应化百蛮风。
(《题枫林揖别图为稚存作》诗草补遗卷五)
才投戈壁忽归田,风马云车此七年。
绝域文章皆化境,更生岁月即飞仙。
诗经敛手神逾王,史未书名世已传。
(《寿稚存》诗草卷十七)
当年慷慨庆弹冠,曾有诗盟结岁寒。
爱我猖狂呼李白,看君光气夺齐桓。
携得惊人奇语在,招魂重与问青天。
(《过阳湖怀稚存》诗草卷十九)
洪亮吉天纵多才,于经史注疏、说文、地理靡不参稽钩贯,又善写诗及骈文,是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人口学家。其经学与孙星衍并称“孙洪”。与黄景仁为生死交,诗也齐名,有“洪黄”之称。张问陶亦才华卓绝,诗、书、画兼善。二人互相激赏,彼此推重。张问陶与袁枚神交,即系洪亮吉特意推荐,洪亮吉在推荐信中称张问陶为“长安第一”126。船山放浪不羁,稚存呼其“青莲再世”;船山则视洪亮吉为异姓兄弟:“异姓逢君疑骨肉,同朝知我耐饥寒”。洪亮吉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船山赞其“能洗名心更不群”。洪氏因痛陈时弊被谴戍西北,张氏深为不平和担忧,牵念悬望,“落日安西凝望远,浮云难掩故人情。”嘉庆十七年(1812),船山辞官莱州府,取道常州去苏州,经稚存故乡阳湖,怀念挚友“当年慷慨庆弹冠”,有感于其立身有磊落之气,赞云“看君光气夺齐桓”。洪亮吉才高八斗,但在科举应试中屡遭挫折。船山云:“翰林惜未遇”,为挚友的怀才不遇而不平。
洪亮吉和张问陶都多次在诗歌中将自己与对方并提。乾隆五十七年(1792),洪亮吉作《题张同年问陶诗卷》,127先是比较船山诗有别于同辈人诗作之处,云:“同辈二三子,诗各有所优。或有春夏气,亦或优于秋。惟君一卷诗,尽把秋气收。惟君一卷诗,宜剪秋灯读。我欲借春气,生君十指间。方君作诗时,桃李皆开颜。”然后高度评价了船山的历史地位:“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128船山则自豪地说“无诗无酒气纵横”,谁能对着二人问死生!虽然二人诗中“抱情各有适”,却能“同化奇光烛云汉”。他们的创作暴露了现实的弊端,但因为是发诸真性情之作,故“人能诋斥天能传”。
嘉庆七年,洪亮吉上《极言时政启》千言,痛陈时弊,遭落职发戍伊犁,期间有不少佳构,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如写天山雪景,洪亮吉言:“天山雪花大如席,一朵雪铺牛背白。寻常鸡犬见亦惊,避雪不啻雷与霆。”用语之大胆,可为前所少见。赵翼论其出塞诗:“人间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领。”评诗又论人。其《天山歌》,写尽天山的高、雄、寒,具体显现了雪深、云密、风猛。“绝域文章皆化境”,便是船山对其塞外之作力度和质感并见的赞扬。
洪亮吉诗本有奇气,督贵州学政,得黔地风云所感,奇气益出,诗风愈加雄奇。清代刻书家伍崇曜赞其“涉笔有奇气”。129稚存豪气雄健,嫉恶好善,伤时忧国,张问陶评其“胸有奇愁”,故“气自雄”。嘉庆元年(1796)正月中旬,洪亮吉贵州学政任满归京师,船山作《喜稚存至自黔南》诗,云:“小别各万里,重逢今五年”。知己重逢,船山设宴为老友洗尘,又专为稚存作“枫林揖别图”,赞其“三年诗笔满黔中”。洪氏高唱“吟咏以性情为主”130,反对依傍前人,要道“前人所未道”131,要求“翻空出奇”132,有所独见。但又强调“凡事皆有本”133,注重“须略谙时事,方不贻后人口实”134。其诗主性情的观点与在真的基础上又讲求“新”、“奇”,与张问陶诗学观相宜。故洪氏诗歌笔势奔放,用语奇崛,船山赞其“敢为险语”,以“惊人奇语”为奇文,文之奇都可化百蛮之风,又赏其诗作无人匹敌。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云:“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而洪亮吉恰有一双点铁成金之手,眼前平凡语,一经他手,顿时奇迹般地变得神采飞扬。故赞云:“眼前真实语,入手见奇创。”船山还高度评价了洪亮吉的才华与成就:“诗经敛手神逾王”,“歌声赛寰瀛,与岳渎抗”,洪亮吉以美才实学闻名于世,船山说他“名高神采王”,“史未书名世已传”。赞扬洪亮吉在清诗坛的地位,则是“五字作长城,骚坛踊名将”,“轩然读大作,一片宫音亮。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
卷施阁是洪亮吉的书斋,更是诗友吟唱雅集的好地方。洪亮吉曾有“夜半清谈振檐瓦”之句,135诗人的豪情可以想见。船山返乡回蜀,行至华阴,夜宿客栈,展读《卷施阁集》,忆往昔,夜半时分,酒酣耳热,兴豪清狂,论列上下千古;136看如今,夜深人静,孤灯独照,形单影只,只恨阴阳两相隔。悲伤之余,写下“死有替人应属我”,决心承继洪氏衣钵,慰藉亡友在天之灵。
张问陶论袁枚、赵翼
清代诗坛,袁枚首倡性灵说,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驰骋诗坛近50春秋,起到了性灵派主将和灵魂的作用。赵翼以其诗歌理论与实践,成为袁枚之外标举性灵说最力者,奠定了仅次于袁枚的性灵派副将的地位。张问陶以其才识和明确的性灵说主张,以及突出的性灵诗创作,成为嘉庆年间性灵派的重镇,是性灵派的殿军,成为与袁、赵鼎足而立的性灵派三大家。137袁、赵、张三大家不仅论诗主旨相同,且同气相投、同声相应,相互推许,密切合作,合力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袁、赵保持密切来往近二十年,其友谊自不必多言。二人与晚辈张问陶也同样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随园船山神交五年,赵翼晚年亲自过访小他四十岁的张问陶。张问陶在《船山诗草》里,记录下了与袁、赵的交往,对两位前辈身怀推崇之情。
张问陶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选庶吉士,五十八年(1793)授翰林院检讨。是年,袁枚“访京中诗人与洪稚存。洪首荐四川张船山太史,为遂宁相国之后。”138这是袁枚首次听说张问陶之名。后来袁枚追忆,早在乾隆丙辰年(1736)于京师与船山之父张顾鉴“订杵臼之交”,作“车笠之盟”。袁枚在陕西任上,也与船山叔祖张勤庞(时任陕西兴安州知州)“琴歌酒赋,备极绸缪”139,故而张问陶视袁枚为前辈。船山作七绝《见怀》与袁枚,云:“先生八十方知我,不死年年望寄诗。叠纸细书三百首,邮筒飞递未应迟。”诗前自序:“癸丑假满来京师,闻法庶子云:同年洪编修亮吉寄书袁简斋先生,称道予诗不置。先生答书曰:‘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感先生斯语,自检己酉以来近作手写一册,千里就正,以结文字因缘。书毕,并上绝句一首。”出于对袁枚的推崇,张问陶将己酉(1789)至癸丑年(1793),四年多所作诗篇选三百首,手书一册,取名为《推袁集》,寄袁枚就正。140袁枚收到书信后,在《答张船山太史书》中说:“诗人洪稚存太史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信来颂执事之才为长安第一。但闻执事已请假还蜀,未知何时得通芳讯,心犹拳拳。不料中秋前十日于王葑亭141给谏家接到《见怀》二十八字,意思深长,有邢颙言少而理多之妙。读《推袁集》一册,命名先不敢当,虽大君子舍己从人,以谦虚为坐荐,游戏标题无所不可,而当今作者如云,万目骙骙,得毋咤执事之才认符拔为麒麟,拜票客为大将乎?损执事之名,折野人之福,千万以换去为祷。然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142王友亮称袁枚“入海求诗不厌深,肯为俗手度金针”143,信然!袁枚推重船山,其奖掖后世略见一斑。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五月,船山收到袁枚来信后,又赋诗《寄简斋先生》诗以答144,十分恳切地表达了对袁枚的崇敬之情,并告知袁枚家父得其消息后的喜悦之情,希望他游历四川,与老亲重叙旧情。袁枚收到后,即作《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有云:“忽然洪太史,145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槃槃大才子。”146六月,有人说船山诗学随园,船山作《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二首》,又在十一月提前作诗,贺袁枚次年八十大寿,题名《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嘉庆元年(1796),船山得随园信后答诗代信:《丙辰仲冬十三日得简斋先生手书答诗代柬》147。嘉庆三年船山从遂宁丁父忧后回到京师,得知随园丁巳年已卒,作诗《袁简斋大令卒于随园》以挽。在张问陶与袁枚的诗书往来中,尤以贺寿诗和挽诗最重要,其对袁枚的人生、诗学理论、诗歌成就及其诗坛地位作出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
(诗草卷十一)
举世推前辈,遥遥廿四科。仙云微点缀,铜印小摩挲。
清浊泉皆好,风尘梦不多。略沾春气息,花影镜中过。
偏不住西湖,幡然嗜好殊。远寻江令宅,幻出辋川图。
山在园中小,人为世上无。愿公忘结习,莫更想蓬壶。
万物供游戏,婆娑八十年。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
有欲人偏服,无功世亦传。预完生死局,哀挽及身前。
纸贵千丸墨,衣香万壑云。名山都识面,荒徼也徵文。
吐握情能到,丹铅老更勤。古今才一石,公在不曾分。
披卷灵光出,宣尼不忍删。好诗堪下酒,退笔定如山。
陡峡开神斧,香云解妙鬘。世人争格律,谁似此翁闲。
小说兼时艺,曾无未著书。气空偏博丽,才大任粗疏。
考订公能骂,圆通我不如。只今惊海内,还似得名初。
寿许通才得,皇天不忌名。洗儿休恨晚,骂佛转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