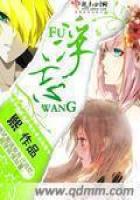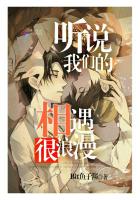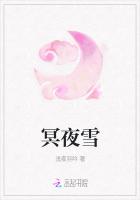人一生要读很多书。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重点。青少年时期所读的书,对人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我的童年处在一个非常时期,书店里没有经典童话,没有民间故事。记得母亲给我买的第一本读物,是彩色连环画《育婴堂里的斗争》,看得我噩梦连连。那个年代的出版物都带有火药味。家乡小镇的书店不大,读物数量有限。读一年级了,我写信给上海的大姑,要她给我寄来《红小兵画报》。这是那年代唯一的儿童读物,虽然只有区区几本,也带给我莫大的快乐。家里还有两本书,一本是陶承《我的一家》,我读了无数遍,欧阳立安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激荡不已;还有一本是瞿秋白《多余的话》,那时候我读不懂。
大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工厂的图书馆开放,我用父亲的借书证借书看。读过的书中,印象深刻的有科普读物《火山和地震》、《蛇岛的秘密》等。还有一本写渤海湾捕鱼的书,书名现在想不起了,书中写到钓带鱼,钓起一条,尾巴上咬着另一条,最多时钓起一串有四条带鱼。这个情节使我十分惊奇,以至于后来我遇到渔民,会反复提起这个细节以求佐证,但渔民们语焉不详,估计书中所描写的只是个案。那个年代仅有的几部儿童小说,如描写农村赤脚医生的《红雨》,描写农村少年成为体操冠军的《新来的小石柱》,描写洞穴探险的《三探红鱼洞》,以及《高玉宝》等。这些书尽管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但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可爱,品格令人钦佩,加上情节曲折,情趣生动,均风靡一时,给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这些书的封面,少年时代的记忆扑面而来,仿佛触手可及,十分亲切。
值得一提的还有浩然的《幼苗集》和《西沙儿女》。《幼苗集》是儿童短篇小说集,书中华北农村风情浓郁,一个个纯朴善良的孩子呼之欲出,语言清新质朴,散发出持久的文学魅力。《西沙儿女》分正气篇和奇志篇,合起来是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用浪漫主义的激情描写奇异的南海风光,正面反映西沙海战,表达了爱国主义情怀。相比《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的这两部小说很少被提起,在特殊年代里却有特殊的影响力。
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是电影《海霞》的小说原作,在当时传阅很广。小说描写了东海某海岛一群女渔民抓特务保卫家乡的故事,其中有个关于海鸥的民间传说,特别曲折特别悲惨,现在想起来仍印象深刻。《沸腾的群山》、《激战无名川》、《连心锁》、《春潮急》等小说,只记得书名不记得情节了。至于那本《虹南作战史》,只读了一点,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只得放弃。在阅读极其饥渴的年代,居然还有无法读完的书,可见这本帮派小说从内容到形式的拙劣、粗鄙。
历史终于翻过沉重的一页。那个年代过去了,不同班级的同学中,开始出现一些以前不敢公开拿出来的读物,如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以及《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等,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战火中的青春》等红色经典小说。借这些书皮破损、纸张发黄的旧书,要排队等很久,一到手赶紧连夜看完,第二天送到下一位同学手中。迟来的童话故事,向我展现文学温情、奇趣、幽默的一面;红色小说,告诉我过去年代真实残酷的人生。隔壁班级有位同学家里订阅《人民文学》,我得知后,经常去他家借,去得太频,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总会满足我。在《人民文学》读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后,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文学进入了新时代,我的面前打开了另一扇窗,通过这扇窗,我看到了更多更远的风景。
阅读面不断拓展,阅读量逐渐增加,在形成自己的阅读观点后,再回头看,发现少年时期读过的书已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我比较偏好主题深刻、关注现实人生、情感充沛的作品,而对武侠、言情、玄幻类则提不起兴趣,读得也极少。这样的阅读态度,显然与我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有关。少年时期读过的书,甚至还影响到人生,这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