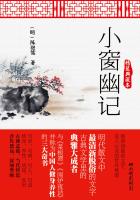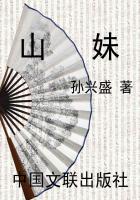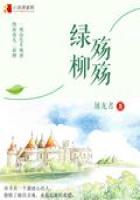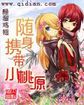凉风习习的夏夜,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到公园放松身心。他们有的散步纳凉,有的练太极拳、做健身操,有的大汗淋漓爬山登高。在幽静的荷花池畔小桥上,有人在自弹自唱,沉郁又深情,唱的是《驼铃》,一首三十多年前的电影歌曲。那年轻人唱罢,我上前跟他聊了起来。我说这么老的歌,被现在的年轻人唱,而且唱得原汁原味,真是意外。年轻人谦虚起来,说刀郎唱过这首歌。“啊?你看过电影?你会唱这首歌?那我们一起唱!”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了,歌词忘了不少,跟随着年轻人的节拍,我重新拾回了有关老歌的记忆。往日的情怀穿越时空的尘埃,泛出温暖的光泽。回家的路上,那些学生时代唱过的歌,以及歌声中的青春场景,一幕幕浮现在脑海。
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大多数是工程师,印象中,他们严谨务实、不苟言笑。一位带苏北口音的老师,有次讲着讲着,不知什么原因,话题离开了课本,而且离得相当远。他谈起了歌剧《小二黑结婚》,越说越高兴,就整了整嗓子,开始唱“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看着他陶醉的样子,我们目瞪口呆。歌声一结束,教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老师微微有些脸红,他告诉我们,要成为一名工程师不能仅仅只有机器、图纸,美妙的音乐是心灵的良师益友,动听的歌声能够陶冶情操。“热爱音乐吧,同学们。”一番恳切的话引起我们的沉思。
后来我们明白了,老师讲这番话是有含义的。在三个班级中,一班的男同学调皮爱嬉闹,女同学穿上藏族服装,且舞且歌《洗衣歌》,长袖摇曳,铃鼓叮当,煞是好看。三班同学比较年长,有位男高音柯同学经常在走廊练歌,声情并茂的《再见吧妈妈》,洒脱豪迈的《祝酒歌》,悲愤激昂的《松花江上》,他一唱,我们鸦雀无声,凝神谛听。三班还有位镇海中学文艺班考上来的小提琴手薛同学,常常在安静的角落练琴,乐音缤纷,片片醉人。只有我们二班最不活跃,很多同学教室里一坐就是一上午,连课间十分钟都不挪动。偶有个别稍稍活跃一下,最多也就是讲几个笑话而已。老师们几次三番要求我们多活动,活泼些。那位苏北口音的老师要我们热爱音乐,想必也是出于同样的善意。
渐渐地,我们终于有所触动,开始行动起来。鄞江桥的王同学拉起了手风琴,常常废寝忘食;郭班长爱上了越剧,贺老六唱得惟妙惟肖,他还有台收音机,午休的时候我们常常聚在一起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外国音乐节目;金塘刘同学学唱英文歌“昨日再来”;有位郑姓的女同学,课余她悄悄掏出口琴,吹一曲“雪绒花”,簧片轻颤,琴声清亮而悠长,引人遐想。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听歌,被班主任汪老师指定担任文艺干事,我颇感“压力山大”,自勉一定要不辱使命。学校举办合唱比赛,要求各班准备两首曲目参赛,我只得硬着头皮上,跟一位部队文工团转业的大嗓门老师学了几招,排练了几回。正式演出时,到“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轮唱部分,我一紧张,手臂略有迟疑,比画错了节拍,歌声就不整齐了。比赛结果当然不理想,为此我自责了好久。还有一次文艺会演,我们班报的节目中有相声,表演者是来自沈家门的龚同学等,但剧本指定由我写。我很纳闷,老师居然叫我这样喜感全无的人设计相声台词,太不可思议了,想想大概老师也不懂相声吧。但又不得不写,我涂涂画画,勉为其难。龚同学他们见我实在没有花头,自己专心去设计排练了。从演出现场效果看,他们的说学逗唱还相当不错。
不同年龄层的人各有自己喜爱的老歌,我独喜爱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抒情歌曲,那个年代港台流行歌曲还没有进入内地。那些歌旋律优美动听,内容也相对比较单纯,像《雪绒花》、《太阳岛上》、《青春啊青春》、《大海一样的深情》等等,至今仍在传唱。岁月流逝,情怀依旧,每次听到一首老歌,我就会想起当时特定的场景。比如,有一个雨夜,我走在早已被拆迁的鼓楼老街上,往学校赶。因为没带伞,我尽量靠近街檐,旁边人家有的还没有关门闭户,有线广播喇叭正在播放每周一歌《泉水叮咚响》。“泉水叮咚,流向远方……”雨水顺屋檐滴落,滴到我的脖子上。记忆中那条老街好长,我从这头走到那头,时轻时重,正好听完这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