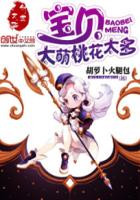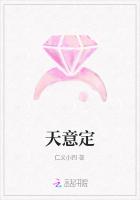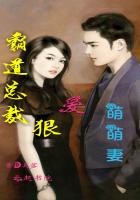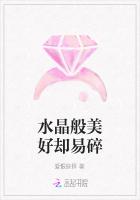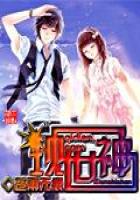百老汇音乐剧改编成电影后大获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像《音乐之声》、《窈窕淑女》、《红磨坊》等等,这回是《悲惨世界》。很多像我这样资深又挑剔的影迷一致用最漂亮的形容词对这部电影大加赞美,在影院,有人频频拭泪,有人和着歌声哼唱,观影结束有人鼓掌。虽然它也有瑕疵,但它带给观众的强烈震撼和深深感动,使这点瑕疵被忽略不计。
电影《悲惨世界》脱胎于舞台剧,高明的导演赋予它史诗般的震撼力,使其与已成经典的音乐剧相映生辉。
音乐剧《悲惨世界》保留小说的情节主线,再现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和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更重要的是,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不公正社会的强烈控诉,对人民起义的盛情赞颂,这些鲜明的思想倾向,都在剧中得到完整体现。音乐剧仿照歌剧的结构框架,全剧不带一句念白,主要角色每首咏叹调前都有叙述剧情的宣叙调,二重唱、三重唱甚至多重唱展现人物之间的情感纠结,恢宏的合唱推动剧情屡屡到达高潮。芳汀的独唱《I dreamed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是全剧最感人至深的唱段。芳汀被赶出工厂,穷困潦倒,她回忆曾经拥有过的和善的朋友、亲密的爱人,而眼前这种地狱般的生活粉碎了她的梦想。艾波妮暗恋马瑞斯,她独自在雨夜街头徘徊,幻想和他并肩散步直到清晨,《On my own(独自一人)》唱尽她对无望之爱的悲怨、凄楚和空空荡荡。另一首名曲《Stars(繁星)》反映的是警探贾维尔的铁血胸襟,他对群星发誓,一定要抓到冉阿让,绝不放弃。在ABC之友社咖啡馆,学生领袖安卓拉激情澎湃鼓动革命,他眼中“红色是开创新世界的晨曦,黑色是终将结束的黑暗”,而坠入情网的马瑞斯却说“红色是炽烈的欲望,黑色是心底的绝望”,这首重唱加合唱《Red and Black(红与黑)》刻画不同人物的心理状态,有深情的喟叹,也有激情的煽动。紧接着的大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你听到人民的歌声吗)》表达人民不愿再被奴役、渴望社会公正的心愿,他们冲上街头,心跳与阵阵战鼓共鸣,坚信美好的明天终将来临。音乐剧《悲惨世界》于1985年搬上伦敦舞台以来,已有数十个不同语种的版本,全世界有七十多个城市常年公演此剧,庞大的观众群为这部电影奠定了很好的市场基础。
电影《悲惨世界》突破音乐剧的舞台局限,运用电影语言和现代技术,还原了两百年前雨果笔下的巴黎社会历史风貌,给观众极具震撼力的影像效果。在音乐剧改编电影这个领域,这部电影创立的一些新的标杆,注定它将成为又一部经典。以往,音乐剧改编成电影一般只保留主要唱段,一些次要的、叙述剧情的宣叙调改成对白,而这部电影保留了音乐剧全部唱段,只添加几句对白。这是因为,作曲家勋伯格运用瓦格纳创立的“主导动机”概念,用特定的旋律表达不同的主题,全剧音乐浑然一体,无法割裂。如开场的《Look down(向下看)》主题属于底层阶级,在贫民区、德纳第旅馆等场景反复出现;善的主题由米里哀主教唱出,成为冉阿让的动机,在冉阿让独白、与贾维尔对峙、贾维尔自杀等场合均有呈现;芳汀爱的主题在冉阿让、艾波妮的咏叹调中也有完整再现,自由动机则在起义、宣战中一脉相承。如果删除了其中哪一段音乐,都会破坏全剧音乐的完整性。演员真唱,同期录音,是这部电影最大的看点。先录音后拍摄,演员根据配唱对口型,观众已经看腻了这样的老套套,导演果断投观众所好,当然大获成功。为了适合演员真唱,导演适当调整了某些唱段的高音、长音,使演员重在演,不必字正腔圆地唱,像安妮·海瑟薇那首为她带来奥斯卡荣誉的《I dreamed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就更像是演出来的。手持摄影机拍摄,大量特写、近景,长镜头的运用,是这部电影的摄影风格,也使电影悲惨、悲壮的主题更加鲜明。冉阿让感动于主教的恩情唱出独白《What have I done(我到底做了什么)》,冉阿让的凄惶、忏悔,到决心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心路历程,在长镜头中都有细致变化。安妮·海瑟薇的那首四分钟独唱特写长镜头中,她从回忆、无助到绝望地泪流满面的全过程,给观众强烈冲击。导演高超的场景调度也使电影增色不少,如重唱《One day more(再等一天)》表现革命前夜各路人马的打算:冉阿让要带柯赛特逃亡英国,柯赛特与马瑞斯相恋,艾波妮暗恋,安卓拉准备战斗,贾维尔追击,画面依次迭现不同人物在各自时空中的动作,很具观赏性,也与原著浩瀚的结构相吻合。
电影《悲惨世界》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加深了感受。这几天反复播放的是舞台剧十周年、二十五周年纪念演唱会,越听我觉得越有味。同时我还找出雨果的原著细读,再次沉浸在名著的魅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