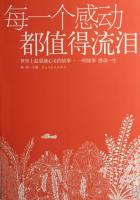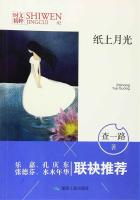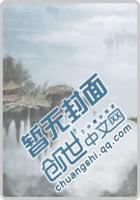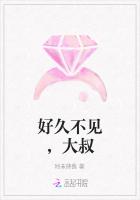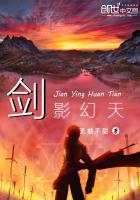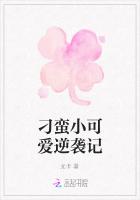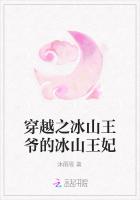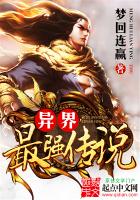在普契尼的四大歌剧代表作《波希米亚人》、《托斯卡》、《蝴蝶夫人》、《图兰朵》中,我比较偏爱《蝴蝶夫人》。普契尼歌剧的一些基本特色,诸如取材于世俗生活,出人意料的悲剧结局,多姿多彩的音乐场景,优美的旋律和脍炙人口的咏叹调等等,在《蝴蝶夫人》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普契尼歌剧这种迥别于瓦格纳、威尔第等前辈大师的鲜明风格,把歌剧艺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蝴蝶夫人》改编自话剧,据考证,话剧又改编自19世纪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洛蒂是一位海军军官,在四十多年的航海生涯中坚持业余写作,作品大多描写各国风情。《菊子夫人》有自传色彩,以西方人的眼光描摹日本长崎的山海庙舍、风土人情,充满了绚丽多彩的东方情调,令当时读者入迷。
我收藏有《蝴蝶夫人》拍成电影的两种影碟和几种唱片。1974年版的电影有超豪华的组合: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弗蕾尼和多明戈联袂出演,演绎和演唱都是超一流的,可是电影拍得比较草率。1995年法国依蒙拉图电影公司拍摄的《蝴蝶夫人》,竟有女高音黄英、女中音梁宁、男高音范竞马三位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使人惊喜连连。
歌剧演员不仅要唱得好,而且还要会演戏。黄英版《蝴蝶夫人》影像华丽,制作精良,视觉效果非常好,我看过数遍,每次都有新感受。电影在突尼斯一处海湾拍摄,导演给黄英的出场是一个长镜头,黄英打着花伞踩着叠叠碎步由远及近一路踏歌而来,神态活泼娇羞,符合十五岁少女的身份。四分半钟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也是一个长镜头,黄英站在屋外一处类似“望夫崖”的山冈边面朝大海,镜头由远景逐渐推近至特写,黄英脸部的表情依次呈现温柔、向往、自信,十分细腻。这部电影在全球公映,发行影碟,是最好的歌剧电影之一。梁宁和范竞马也表现不俗,特别是范竞马,热烈奔放,洒脱倜傥,风头直追美国男主角。范竞马曾被多明戈称为“近十年来欧洲罕见的男高音”,英国BBC月刊曾评论他是“拥有与帕瓦洛蒂和传奇式人物吉利一样迷人歌喉的男高音”。梁宁的音色如中提琴般厚实低润,高音区又像单簧管一样柔和明亮。黄英、梁宁、范竞马在国外都出过数张唱片。上海声像公司发行过黄英的首张专辑《深情的咏叹》引进版,里面收录了普契尼、多尼采蒂、罗西尼等歌剧和几首中国歌曲。最近一次在电视上看到黄英,是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的演出活动上。范竞马在荷兰发行的《我住长江头》中国经典艺术歌曲和民歌专辑,收录了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这些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一流歌唱家演唱中国歌曲,更具气魄,更精彩优美,给听众全新的感受。
歌剧要吸引观众,除了剧本要具备戏剧元素,最重要的是要有出色的音乐,普契尼具有只用很少的音符就谱写出最优美旋律的神奇能力,他的音乐感情浓郁,常常是一段旋律,即便只是短小的过门乐句,也能直接诉诸情感,直指人心。《蝴蝶夫人》中的唱段《晴朗的一天》、《我亲爱的小宝贝》,以及第一幕的二重唱和第二幕的场间幕后哼声合唱等,都使人入耳难忘。巧巧桑新婚之夜遭到众亲唾弃,孤苦的境遇使她对平克顿的爱情本能地带有寻求庇佑的祈愿,这时,爱情的甜蜜已经退让其次,对托付终身的期待使她更急于倾诉,而花花公子平克顿的甜言蜜语源自对美色的渴求,早已被炽热情欲所燃烧。在第一幕长达十五分钟的爱情二重唱中,巧巧桑和平克顿不同的音乐形象轮番呈现,交相呼应,时而委婉舒缓,时而高亢激越,最后到达辉煌坚定的最强音。这里,丰富的配器和对人声潜力的发掘,使这段二重唱绚丽多彩、气象万千,美得无以复加,简直令人心碎,我每次听《蝴蝶夫人》总要把这段反复听上好几遍才过瘾。
现场看演出,与在家里看影碟听唱片相比,有更慑人魂魄的感染力。在现场,戏剧张力、音乐表现直接诉诸观众感官,直达人心,易于接受。而观众的反应,又给演员以良好的互动,刺激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演得更加精彩。《蝴蝶夫人》是最早引进中国舞台的西方歌剧之一,也是中央歌剧院的保留节目,几年前,我在逸夫剧院看过中央歌剧院在浙江的巡演,那次主演是柳红玲。歌剧演出的灵魂人物是指挥,而主演的作用是撑起整台戏,两者珠联璧合,才能够完成演出。柳红玲的声线比较浑厚、纯净,演绎十分到位准确,有很多惊喜的表现。乐队指挥高伟春一头白发,身手不凡。乐队规模不大,乐手表现比较精准,合唱团更具有强烈气势,整台演出一气呵成。全剧结束,观众还沉湎在《蝴蝶夫人》的魅力里,静默了一会儿后,接着爆发出长时间掌声。
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普契尼》的封面,是普契尼生命晚期的照片,那时音乐家遭受喉癌的折磨。他戴礼帽,穿西服,结领结,脸部轮廓棱角分明,深深凹陷的眼眶中,凝视着远方的目光尽管依稀仍有桀骜不驯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对宿命的无奈。普契尼出生音乐世家,幼年丧父,青年时期饱受贫穷饥饿,成名后热衷于打猎、汽车和快艇,这样的经历折射在作品中,每每呈现出乖戾的音乐动机、凄美的旋律和复杂的多元性,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