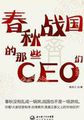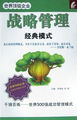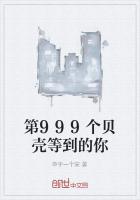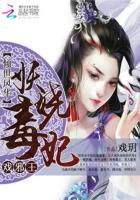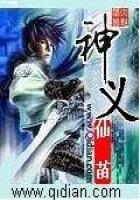意识,是“人类特有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最高形式,是人的有意心理部分的总和”。它有六个基本特点:自觉性;目的性;丰富性;深刻性;能动性;创造性。瑞士心理学家丹尼什认为“意识指的是一种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知能够以其清醒的、理智的和周全的方式发挥功能。意识是精神存在的核心”。这两个定义的共同点便是强调了人的主动作用。而生命意识就是指人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在与自我之外的一切的关系活动中有意地发展丰富自我,以追求自我价值最大实现的精神活动。在人生上它表现为关注人存在的价值,重视个体精神生命的丰富,在创作上则表现为关注人物的处境、人物对命运的选择和人物在这种选择中的精神状况。
司马迁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史学家、文学家。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意识的灌注,《史记》的思想感情异常丰富,其历史影响也十分深远。这里我仅就司马迁关注人的生命意识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司马迁之前及同时代人对生命的认识。
殷商时期为中华民族有文字的文明史的开端,商人迷信天命,尊事鬼神,不大重视人的价值,常用人作牺牲来祭祀鬼神,还用活人殉葬,根本不重视人的生命,更别说生命价值的实现。西周的统治者从殷商的教训中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初步树立了人的价值观。周初统治者还反复强调要关心、照顾鳏寡孤独,有了人道主义色彩。但这只是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强调安民的重要性,所以,“保民”其实是“护治”。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纷纷推出自己的学说,其中也大多涉及对人的看法。孔子说“仁”者“爱人”。杨伯峻先生认为“孔子心目中的人和民的概念有时相同,有时相异,但他重视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也就是说,孔子重视一切人的性命,在精神层面上却只注意士,民是排除在外的。到了孟子则有所进步,开始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利。荀子也提出人要制天命,但大体上,生命还是严格在等级之内的。与儒对立的墨家谈“兼爱”、“非攻”,却以“利”为准则,关注人的生命意识中带有较强的政治功利色彩。老庄讲养生,既要“绝学”、“弃智”,又要顺应自然,其结果是忽视人的主观力量。法家治人“严而少恩”,严刑峻法重于人的生命,基本上不考虑人的情感需求。阴阳家的眼里则把天与自然神秘化,生命只是天命的结果而已。
只有战国初期杨朱提出“为我”、“轻物重生”,他认为人只有以自己为目的、保全自己的天性与真情,才是有价值的,为君主牺牲自己的价值是可悲的。他在中国古代最先强调了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但又走了极端,把个人与他人及社会完全对立起来了。
汉初统治者废除秦朝苛法而尊黄老之学,百姓在无为的统治策略下的确过了一段休养生息的生活。可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情况发生了变化。儒学大师董仲舒把战国邹衍的阴阳学与春秋公羊学结合起来,提倡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论”、“五德循环论”,宣扬天命的不可违抗,这样一来,时代前进了,官方意识形态对人的关注反而弱化了。
司马迁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他的父亲司马谈熟知诸子百家,尤喜黄老,司马迁自然深受影响。一般认为,司马迁师事过董仲舒,跟他学习公羊学。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存在许多疑问(如陈桐生在《文献》2001年1期发表的论文《论〈史记〉“厥协六经异传”》即提出一些质疑),但司马迁受过公羊学微言大义的影响,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西汉中期复杂的思想交汇的背景下,出现了司马迁这样一个极其关注人的生存、真正重视生命的划时代思想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虽说与当时的“天人合一”的权威思想有一定关联,但他处理天人关系时,其重心在人而不在天。“天”没有压抑人的生命意识。司马迁以其特有的史家风范和人道情怀去思考自我的生命价值并推及时代中人、历史中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状况。《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司马迁生命意识的结晶。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看看司马迁思想前期也就是在李陵之祸以前的生命意识特点。
司马迁最初思考的是自我的生命价值。这时的他才华横溢、年富力强又得以跟随汉武帝壮游天下,有着强烈的实现自我的要求。他“少负不羁之才”,有很好的天赋,再加上“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江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昆明,还报命。”一方面是家学渊源又孜孜以求,一方面是少年得志遍游天下,天赋、才学与阅历见识都使得司马迁不可能甘于平庸的人生,他有着让生命更加绚烂的渴望。所以他要“拾遗补艺,一家之言,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最终“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对于完成这部宏伟著述的才能,他是非常自信的。他自负地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可见,司马迁是把自己创作《史记》与孔子编写《春秋》相提并论的,自然,他也希望自己的《史记》可以像《春秋》一样成为“补弊起废”具有社会作用的史书。不过,此时司马迁的人生理想还是忠君显亲扬名,生命的价值就是效忠皇上为繁盛的帝国建功立业,他希望自己“上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这也是同时代里士人的共同梦想。
生命的朝气蓬勃,胸襟的阔大恢弘,阅读的广博深厚,又使得司马迁有着“爱奇”的性格,遇事总是要亲自查探一番。传说中的五帝、大禹的奇闻,他去了解个究竟;孔子的故里,他去瞻仰;甚至还沿着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走一遍;屈原投江的地方,他也去凭吊。总之,他把他旺盛的精力都投入到历史中的奇闻奇事、奇人奇语上。他接触各种身份的人,不分贵贱贫富。他饶有兴味地发掘他们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反对平庸,接触异端,热心于生命中卓异的东西。班彪因此而批评他“欲以多闻广载为功”。郑樵则赞扬他“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记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两种态度截然不同的评价道出的是《史记》的同一个特点,即详尽宏奇。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思想发展具有转折意义,在此以后,司马迁的生命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果说,这时的司马迁是因为自身无穷的生命力而对生命产生一种本能的珍爱,那么,“李陵之祸”则把这种珍爱推向沉静又怨愤的思考,从而,生命意识吸纳进更丰富的内涵,向纵深发展。当自己的身体突然承受奇耻大辱的刑罚后,是生还是死的问题突现在面前。司马迁思考的最终结果是选择生存,留下有用之躯以完成《史记》。
这不是简单的求生。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司马迁的禀赋、才学与非凡的抱负,和他不甘于平庸的性格。所以,当他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苦难甚至毁灭的威胁时,他不可能屈从、认命。司马迁对生死的痛苦思索,最直接的体现在《报任少卿书》。从此文中可以看到,司马迁首先感受到的是无以复加的耻辱,他说“祸莫惨于欲列,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可比数”;“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面对这种耻辱,是否应该按传统的观念“杀身成仁”以全士节呢?司马迁不是没有想到死:“仆虽怯儒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人不能早日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
司马迁在一般士人不能忍受的耻辱中开始用不同于以前的目光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问题。本来,因为“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二十余年,他也曾“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且,他为李陵说话也是为了“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可结果却以口语获罪。再加上面临灾祸时自己又陷入“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窘境。连李陵这样的将门之后“举事一不当”也被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自己心目中的明君也只凭一时的喜怒来作决定。他进而发现在君王眼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在世人眼里也是“流俗所轻”,自己则“鄙陋没世,文彩不表于后世”,这样死,是“伏法受诛,若九牛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样死,“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死既毫无意义,生也极为困难,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在对生命的反复思考中,司马迁生存的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了,这种欲望进而凝聚成一种生命的抗争意识,他要让有限的生命去实现对永恒的追求。
他想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和《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由此,司马迁对生命思考的结果是:古今圣贤大多遭受过重大挫折;挫折之后都心存郁愤;然后用著述寄托生命之志与思;这些著述使圣贤的生命在历史的沉淀中愈见光芒。司马迁从前贤的生命之路中找到了力量,再加上父亲病榻前的嘱托,二十多年的见闻学识的积累,已经进行了七年的《史记》的编撰,司马迁终于选择了生:他要“发愤著书”,他要“成一家之言”。尽管这种选择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粘衣也”。但是在选择生的同时,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与古圣先贤历史名人进行精神对话。这种对话使《史记》不再是“资于治道”的历史教科书,不再是为所谓帝王作“家谱”,而成为司马迁的思想生命的结晶。
司马迁把生命意识灌注到历史人物身上,在他们的言行中寄托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和理解。
此时司马迁从浪漫狂想中逐渐清醒,也从时代中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他反观前代和所处时代的思想及人物,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的条件,而是注重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的程度,只要这些历史人物在既定的条件下及时建立功名,就对他们的生命给予高度评价。于是,在思想的变化发展中,司马迁更加关注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命运,或者说,司马迁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着他笔下的生命,并把它形诸笔端。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司马迁高度肯定历史人物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要求。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奇语:项羽,“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刘邦,“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陈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孟尝君,“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霍去病,“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连小官吏宁成也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这些豪言壮语凸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展示着生命的无穷的能动力和强烈的生命意志。与司马迁对生命的感受非常吻合,他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美,生命力量的美,生命意志的美。言出自历史人物之口,情实出自司马迁之心。这些语言材料的选用既反映了司马迁“爱奇”和崇尚英雄的性格,更表现了司马迁把生命激情转而曲折地移情至笔下人物的本意。
第二,司马迁充分肯定社会阶层人物对历史作出的贡献,肯定他们各自的生命价值。
《史记》第一次把医卜星相、游侠刺客、俳谐倡优、商贾博徒载入史册,给他们以应有的位置。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在通过比较贫富者的生活得出“凡边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句话已尖锐地揭示出人的精神很容易受到经济的重压。那么,人民通过求富来改变自己生命受轻视、精神受压抑的处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主观上证明了自身价值,客观上增加了社会财富,“智者有采焉”。虽说司马迁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士”与“民”的界限,但他已经在前人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不仅不再轻视民的存在,而且能够尊重关心他们的生命需求。当然这里面也融有他曾因“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而就极刑的苦楚。
第三,司马迁更为关注封建集权政治下儒士和文人的道德选择以及他们对文化发展的意义。
虽然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里,历史和文学并没有截然分开,但他已经为儒士和文人分别立传,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把儒士看作是专门从事六经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工作的人,而把文人看作是专门用文辞抒发内心情感的人,他尊重前者,也赞扬后者。因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更为珍视自己及同类人的精神产品,更懂得它们的意义。又因为他真切地体会到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对人的压迫,尤其是对人精神的压迫,所以,他努力探寻着这些文化人的内心世界。
儒林中的申公、辕固生、儿宽、董仲舒等传经之儒坚守儒家的操行标准,道不行则退而治经学,绝不肯为趋富贵而损德操。而儒者中如公孙弘、主父偃俱已仕进。他们奔走到花甲之年方才被起用,所以格外珍惜,一心媚上,“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迎合了皇权的需要,所以发达,耿直的汲黯批评他们“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真是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们的精神状态。文人如屈原贾谊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却不能施展,又不肯随波逐流,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终于一个自沉汨罗,一个忧郁而死。而司马相如则专作些粉饰盛饰王朝的应制之作,而且为了保全自己,还不得不常常称病不出,以躲避政治的漩涡。这是个软弱的文人,每每宏篇大制之中,只能在末尾稍稍现出一点讽谏之意,也难怪受到“劝百而讽一”的讥刺。
以上两两相对的比较其实也只是德行上的,从这比较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真挚地赞颂着这些文品与人品兼美的智识者。可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是非却绝不能只在道德的法庭上,这一点,见识超乎一般史官的司马迁是深知的。他选择这些类型要说明的也绝不只是简单的好与坏的问题。这也表明司马迁的生命意识已进入更高层面的思考了,也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评价。他发现每一种生命形式的选择都会使个体的精神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因此,文化人的生命应该尽可能地对文化作贡献。所以司马迁既详细记述了申公、辕固生、儿宽等人传经的艰辛和身体力行的执著,同时也实录了公孙弘作学官时上书进言大兴儒学的功绩;既称颂屈原内容深广、感情浓郁的楚辞,同时也赞叹司马相如宏篇丽制、归引节俭的汉赋。文化需要多元,对文化的贡献也是丰富多样的;有文化思想的传承,也有文化传播的推进,有文学风格的创新,也有创作手法的演进,而且这些文人们就是因为他们对文化的贡献才得以青史留名。
第四,司马迁的生命意识还表现在:把历史人物的命运与自我感受的共鸣之处以隐微之语传达出来。
如《平津侯主父列传》中,“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孔车收葬之。”这不正是司马迁遇祸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同声吗?《日者列传》中“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鞹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这不正是对那些“全躯保妻子之臣”的严厉指责吗?而“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不也是对自己因言获罪的哀叹吗?也因为这些话,我同意张大可先生认为《日者列传》是司马迁原作的看法。也只有司马迁能在那个时代提出这样大胆的观点。
当然,如果仅仅以为司马迁是在借历史人物泄一己私愤的话,那就太小视司马迁了。司马迁的“愤”的矛头是指向人的生命的险恶处境的。司马迁那么热爱生命,尤其是有着无穷生命力和卓异才华的生命。所以他才会对时代社会中压抑摧残生命、阻挠生命价值实现的巨大势力产生无比的愤恨,他想用他的笔去为生命唱赞歌,为生命赢得应有的尊重开辟道路。
综上所述,司马迁所谈的生命价值意义已具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内容了。他平静地评价各类生命主体,他的生命意识往往通过笔下士人的道义感和使命感来体现。因此,刺客是士,专诸被公子光“善客待之”;豫让被襄子赞为“义人”;“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聂政自己也说“政将为知己用”,俨然以士自视,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游侠是士,“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其非人之所谓贤豪者邪?”记佞幸者他可以找出其所长,传酷吏也是“其廉者足以为代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对自己心目中英雄项羽赞誉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师古”“欲以武力征伐天下”的错误。
再如帝系中在《秦始皇本纪》之前列一个《秦本纪》,司马贞认为秦虽然是秦始皇的祖先,但只是西戎一个诸侯国,不能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应降为世家。他还认为项羽虽然争雄一朝,但没有真正登上帝位,也不可称本纪,陈涉则应降至列传中。张大可先生在《〈史记〉文献研究》中分析司马迁立《秦本纪》是为了表明秦始皇统一六国有其祖先的功劳。而项羽为本纪、陈涉为世家是为了标明灭秦之功在陈、项而不在刘,只是司马贞不明司马迁的本意而已。
我赞同后者的看法,而且我以为这更是因为司马迁评价人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温柔敦厚”的儒教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而是这时他已经意识到生命其实是一个坐标轴中的无数个点,生命的价值必须定位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结处。他已经发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光有同时代人的评价是不够的,也是不全面的,生命意义只有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久远的历史时段中才能更清晰地见出。所以司马迁越是了解生命,就越是尊重每个生命的个体选择;越是珍视生命,也就越能胸襟开阔,容纳百川。这便是生命意识的更高境界。
总之,司马迁的生命意识在自我身上是朝气勃发渴望释放,遭遇挫折后由怨愤转为沉静地思考自己和他人,最终在对众多生命的探寻中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从而融会各家观点之长,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多元的思维去认识人、评价人,进入了一种理性的哲学的思考。这个思考是痛苦的,但是也是必须的。因为人类向前发展的同时,对自身的探究也就必然更加深入。后人也正是在《史记》这个庞大的人文世界中,在司马迁强烈的生命意识的感染下继续生命的体验和探索。
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