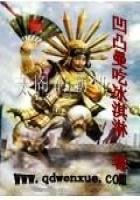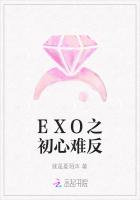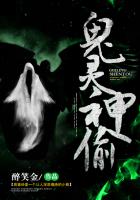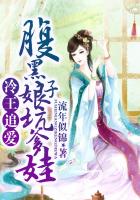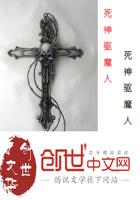两广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即密派解方去广西联络。临行前,交代他:“我派你代表我速去广西向李德邻(李宗仁)等表示,我非常支持两广的抗日主张,征求他们希望东北军怎么配合的意见。另外,细致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真诚抗日?有什么具体办法和主张?”(19)解方到达广西时,李宗仁还在广州,只见到白崇禧。待李宗仁回到广西,两广局势突变,陈济棠已经下野,张学良在军事上援助两广已经不可能。尽管如此,李宗仁对张学良的支持还是深表谢意,并希望张在西北能够有所作为。解方离开广西回西安向张学良复命时,李、白给张学良写了亲笔信,并派刘仲容、李宝莲二人为其代表与解一道驻于西安,与张学良具体会商双方合作办法。
8月末,张学良派其秘书栗又文赴新疆联络盛世才。盛世才是辽宁省开原人,1917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后转入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在第8混成旅旅长郭松龄部下任职,深得张作霖、郭松龄赏识。1923年由东北地方当局送往日本联军大学中国学生队继续深造,因为参加郭松龄的倒张活动,兵败后逃回日本被取消公费资格,在孙传芳、冯玉祥的资助下才得以完成学业。1927年回国参加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科长。1930年来到新疆,1933年任东路军“剿匪”总指挥。这是盛世才在新疆辉煌时期的开始,但很快蒋介石欲改变新疆半独立状态的设想,使盛的仕途遇到阻力。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第118次会议正式通过对盛世才等的任命,但这个任命同时包含着对盛的牵制,因为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三人一同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刘兼省府主席,盛兼边防督办。张兼伊犁驻屯及陆军新编第8师师长。为摆脱此种局面,盛派他的外交署长陈德立向苏联驻迪化领事示好,表示愿意与苏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答应他的要求,出兵塔城,并换着中国军服,向张培元控制的地区发动猛攻,至1934年1月,张培元见所部大败,即留下遗书,请盛世才照顾他的家小,而后开枪自杀。自此,盛世才开始了在新疆的正式统治。
苏联支持盛世才是有其自身利益需要的。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与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6,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新疆省与苏联中亚地区有相同的民族和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处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苏联需要近邻中国新疆与其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预防其他大国和一些政治势力插足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新疆危害苏联利益。
此时,中共中央对盛世才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政策。1936年6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派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与盛世才联系,后邓又经新疆乌鲁木齐到莫斯科,使中共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其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与滕代远也一起从莫斯科进人新疆,接援西路军。陈云对苏联、中共与盛世才发展关系作了如下评述。他说:
盛世才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20)在苏联帮助下执政新疆的盛世才,积极奉行亲苏政策。1936年4月,在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盛正式颁布实施“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编写了《六大政策教程》一书,进行公开宣传。这一政策的推行,为苏联与盛世才建立联盟,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张学良亦希望通过盛世才沟通他与苏联的联系。于是,他派遣栗又文与东北军105师1旅旅长董彦平一起来到新疆。让董参与这一使命,是应盛世才的要求作出的。董彦平是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谈话方便一些。此时,中共派来协助张杨部署军事的叶剑英已到西安。栗又文等到迪化后,首先见到了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安德烈夫要求栗又文提供一个关于东北军情况和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情况的书面报告,之后开始与盛世才会谈。栗又文等在那份报告中,除了介绍东北军的基本情况外,对着眼抗日的军事准备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并特别提出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后来,安德烈夫将这个报告递交给了斯大林,并答复栗又文:“对于你们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平凉(甘肃省)建一个兵工厂”。(21)在张学良联络新疆之时,杨虎城亦开始做华北各地实力派的工作。
杨虎城委派蒲子政先后抵达太原、北平和山东,联络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共同抗日。阎锡山对杨虎城提出的联合抗日和逼蒋抗日的主张,没有给予肯定的表态,只是说:虎城主张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须从长计议。
宋哲元表示:29军位于抗日最前线,日前抱定的态度是,有限度地避免同日本人冲突,但是他决不当汉奸。日本逼他无路可走时,他一定抗日。
韩复榘对反蒋比对抗日更感兴趣。他说:西北主张联合抗日,他赞成;但山东处境特殊,如公开抗日,将首先挨打。因此他不主张公开说抗日,但可讲抵御外侮。
杨虎城还派傅剑目去四川做了刘湘的工作。刘湘亦表示,赞成抗日,西北如有行动,他愿附翼其尾,并派他的参谋黄慕松回访了杨虎城。
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变发生后,虽然为“讨伐”还是“和解”吵得不可开交,但丝毫没有放松分化张杨联盟和做安抚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孔祥熙13日早晨回到南京后,即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通电各省、市,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抗敌御寇,素有决心”,要求各地“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共策国家安全”。同一天,孔祥熙又给那些与蒋矛盾较大或与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单独发了电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至于太原阎氏,老成望重,与张有世交,张亟望其助力,故以调处之任托之”。孔祥熙了解到四川的刘湘有出兵援助西安的意图后,即令顾祝同去信制止。在同京的3天时间内,孔祥熙先后向各地发电20多份。
为分化张、杨联盟,孔祥熙电请河南省主席商震,去策动与其有儿女亲家关系的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叛变。他给商震的电文说:“查汉卿之警备旅长刘多荃。与兄关系最深,务请速派妥员,前往没法婉劝汉卿,使之觉悟,泯大难于俄顷。”商震接电后即派刘多荃之弟刘多麟实施策反,但刘多荃不为所动。孔祥熙还令甘肃省财政厅厅长陈端去拉拢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也没得逞。
驻防洛阳的46军军长樊崧甫,其弟樊光在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缘此与孔结识。孔通过樊收买了杨虎城部第7军军长兼42师师长冯钦哉。因为冯钦哉与孔祥熙同是山西老乡,冯又是孔的学生,策反活动很快得手。冯钦哉叛杨附蒋,对时局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潼关的放弃,不仅使张杨的东线始终处于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之中,而且导致了人心浮动、军心不稳和外界对张杨的实力发生动摇。原来准备赞助张、杨的,有的义转而拥护蒋介石。
冯公开背叛杨虎城,声明站在“中央”一边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任命冯钦哉为“渭北剿匪司令”并委托肩负“慰宣”使命的于右任送去100万元巨款资助冯部,表示以后冯部军饷由南京方面解决。樊崧甫由于策动冯钦哉叛杨有功,也被提升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前敌副总指挥,并获得孔祥熙亲自拨批的经费1万元,答应“嗣后当每月酌予补助”。
孔祥熙亲自致电冯钦哉,通报南京对他的奖赏。电文说:“中央已任命兄为渭北剿匪司令,并以贵军给养或有问题,已托于院长将月饷携致。嗣后公私方面如有需协助之处,即盼电知。”孔在电报中同时提出,希望冯策动杨虎城叛张释蒋。19日,冯钦哉复电孔祥熙,声称他从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许海仙口中得知,此次事变,除杨虎城一人外,17路军各长官事前概未与闻。这封电报增强了孔对杨虎城的幻想。他当天致电冯钦哉,说:“吾兄与虎城相知最深,仍希就近设法,俾获介公一同脱险为祷!”“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你“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其最大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功勋”。(22)冯钦哉按照孔的指示,献计要派陈子坚到西安,去间离张、杨的关系,设法要杨虎城离开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三原再转大荔。又派刘峙的代表携100万元巨款,密赴西安从事策反活动。结果,这两个阴谋都未发生作用。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加入到说服各地大员的行列。按理说,他与张、杨在抗日上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因为冯有几次举兵反蒋的历史,被蒋排挤,与蒋有着很深私怨,他应该同情张的扣蒋举动。冯玉祥对张学良的支持只发生于一瞬间,听到发生事变的消息时,他称赞道:“汉卿这小子真行,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之后,便开始公开谴责张、杨。他知道,张、杨必定要借重华北的地方实力派,逼使南京认可“八项主张”,就派人星夜赶赴华北,去见宋哲元和韩复榘,利用他的北方实力派名义领袖的地位,训示二人要小心谨慎,沉机观变,不可受别人所惑,要采取一致行动,营救蒋介石。还给二人出主意:如给张学良去电,“均称拥护中央到底。”(23)国民党中央在拉拢地方实力派方面,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是张、杨无法相比的。这种不利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当局不断’加大对各地方大员软硬兼施的力度,以及其后宋氏姐妹赴西安和谈。使各地方实力派的观望态度进一步拉升事变后完全支持张、杨行动的,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的李济深。桂系与蒋介石长期有矛盾,并多次发生战争。在西安事变前几个月,桂系还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那时,张学良的代表解方不仅带去了张对两广行动的支持,而且授权与桂系商讨西北如何配合行动。西安事变发生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仍驻于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发给李、白的密电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引者)乘机来此,共商一切。”
李、白对于张、杨扣留蒋介石的做法虽然“不表苟同”,但他们表示,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显然,广西的表示与张、杨的救国通电的主张是一致的。在李、白得知西安发生的事变后,南京方面也致电广西要求他们表态,支持中央。14日,李、白在给孔祥熙的复电中,未对张杨进行任何谴责,更未使用“叛逆”的字眼,只是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引起的“越轨行为”。
在何应钦掀起“讨逆”风浪时,蛰居广西家乡的李济深,于15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明确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这实际上是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积极响应,是对西安事变的明确支持。18日,李济深再次发表通电,公开支持张、杨。通电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爆发,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因为张学良屡谏不纳,才迫以兵谏,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
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的当晚,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等人又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通电的要点是:(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这个通电的主旨是,反对南京派兵讨伐西安,主张“政治解决”;解决的办法,不是南京要求的无条件释蒋,而是要建立在“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的政治解决基础之上。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是地方实力派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统治的四川,物产富饶,号称天府之国;毗邻陕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他掌握的几十万川军,以骁勇善战而闻名海内。正是这一因素,使蒋介石惧于他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因而在1935年初,以追剿长征红军为由派“中央军”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也正是蒋介石对刘的不信任情绪,使蒋、刘矛盾由此激化。
刘湘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正在这时,杨虎城的使者找到刘湘,征询对于抗日的看法。刘湘自然明白西安的用意,他认为,如果能够与西安实现某种联合,将有利于他在四川的统治,所以他十分痛快地答应甘做西北的“后盾”。有了这句承诺,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接连再次致电刘湘,争取刘的支持,并还派代表到成都具体商议。
刘湘对张、杨兵谏扣蒋特别高兴,他感到这是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良机,于是,便向张、杨的代表宋醒癡明确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作后盾。”对外他公开表示反对讨伐西安。他说:“西安事变,已使我御侮救国工作,蒙莫大之打击,若再继以大规模之内战,不啻蹈西班牙之覆辙,我国家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悲境。各方所争,既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心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在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抵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将其所辖的45军军长邓锡侯、47军军长李家钰、21军军长唐式遵、23军军长潘文华、44军军长王绪赞等召到成都举行军事会议,名为研究防备,实则准备援助张、杨。
刘湘所处的四川具有与西安遥相呼应的重要战略位置,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他的言行相当关注。为确实了解四川的军事动向,孔祥熙委派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带去顾祝同的亲笔信返川安抚刘湘,向他传达南京要他“顾全大局,不可有任何轻举妄动”的旨意。为稳住刘湘,南京国民政府还于12月17日公开宣布刘湘任川康绥靖主任的任命。
处在两难之中的刘湘,18日被迫公开表态。他采取表面上敷衍南京,实际上同情西安的态度。在发表的通电中刘湘表示:“拥护中央,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主张“以政治方法翊赞中枢,稳定全局,促成和平解决之办法,以保全救国御侮之实力,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