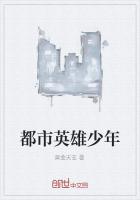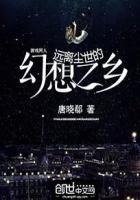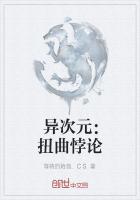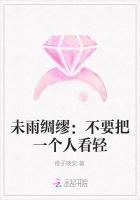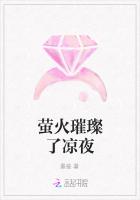19日,刘航琛向南京复命,称他“已将敬之(何应钦)、庸之(孔祥熙)、墨三(顾祝同)诸公所述”报告给刘湘,“甫公(刘湘)已发出通电一件,说明巩固中枢,抗战救国,弭息内争四项。又发出致西安营救委座通电一通”;至于南京风闻事变后刘湘与张学良曾有电报往来的说法,刘航琛在电报中予以否认。说“归查此间并未得(张学良的)片纸只字”。
同日,刘湘也致电何应钦、孔祥熙和顾祝同,说他遵照南京旨意,已给张学良发去电报,向张提出了3个问题:“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务请立即恢复介公自由”;“如兄在政治上有所主张,弟当居间进言,以求解决”。
在稳住南京的同时,刘湘仍暗自进行筹划,部署援助西安、将“中央军”挤出四川的准备。就在刘湘宴请张、杨的代表之时,张学良释蒋的消息传到成都,刘湘“闻报大怒,当宋氏(宋醒瘢)之面,拍案大骂张副司令不止。”可见,刘湘是真心支持张学良扣蒋,并反对无条件释蒋的。
控制绥远省的傅作义,与张学良的关系颇深。傅作义结识张学良始于1927年,当时晋军与奉军交战,傅所守城郭被张学良围攻,但张对傅作义这一阎系守城大将惺惺相惜以礼相待,从此结下友谊。张学良主持北方军政时又举荐傅作义当上了第35军军长和绥远省主席之职。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道义上给傅以支持,还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兵援绥。虽然蒋介石没有批准张的请求,但却命张从东北军中抽调骑兵第7师,加入傅作义的作战序列。扣蒋之后,蒋介石终于不能阻止张学良的行动了,张、杨立即发出通电,宣布组建抗日援绥军,任命孙蔚如为第1军团军团长,王以哲为第1军团副军团长,郭希鹏为第1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1军团炮兵指挥官;任命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张学良这些举动,使傅作义深受感动。
15日,张、杨派出的代表苗滓然到达绥远。傅作义了解西安“兵谏”的宗旨和经过之后,当即表示支持张、杨的义举。他向苗浡然表态:
一、联合抗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二、绥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脱离西安被动的困境。
三、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与张副司令同患难。(24)傅作义说到做到,他在动身前,先到太原和集宁,向阎锡山、汤恩伯说明了去西安的打算,阎、汤得知傅的此行意在张、杨早日放蒋,亦没有阻拦。傅亦致电孔祥熙,提出他要去西安救蒋,希望南京予以解决交通工具。孔祥熙听后大喜,即让宋子文派欧亚航空公司飞机一架到绥候用。
傅作义于22日乘机离开绥远,拟经太原去西安。飞行途中,飞机在大雾中迷航,只得迫降于河北易县。傅又改乘汽车到北平,再乘火车去太原转西安。几经周转,刚刚到达太原,即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
傅作义虽没能对张、杨提供实质的帮助,但他完全支持张、杨的态度,使张、杨颇感慰藉。
与傅作义的情况几近相似,同样欠着张学良的提携之恩和长官之谊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冀察绥绥靖主任的宋哲元,在压力下却没能站在张学良一边。
宋哲元与张学良有着较深的历史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曾接受张学良的改编,被张荐任察哈尔省主席,受当时担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张学良的节制。张学良自认为,中原大战之后,他统辖北方8年多,宋哲元和韩复榘当年都受他节制,自己走后,整个“地盘”都交给了他们,而自己主政华北时,待他们确也不薄,如今北方处在抗日前线,发动西安事变目的就是打击他们面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大的目标是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受益的是北方各位将领,因之得到宋、韩的支持顺理成章。
事变当日,张学良就致电宋哲元,希望他“接电后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前来,共商国是。”这封电报12日夜即送到宋哲元手中。但比之南京的步伐还是晚了几个小时。何应钦、孔祥熙不仅分别致电宋、韩,还委托与之关系密切的戈定远、李世军、李毓万前往笼络;冯玉祥也派出他的高级幕僚长携信北上,以叮嘱宋、韩“小心说话为主”,对事变宜持谨慎态度。
面对大变,宋哲元不知如何才好,想了一夜,还是采纳了老领导冯玉祥的意见。13日,他召集其高级将领和幕僚开会研究对策。会上,各种意见都有。宋认为,张学良发动“兵谏”有一定背景,情况相当复杂。他主张对西安事变要想一想,看一看,头脑要冷静,不宜轻易表态。他决定暂不派代表赴陕,可给张学良先发个电报,盼其“以国事为重,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一切均可从长计议”。等把各方面情况大体弄清楚之后再考虑走第二步。
为弄清情况,宋哲元派戈定远前往南京,一方面表示对南京的忠诚,同时探听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安的态度,以便决定自己的方针。南京此时一边倒的讨伐之声对宋哲元产生了影响。从后来的事态看,在张学良与南京的天平上,宋哲元倾向于南京,这不仅是因为冯玉祥是他的老上级,他的仕途命运全系于南京,还由于他的面前摆着大批日军,拥护西安将招之日军的大举进犯。宋哲元于14日发表声明,表示要全力维持冀察的和平秩序,继续执行防共政策,继续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命令。16日,又发布紧急治安令:严禁集会、结社、游行;严禁散发传单,各报馆不得发行号外。这是他惧于日本借此向华北再度进攻的思想反应。
宋哲元最终没有与张、杨走到一起,这使张学良感到心寒,但宋哲元的做法却得到南京特别是蒋介石的嘉许。七七事变后,29军居于华北抗日第一线,在部队南撤途中,宋哲元因病离军,各地对宋颇有指责,此时蒋介石出来为他说话:“这次事变的爆发以及宋主任离开北平,不是宋主任一个人的责任,首先应由中央负责。”“一年多来,宋主任在冀察应付这个局面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们为了抗战,就必须有一个从容的时间来准备,要取得这个时间,就必须设法缓延日本对我国的军事进攻,宋主任对日本的应付,是起了这个作用的。”(25)一向计于诿过的蒋介石,能够站出来替宋哲元承担责任,这是少有的现象,也是他感恩于宋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倒向西安方面的回报。
事变期间与宋哲元联络频繁的山东韩复榘,采取了表面不偏不倚,实则支持张、杨的做法。韩复榘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即于12月13日致电何应钦,认为“事已至此,惟有设法营救委座为第一要著。”14日,又致电孔祥熙,表示“惟盼钧座与中央诸公,从速远筹决策,俾得其早脱险地”。韩复榘还派其参议员靳文溪赴河南开封,与刘峙、商震商讨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又派部队参加刘峙的东路集团军。
但是,韩复榘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内心他是站在张学良一边,期望扳倒蒋介石,以改变他的处境。韩复榘对他的心腹说:“张汉卿这一手是英明果断的壮举,大快人心。”他认为,张、杨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促成国内和平统一,否则将造成更大的内乱,届时日本将长驱直入,若河北不保,山东便成为抗战前线。因此,争取一个好的结局,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蒋介石,只要蒋介石活着,南京方面必定投鼠忌器,不敢真打。于是,他决定派刘熙众为代表去西安向张学良表明态度,即:
(一)完全赞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二)拥张为领袖,组织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执行抗日救国大计;(三)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并予以优待;
(四)准备以响应讨伐为名,派部队沿陇海线西进,准备到达洛阳以西,即与东北军相呼应,夹击西进中央军,将中央军消灭在陕县、灵宝、卢氏、阙乡一带。(26)与此同时,韩复榘于12月21日以“马电”密电张学良,称赞张、杨的主张和行动是英明的壮举,并说明他的军队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不要发生误会。结果,这个密电被南京方面破译,公开于世,不仅使援助张、杨行动的军事计划无法实现,而且引来各方面的反对和劝告。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以韩复榘兵败为由将他处决,正是由于这则被破译的密电。
韩复榘派往西安的代表刘熙众,由于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济南降落时,螺旋桨被折断,不能飞行,刘只得乘火车经洛阳赴西安。而不巧的是,在洛阳换车时不仅没被送往西安,而且被送到了太原,这使韩与张、杨的联络中途中断。
在压力之下,韩复榘于12月22日约宋哲元、邓哲熙、秦德纯等在德州会面,并于次日联名发表通电,指出:
各地方长官纵因事实上特殊之困难,感觉有所不同,然无论如何,应论列意见。为中央统筹公决。万不容在困难严重之际,再有自伐自杀之行动。不此之图,竞成出轨之事,国人在忧慌震骇之余,皆不能考其主张之奚若,则其结果,非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不止。所谓亲痛仇快者是也。目前急务,约有三大原则:
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
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
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
以上三义,夙夜彷徨,窃维处穷处变之道,迥与处经处设趋极端断然之途径,上列三义,恐难兼顾,或演至兵连祸结,不堪收拾之时!虽有任何巨大之代价,不能弥补挽救此种空前之损失。
敬祈者公本饮冰茹孽之胸怀,执动心忍性之态度,审外来之危机,测来日之转捩,庶我领袖为国家之预定步骤,依然能在狂风暴雨之中,安全到达,则我国家人民与领袖之光荣,纵蒙一时阴霾,更不能有毫发之伤害。倘蒙俯察,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所有旋乾转坤之功,胥拜诸公讦谟之赐,至于具体有效办法,悉待诸公迅速沈洽议,一致进行,不胜盼幸屏营之至。(27)这一漾电,本是韩复榘为弥补“韩张密电”对南京的刺激而采取的一个行动,但其高揭反对内战、和平解决事变的大旗,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反响,使得南京当局高度关注。
23日,韩复榘通电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派人前往河北、山东进行解释,企图说服韩、宋收回漾电。当天,孔祥熙又派李世军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请秦对宋哲元进行说服,并透露了南京对西安采取的策略。第二天,李世军又奉孔祥熙之命致电秦德纯,明确指出:孔甚盼韩复榘、宋哲元“能立即郑重发表谈话,说明漾电系完全本中央应付事变之既定政策,阐明反共救国以及迅速恢复介公安全之至意,以故目前急要之事,为介公早日回京主持大计,至于主张召集在职、在野名流,共议大计,系在介公回京后应有此集思广益之举。”电文的最后说,宋、韩“如能发表如此谈话,一则抑制张、杨气焰,一则免为日本借口,发生种种外交之压迫”。
孔祥熙本人于24日亲自致电韩复榘、宋哲元,就他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作出答复。
对于如何维持国家命脉、避免人民涂炭问题,孔祥熙回答:“现欲维持国家命脉,避免人民涂炭,非健强政府之力量不可;健强政府之力量,非先整饬国家的纲纪不可;整饬国家之纲纪,非先恢复领袖之自由不可。”
关于提议召开在职、在野会议的问题,孔祥熙回答:在蒋未获释的情况下,“所谓召集会议一节,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他接着说:“兄等现殷殷以领袖安全为念,即祈迅为共同设法,劝促汉卿,早将介公护送回京,对于党国大计,或可以从长计议。”
孔祥熙明白,韩、宋之所以提出三个问题,主要是他们反对南京对西安的武力讨伐方针。所以在给宋、韩的电报中,专门解释了讨伐令的问题。他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协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28)南京当局对韩、宋的一纸通电如此重视,足见他们是十分担心韩复榘和宋哲元投向张、杨一边的。
盛世才一开始也是支持张、杨的。这是因为他一贯反蒋,从1934年起,南京派来的官吏均被他逐出新疆,学校中的党义课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停止发售。1936年7月19日,盛世才还在苏联的作用下发出救国通电,提出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不点名地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派使者在与盛联络的同时,亦与苏联发生联系,固此,盛认为事变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因而较早地释放出支持信息。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新疆后,《新疆日报》立即发了号外,报馆连夜赶写拥护张学良扣蒋抗日的社论。13日,盛世才召集省属各机关正、副长官及少校以上军官进行“观点测验”。盛当场出题:
1.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是否正确?
2.是否以下犯上?
3.张举行兵谏是不是呼应本人的7月救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