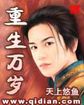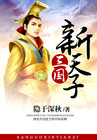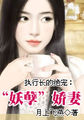其三,苏联的态度对中共决策产生了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12月16日正式收到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电的,这一由共产国际书记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回电,说:
现回答你们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有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者。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必须考虑现实,中国共产党应根据以下原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使一切抗日运动的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同红军合作。(4)与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合作。(22)如果不出意外,这封电报将会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时制定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以直接帮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电台密码出现差错,译电员无法将电报内容译出。中共中央于18日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电文出现乱码,“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到20日,中共中央才正式收到共产国际所发的电文,而在此之前的12月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尽管共产国际16日的指示电对中共中央决策西安事变的方针没有直接的帮助作用,但此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的反应,已经对中共产生了影响。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的社论说:在中国陕西发生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扣蒋事件,是一种“叛变”行为,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的行为,它“名义上举起抗日的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发表的评论,则更无根据地将西安事变与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联系起来。竟说:
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此类要求,仅发动之烟幕,实际上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及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自蒋氏执政以来,中国已逐渐集中力量,显足表示其领导国防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国民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夫反日人民阵线,乃系于南京合作之阵线。毛泽东与其发表密勒周报之文字中已直言其事。张学良之举动,其最近影响,即新的内战之爆发,亦即日本所急欲利用机会以作更深侵略之举者。(23)苏联的媒体所发出的声音,虽然也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但它的出发点与事件的本身,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却是南辕北辙的。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而苏联却为着自己东方战线的安全。因而,它对西安事变的判断一开始就陷入了片面。事过多年,谈及此事,周恩来仍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他指出:“两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24)苏联所发出的声音,除了向中国南京当局表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之外,就是向中国共产党传递它的声音,以影响中共中央对待事件的看法及其立场。尔后,苏联政府在与南京方面就此问题进行会谈就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中国共产党了解我们的立场。
斯诺在《漫评》中曾这样写道:
斯大林立刻向保安的中共领导人发布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释放蒋介石,否则将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关系。
斯大林的电报发给了上海的孙中山夫人,然后由她转交给毛泽东。斯大林宣布,除非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蒋介石获释,否则,莫斯科将公开把他们斥为“土匪”并与他们断绝关系。(25)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电报的真实性。因为,已经公布的资料表明,苏联及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问题给中共最早的指示是12月16日共产国际的回电。即便如此,毛泽东及党中央仍然能够通过广播、电台和其他足够的渠道及时了解苏联对于事变的反应。事实上,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公开表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共的决策。
苏联的反应不仅影响了中共,也影响了张学良。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之前,张学良已从广播电台上听到苏联反对事变的声音,对此,他很不理解。13日,苏联塔斯社广播《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拿着新闻记录稿,正碰上宋黎站在楼下,就说道:“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还对刘鼎说:“为什么苏联认为事变是受日本的挑动,持反对意见?”17日,张学良再电中共中央,询问:“国际对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祈告。”毛泽东当天复电,说:“我们对远方(即共产国际和苏联)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群众运动情况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群众联系的消息,当寄以同情。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中共代表团达到西安以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张学良又提苏联态度的事。《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掐述了那次会谈的详情:
宴会后,周恩来趁与张学良小憩之间,要罗瑞卿即刻去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17路军的情况,为第二天与杨虎城会谈做准备。然后他便与张学良一起走进小客厅,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张学良向周恩来叙述了蒋介石被扣后的情况、南京的动态及各方面的反应,继而说道:“蒋介石独断专行,一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力逼我和杨将军配合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和杨将军怎么劝说都不顶用,苦谏不行,进行哭谏,委员长反而声言要把我们的队伍调离西北,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万不得已,只好实行‘兵谏’。倘若不捉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就不能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谈。”说到这里,张学良面起忧色,叹息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张《消息报》拍在桌子上,连连摇头说道:“可苏联的态度,令人失望,真可谓一派胡言。”
周恩来盯了一眼《消息报》,又怔怔地注视着张学良。
张学良语调很沉重地说:“本来,我一直是想取得与苏联的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施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愤然拍了一眼前的《消息报》说道:“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要求的抗日的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据,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苏联的态度,实非我始料所及。”
苏联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周恩来当时并不清楚,但从《消息报》和外电上也有所略知,他感到苏联方面的指责,对张、杨两将军的义举中伤太重。面对张学良,他既是同情,又有些无奈,呷了口茶,才慢慢地回答说:
“对苏联的看法,请张将军不必多有顾虑。他们不大了解我国的国情,看问题难免有偏颇之处。然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主张事变和平解决。……我党将会努力向苏联方面进行解释,相信他们只要了解事实真相,是会改变对张将军和西安事变的态度的。”
张学良对苏联的反应如此在意,可见苏联的态度对他产生的影响。
其四,蒋介石态度开始向着接受和平调解的方向转变。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取决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张、杨是否愿意放蒋;二是蒋介石是否接受张、杨的主张,这是“释蒋”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在被扣之初的两三天内,态度是顽固的。
12日上午,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走进新城大楼蒋的临时卧室,先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委员长受惊了!”连说了两遍,蒋都不理会。张学良接着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变,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为了委员长,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以颤抖的声音说:“你既为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然后再谈,否则法币、公债都完了。经济崩溃了,抗日也无从谈起。”
张回答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我们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仍执迷不悟,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一听,神色骤变,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以为全国民众的舆论会赞同你们的叛乱行动吗?恐怕即使你们平素所说的‘人民阵线’里的人,也不至于做出像你们今天这样如此荒谬和狂妄的举动。你自称为革命,叛逆也可以称革命吗?陈炯明何尝不自称革命,天下人有谁能相信他是革命呢?你的部下就在这个房间的周围,你竟如此犯上作乱,你又怎样率领你的部下做人呢?”说完闭眼坐在椅子上,额暴青筋,全身发抖。张学良神色沮丧,只好退出。
12日这天,张学良去看蒋介石三次,但蒋根本不让张说话,有一次,还大声斥责张学良说:“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是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他甚至用手捂住耳朵,连说:“我不同你讲话,我不同你讲话。”张只好再次离开蒋的房间。
张学良为打破僵局,同日上午,让邵力子单独见蒋。邵劝蒋说: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件事,请委员长仔细考虑。当前,日军实际已控制了华北,正向绥远进逼,已激起了全国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邵力子还说:张、杨的做法虽不免鲁莽,但其用心良好,希望委员长从民族国家的全局着想,接受张、杨的“八项主张”。
蒋介石表示,决心牺牲,决不受任何要挟,或者立即送回洛阳,或者立即枪毙,皆由张学良选择。邵力子听出,蒋以死相威胁,意在摸清张学良的意图,就宽慰他说:送回暂无可能,枪杀也决不敢。邵还试探蒋介石是否会以辞职而保全性命,俟国家需要再行复出。蒋介石回答:“决不能在武力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邵的这次谈话也无成果。
蒋介石还在这天拟好了两份遗嘱,给宋美龄的是:“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给蒋经国、蒋纬国的是:“余只承认宋美龄女士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之下亦瞑目矣。”(26)并把这两份遗嘱交于张、杨,让他们代为拍发。
蒋介石真的准备以身殉国吗?此时的蒋介石对生死的判断极其矛盾。一方面,蒋介石不会想不到,自1927年以来,他屠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无数,此次事变,即使共产党没有亲自参与,也与受其影响不无关系,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此次事变,是为抗日“剿共”而起,自己西安之行,不仅有威逼张、杨部队“剿共”之意,更有撤换张、杨的把柄,张、杨能轻易放他吗?这使蒋介石深深感到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从张、杨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邵力子谈话所露的口风分析,不像要杀他的样子。
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要维护他作为领袖的尊严。有了领袖的尊严,如果死,那将留下英雄的形象;如果生,那将增加后面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在被扣的初期,蒋介石表现出了极其顽固、死硬的态度。
可13日发生的一件事,使蒋介石企图维护的那点自尊、那点英雄形象,大大缩水。起因是12日夜,西安绥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大意是说:委座蒙难,关系国家存亡,希望李能运筹帷幄,救委座出险,以建立这千载不朽之奇功,等等。恰巧,毛泽东、周恩来这晚也有一电发给张学良,电报富有预见地提出:
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万须将蒋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严防蒋收买属员。(27)围绕同一件事出现的一信一电,引起了张学良注意。他与杨虎城商定,决定把蒋介石转移到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由东北军卫队营看管,以防意外。
13日上午,张学良找到邵力子,请他出面劝说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但蒋介石并不买张学良的账,他坚拒道:“我决不迁往他处,如张不能送我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地,这是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我是行政院长,所以,决不能离开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张。”邵力子看清了蒋氏这是怕死,就宽慰蒋说:张学良请你移居高公馆并无恶意,此时“勿再峻拒张学良进言”。这句话对蒋产生了作用,蒋随即问邵,能否搬来同住?
还没等蒋介石就改换住处问题最后说定,当日深夜11时,刘多荃师长奉张之命偕宋文梅到新城大楼劝蒋搬迁。蒋误以为是要枪毙他,因为他的南京部下处决政治犯多在夜深人静之时,而且他看见宋文梅腰间挂着手枪。蒋介石立刻萎缩到床的里面,重复上午给邵力子说过的话:“我兼行政院长,西安绥署直属行政院,是公家地方,要死也死在公家地方,哪里也不去。”之后,蒋用被子蒙住头,任凭谁如何劝说坚决赖住不走。
谁也没有想到,蒋氏顽固的态度,事过一天即很快改变。能够使他改变的人,就是宋美龄派来的和平使者端纳。
端纳是14日中午到达西安的。在西安西郊机场,张学良派来了他的私人“洋管家”、也是端纳的老相识、美国人米·埃尔德前来迎接。端纳看到蒋介石的座机安然无恙地停放在机场。又听米·埃尔德介绍西安事变的粗略经过和蒋介石的近况,初步证实“蒋介石没有死”的此前判断。
端纳还没有从思绪中走出来,汽车已开到张公馆。端纳在客厅落座之后,张学良便出来接见了他。见到昔日的顾问,张学良显得非常高兴,一番寒暄之后,端纳拿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学良。张学良阅后,即让秘书抄写了一份,然后将原件还给端纳。
会谈一开始,负有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使命的宋美龄的亲信黄仁霖上校,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他告诉张学良,蒋夫人派他来,就是要看看委员长的健康状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的翻译。他要求立即见蒋。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但现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