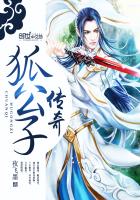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杨虎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刚刚同意放蒋,张学良又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这个举动有点像旧戏《连环套》中窦尔敦摆队释(黄)天霸的情节,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怎样也无法联系在一起。何况,张学良面对的是毫无信义可言的蒋介石,送蒋之举确乎冒险。
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表示很不理解,他在事后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还一定要陪蒋走,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
中共在西安的代表也不赞成张学良的这个做法。周恩来认为张学良此举过于冲动,他叹息地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博古也认为,张学良送蒋这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驱使下做出的一种行为。
张学良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如果蒋介石不讲信义此举的后果吗?
张学良当然不会不考虑,但是,为了实现抗日初衷,明知艰险,却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对张学良来说送蒋并非仓促草率之举,而是考虑很久。在扣蒋之后,张学良就考虑送蒋问题。
12日上午,蒋介石被扣后被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不愿见蒋,张学良即对杨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2)当三方面商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想法更具体了。19日,张学良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文中说:“当他(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3)谈判期间,在东北军的一个干部会上,张学良向周恩来透露,他准备亲自送蒋回南京,周说:
我没有那个心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送蒋大可不必。
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
蒋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杀就是一个证明。(4)张学良听后未做任何表示。
周恩来不赞成送蒋,主要是从张学良的安全着想的,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张送蒋一旦被扣,对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对东北军、17路军这两支抗日军队,特别是约束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有承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张学良看来,周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他的送蒋之举很高明。
一是有利于敦促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使蒋不至反悔。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允诺了他们的条件,但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被迫的;虽然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履行自己的诺言,但那都是纸上的东西,即使签了字,也没有多大价值,他不想履行,“回去以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执行了,兵暂时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我们又奈何于他?”(5)因此,张学良认为,亲自送他回南京,使蒋介石看到,张是守信的,履行了此前讲过的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的诺言,以此敦促蒋介石也要信守对张的诺言。张学良说:“我亲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二是能给蒋介石撑足面子,帮助其恢复领袖尊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独裁领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反对者不乏其人,但没有能够成事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却是个例外,这就使得独裁领袖的形象黯然失色。蒋介石被扣之后考虑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
被扣之初,他不与张对话,不改顽固立场,并给妻儿写下遗嘱,做出“宁可玉碎”的姿态,都是基于维护他的所谓领袖形象出发的。
端纳到西安后,随行的黄仁霖为了完成孔祥熙要他“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的使命,与张学良反复磋商达成协议:黄可以见蒋,但只准说些问安和身体状况如何之类的话,否则黄便不能离开西安。蒋、黄都答应了张开出的条件。但张学良领着黄进入蒋的卧室后,蒋却违背约定。他倒是与黄没有说几句话,却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要黄带回南京,信中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即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6)写完后蒋介石当着众人的面连续念了3遍,意在使黄记在脑子里,即使此信被张、杨扣留,凭记忆回去后也能向宋口述。尽管这个小动作被张学良识破,黄仁霖见蒋后被留在西安,直到蒋获释后黄才获准离陕,但蒋介石此举做给外人看的还是维护其“领袖”的形象。
蒋介石被扣期间哭过几次,其中一次大哭就是为了他的领袖形象。那是在谈判达成后宋氏兄妹为蒋早日离陕绞尽脑汁之时,蒋介石说: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说罢,大哭。这次大哭是不是有意做给张学良看的另当别论,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自己的领袖尊严是很看重的。
张学良看透了蒋的这些心思,所以,他宁愿自己冒险,也要送蒋回去,成全蒋的虚荣。12月24日,张对东北军将领透露送蒋的决定后,将领们表示疑虑,就问他:“副司令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郑重地回答说:
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7)三是可以挫败亲日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出了武力讨伐张、杨的决定,力图挑起新的内战,从中渔利。几个回合下来,何发现事态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发展。在蒋被扣于西安、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位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3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何应钦虽有指挥军队的实权,却不可能像蒋介石那样可以专权,因为他的权力仅在军事委员会内部,党政部门他无法问津,即便对于军事问题,他也只是7常委之一,许多重大事情必须由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体作出决定,而不是何应钦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这个集体的决定,何应钦寸步难行。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明确规定:“自本日起,一切宣传均应绝对遵照本决议,不得稍有违背,其个人之言论与本案决议不合者,一概不得发表”。“以后商谈办法,应绝对遵照本案决议”。这样的格局已经十分显然,即使蒋介石死了,蒋留下的权力也是要分而享之,而不会全部落在他何应钦身上。
何自知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李宗仁、阎锡山相比,即使蒋介石有不测,他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龙袍加身。为了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动,何应钦想到了汪精卫作为自己的合作者,他的布局是,先由汪掌党、政,自己握实权主军,等时机成熟再全面接班。
于是,何应钦致电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精卫收到国内的电报,喜出望外,急忙打电话预订12月22日回国的船票,并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置,盛赞“中央对此事一切决议,是应付事变的指南针”,宣告“要提前回国,共赴国难”。汪精卫急于回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何应钦,他有自己的考虑,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来代替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领导全国”。
何、汪的活动,已经昭然若揭。张学良想到,继续把蒋介石留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而送蒋回去,则可以造成南京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掌握不了实权,“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四是送蒋是日后张学良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封疆大吏也是军政要员之一的张学良日后必然还要与蒋介石打交道,因而南京迟早要去。如果基于安全顾虑而不送蒋,将引起蒋的更大怀疑,日后被扣的可能性也将更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与政治对手斗争的历史上,扣留政治对手是蒋介石惯用的方法,1931年扣留胡汉民,1932年扣留李济深,1938年扣留并枪杀韩复榘……避免被蒋扣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李宗仁的路子,不去南京,不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会议,保持半独立状态。胡汉民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常驻广州而拒不北上南京,从而保持了对蒋的牵制;韩复榘也效法李、胡的做法,但是,仅仅有一次没有顶住蒋氏的邀请,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军事会议,结果被扣于洛阳,随即被处决。汪精卫1936年年底抱着重新执政的期望从德国回国,先是住于上海,也是没有经得住蒋介石的邀请,回到南京,从此被蒋控制,所有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对于防遭蒋介石的毒手,毛泽东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6年8月,就致电张学良,说:鉴于两广事变的经验,南京是不能再去了。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去做,也不能效法李宗仁的路子。因为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他与蒋介石还存在着一时无法割舍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扣留蒋介石,是反对蒋的政策,却不反对蒋介石个人。他所设想的抗日,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这种以与蒋介石共事为基础所产生的政策指向,自然不可能预见与蒋氏决裂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想象不去南京的情形。
张学良断言:不送蒋介石回南京,可以避免蒋介石扣他于一时,而不能永久躲避,蒋介石要抓他、杀他,随时都可以做到,与其处于被动地位,不如主动上门。
张说:“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们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走好得多。”(8)从与蒋介石日后共事角度考虑,张学良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西安事变决非小事,把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扣于西安,让他丢尽脸面,险些丧命,这等奇耻大辱,他能善罢甘休吗?他能对于此种羞辱不去计较吗?在如此情形之下,张、蒋合作共事的基础还存在吗?张学良以为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纯洁无私的,用心是善良的,但蒋介石能否也能以同样的心态对待张、杨呢?如果那样,他也就不是蒋介石了。这也就是张学良对蒋介石认识不够深刻、对此事考虑不够周详之处。
五是送蒋乃效法古人故事,演出流传千古的好戏。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化敌为友、握手言和、重义轻利的动人故事。2000年前的汉代,就有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的典故,那时,赵国大将廉颇对上卿蔺相如骄横无理,而蔺相如却一再退让,他认为,将相不和于国家社稷不利。后来廉颇悔悟,就身背荆杖,去见蔺相如,虚心认错,请求责罚,于是将相和睦,赵国更加强盛。
张学良显然是受到了古人的影响,12月24日,他亲口告诉卫队团团长孙铭九,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9)张学良自比廉颇并不为过,但蒋介石却不是蔺相如,他没有蔺相如的胸怀,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于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清楚。他曾与其秘书栗又文讲过蒋的这样一则故事:
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钉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又退给许了,从此两人一直不睦。
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
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小,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10)明知蒋介石不可能有蔺相如那样的胸襟,却仍然坚持再演一次现代“将相和”,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张学良认为,他有“三张王牌”使蒋不敢扣他:一有“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不仅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存在,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到西安的目的,就是拆散“三位一体”,以便各个击破,但“三位一体”的团结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三位一体”更加团结,更加牢固,这使张学良认为,有“三位一体”存在蒋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说:
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只要)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
二有回西安的交换条件。西安事变时,南京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等以及几十架飞机同时被扣。张学良认为,只要不放走蒋介石的十几位大将和飞机,蒋就不敢扣他。张学良说:
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将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
三有他与蒋、孔、宋有良好的关系。张学良认为,他对蒋个人并无恶意,在释蒋问题上,孔祥熙和宋氏兄妹还欠着他的人情,何况蒋和宋氏兄妹对他的安全都有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