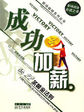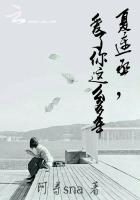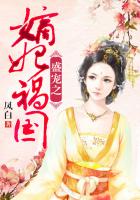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古人说:“知人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见形也若光之与影也。其察言不失也,若磁石去针,舌之取燔骨。”这就是说知人必先自知,不了解自己,也无法了解对方。人和人之间的相知如比目鱼须相并而行,如光生而影见,不可或缺任何一方面。圣人察言正如磁石吸引针,舌头吸炙骨。
人贵有自知之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谚说的好:“你的知识并不重要,你是怎样的人最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要努力的解剖自我,认识自我,自我省察修炼自我,再现自我的良好形象。
战国前期,有位“赫赫有名”的魏惠王。他之所以有名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将其祖父魏文侯、其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开了序幕。
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成了三晋中实力最强的老大。
为了称霸天下,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之间;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继起的魏武侯效法其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
应该说,父祖辈给魏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然而,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魏惠王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
根据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所以,魏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防止四面树敌。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遗憾的是,魏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
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把都城从安邑搬迁到大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魏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魏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尤为可悲的是,魏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
头脑简单却自视甚高的魏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魏惠王曾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攻齐,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互为死敌的本质属性,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
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魏惠王戴高帽,灌迷汤:“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
爱面子的魏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商鞅见招数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魏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即鼓动魏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用兵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魏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已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不敢仓促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
于是乎,魏惠王兴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
这时候的魏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身段。殊不知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魏惠王的面子亦随之丢得干净。
评点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魏惠王的可悲,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好高骛远,忘乎所以,稍有资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势便要摆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的确是大的智慧。但是普天之下能有几人做的清楚呢?战胜别人要比战胜自己困难许多,难怪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座大山,其实最难攀越的是自己。我很是相信这么一句话,的确,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能有几人战胜自己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应该关注的问题!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应该反思一下吗?在大智慧和小聪明之间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塑造自我,修身立命
人的一生,是自我修炼的一生。没有人生而完美,一切优秀的品质,都需要我们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完善和塑造自我。这就需要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而在我们不断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选择乐观的态度还是悲观的态度。我们思想上的这种抉择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也有可能阻滞我们前进。
祖逖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将领,他半夜闻鸡起舞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激励现代的人们刻苦努力、奋发图强。
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今河北省定兴县)人,他的父亲祖武曾经做过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太守。祖逖有几个兄长,父亲去世时他还年幼,生活就由兄长们来料理。祖逖生性活泼、开朗,从小就爱动不爱静。十八九岁时,他才开始励志读书,到二十三四岁时,已经博通今古。他还是一个谦虚好学的人,经常到京城洛阳向有学问的人请教。见过他的人,无不对他赞不绝口,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24岁时,祖逖当上了司州(今洛阳东北一带)主簿。主簿虽然只是主管文书簿籍的小官,但祖逖工作认真负责,还认识了一个叫刘琨的同行。刘琨是汉朝宗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同祖逖一样,刘琨也是一个有志气的青年。俩人情投意合,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无话不谈,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的时局,谈论自己的抱负,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建功立业,报效祖国。两个人经常谈着谈着就忘记了时间,直到夜深了才睡觉。
一天夜里,祖逖被一声鸡鸣给惊醒了。他向窗户外面一看,天色还有一些暗,一轮残月还挂在天边。祖逖心想该起床练功了,于是叫醒了刘琨。刘琨睡得迷迷糊糊的,就问祖逖怎么了。祖逖对他说:“你听,鸡在叫了。它这是在催我们起床呢。我们赶快起来练功吧。”刘琨听了以后,赶紧起床了。他们拿下挂在墙壁上的剑,来到屋外,在熹微的晨光下舞起剑来。从此以后,俩人每天都苦练武艺,还经常探讨兵法。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俩人后来都成了有名的将军。
晋朝时,匈奴贵族横行北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北方人民的生活十分不安定,有很多北方人到南方去避难。祖逖的家乡也受到了匈奴人的侵扰,于是,他带了几百名乡亲来到淮河流域一带。在逃难的过程中,祖逖主动把自己的车马让给老弱病残的人,与众人一起分享自己的粮食和衣服。祖逖一路上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人们一致决定由他来做大家的首领。经过长途的跋涉,他们来到了泗口(今江苏清江市北)。这时的祖逖已经拥有一批壮士,他们都来自北方,希望祖逖能够率领他们赶走匈奴人,尽快收复中原。
当时,司马睿还是琅玡王,还没有继位当皇帝。祖逖渡江到建康去见司马睿,并对他说:“现在朝廷局势大乱,主要是因为皇室内部纷争不断,大家互相残杀,给胡人留下了可乘之机,才使得他们攻进了中原。匈奴人无比残忍,他们残酷的杀害中原的百姓,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想将匈奴人赶出中原。只要大王一声令下,派我们去收复失地,北方各地的人民一定会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对付敌人。”
司马睿此时并不打算收复中原失地,但是听祖逖分析得十分有理,也不好推辞,他思量再三,最后勉强答应了祖逖的请求,任命祖逖为豫州(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刺史,同时还给了他3000匹布和可供1000个人吃的粮食,但是并没有派给祖逖人马和武器。
虽然只有粮食和布匹,但是祖逖并没有放弃,他将自己带来的几百名乡亲组成一支队伍,横渡长江。当船行驶到江心的时候,祖逖拿起船桨,一边拍打着船舷,一边发誓说:“我祖逖发誓一定要将那些占领中原的匈奴人赶走,否则我以后再也不会横渡这条大江。”祖逖的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随行的壮士都被他这种豪迈的气概所感动,个个心中充满了杀敌的勇气和决心。
他们很快来到了淮阴,并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祖逖和众壮士想尽各种办法制造兵器,并且在这里招兵买马,最后他们聚集了2000多人马,一路向北进发。当地的人们听到祖逖的军队攻来的消息,纷纷给予支持。很快,他们就收复了许多失地。
中原大乱之时,长江以北的很多豪强地主趁机占据堡坞,互相争夺。祖逖说服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使他们停止内争和他一起北伐。而对于那些不听号令甚至是依附敌人的豪强地主,则坚决予与打击。
祖逖的好朋友刘琨在北方听说祖逖的事迹之后,高兴地说:“我每天晚上都枕着自己的兵器睡觉,就是一心要消灭敌人。没想到,祖逖比我快了一步。”
公元319年,陈留地方的豪强地主陈川向后赵国主石勒投降。祖逖听说后,决定发兵进攻陈川。石勒派后赵国的5万军队来援救陈川,也被祖逖打得大败。随后,后赵的将领桃豹和祖逖的部下韩潜争夺蓬陂(在河南开封市附近)城,双方的战斗了持续了40天,仍然分不出胜负。由于战争时间过长,双方的军粮基本上都快耗尽了。
祖逖心中十分清楚,再这么相持下去,对自己很不利。于是,他想到了一个计策。他让士兵们将泥土装满布袋,封好袋口,让1000多名士兵,将布袋运送到军营里,装成好像在运粮的样子。最后,他又派几个士兵扛着几袋米,走到半路的时候,装作很累的样子,停下来休息。
桃豹在赵营内得到消息后,十分眼红,想将晋军的粮食抢过来。现在,看到晋兵在半路上休息,他心中大喜,马上派了大批兵士去抢米。晋兵看到赵军果然上当了,丢下米袋就逃。赵营里的粮食早已经吃完了,现在虽然抢到了一点米,但也只能勉强维持几天。士兵们看到晋营里运来那么多军粮,军心难免就有些动摇了。桃豹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派人向石勒求救。石勒收到桃豹的消息,马上装运了粮食,派人用1000头驴子给桃豹送去。祖逖早就得到石勒运粮的消息,于是,提前在路上设下埋伏,把后赵的粮食全部抢回了晋营。桃豹无计可施,只得连夜逃跑了。
通过祖逖不懈的努力,率领晋兵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领土。晋元帝登基成为皇帝以后,鉴于祖逖立下的功劳,将他封为镇西将军。
战时环境十分艰苦,但是祖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将领就与众不同。相反他的生活十分节俭,常用自己平时省下的钱去帮助部下。他经常身先士卒,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并不断的鼓励他们。他还奖励耕作,招纳新归附的人。
祖逖对待身边的人,不管关系疏近、地位高低,态度都很热情。一次,祖逖举行宴会招待当地父老。人们十分高兴,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场面十分热闹。一些老人流着眼泪说:“以前,我们每天都担惊受怕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杀死。现在,我们的年纪都大了,能看到自己的亲人都健健康康地,死也瞑目了。”
祖逖的种种做法,使他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
评点
《礼记?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首先要认识自己,托尔斯泰说过:“个人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则分数的值越小。”一个人应该具有良好的修养,只有先塑造自己,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目标是人们前进的动力,爱迪生曾说过:“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目标会给人带来希望,要想实现我们的目标,就要不断的超越自己。
切忌“夜郎自大”
“夜郎自大”的人,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不知道人外有人,只会盲目地高傲自大。而人之所以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往往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一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人们经常会产生高傲或自卑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也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了解不够。《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自食恶果。
赤壁之战,曹操元气大伤,刘备收复荆州,随后又夺取了巴蜀,孙权也巩固了自己在东吴的势力,自此以后,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
蜀国这边,由关羽留守荆州,一直想要吞并东吴,关羽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武艺高强、兵强马壮,连连向北边的曹操发动进攻。
东吴这边,鲁肃在世时,一切以大局为重,他主张联合西蜀,共同对抗魏国。蜀吴之间虽然也有一些战斗,但是关系仍然十分紧密。鲁肃死后,孙权将鲁肃的手下全部调给吕蒙统领,并封他为汉昌太守。这样一来,吕蒙的辖地正好与关羽留守的荆州紧紧相连。吕蒙深知关羽一直有吞并东吴的野心,并且他占据了吴国的上游,如果一直这样分而治之,对吴国必然十分不利。当初孙刘联军是为了抵抗强大的曹操,而现在,随着西蜀势力的逐渐强大,三国相互吞并已成必然。
于是,吕蒙上书孙权:“依现在的形势看来,我们应该先夺取荆州,然后派征虏将军孙皎守卫南郡,潘璋守住白帝城,蒋钦率领万名游兵,在长江中下游巡行,哪里有敌人就将他消灭。接着,由我带兵北上攻取襄阳,到时候,我们就完全控制了长江,那么,我们的声势就变得更大了,那时曹操和关羽何足为惧?”
孙权说:“关羽把守荆州,现在他兵强马壮,士气正盛,恐怕很难攻下,为什么不攻打曹操的徐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