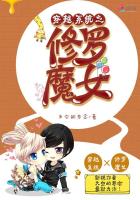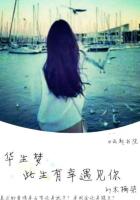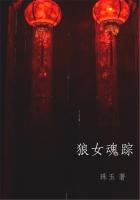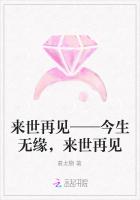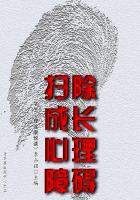纪晓岚双手接过扇子一看,果然是匆忙中漏写了一个“间”字。他心里一阵紧张,但纪晓岚毕竟是纪晓岚,他拿着扇子略一思忖,便有了主意。急忙奏道:“皇上明鉴,臣是将自己所作的一首长短句(古代的词和乐府诗因每句的字数不同,所以称长短句)书在皇上的扇子上,想请皇上指教。虽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字面近似,但句读(语间的停顿。古人写诗和文章,从不用标点,掌握断句是基本功)完全不同。”说完偷偷瞥了一眼乾隆。
乾隆在古代的皇帝里也算是一代风流天子,崇尚风雅,自诩为“圣学渊源”,但他接过扇子反复琢磨,怎么看也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除了漏掉一个“间”字,没有半点不同。心想:尽管你纪昀才高八斗,但白纸黑字,看你如何狡辩。于是板着脸说:“你既说是你的长短句,且读来朕听,若有矫言,朕可要治你欺君之罪!”
这时纪晓岚胸有成竹,只听他抑扬顿挫地朗声诵道: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乾隆惊呆了,他细细品味着这酋长短句,发现不但文意畅通,语势连贯,而且音韵和谐,朗朗上口。根本看不出勉强改动的痕迹。从风格和意境上看,保持了《凉州词》的雄浑苍凉,确实不亚于王之涣的原诗。乾隆心中叹服,哈哈大笑:“好你个纪晓岚,果然机敏,确有奇才,不愧我大清第一才子!朕有你佐治文事,可以高枕无忧了!”
评点
纪晓岚能够化险为夷,自圆其说,在关键时刻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在于他善于应变,从容自若。他能够及时调整思维,巧妙的回答问题,换几个角度,别出心裁,为自己打圆场,同时又不偏离问话的限制。如果他只顺从一条思路,只遵循一种逻辑,陷入单向思维的死胡同,就不能免去灾祸了,言语上出现过失,要及时灵活的相处应对的办法。我们经常需要补救的不只是言语上的过失,也有外界突然发生的局面需要在瞬间作出判断,灵活应对。既然危险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冷静下来,从容应对,将错就错,或许能化险为夷。
韬光养晦,谨慎做人
韬光养晦是要隐藏自己的光芒,使自己处在一个相对不显眼的位置。韬光养晦表面上看起来是退却,其实具有很强的进取性。善于与他人相处,它是一种优秀的策略,也是有“心机”之人的处世之道。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懂得韬光养晦,从而保全自己的。
说起韬光养晦,不能忘记这一谋略的高手曾国藩。在当时的清朝,曾国藩能够稳稳地坐在权势的位子上,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韬光养晦之道。这个颇有“心机”之人,懂得适时进退,懂得适时掩盖自己的锋芒,所以才会仕途顺利,官运亨通。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长沙府湘乡县(今湖南省双峰县)人,早年曾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风云一时。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这支队伍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这支军队的士兵全部是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只对曾国藩一人绝对服从。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以后,矛头首先就指向了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全部都归曾国藩管制。自从清军入关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的也就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当时获得的权力,可以说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获得的最大权力。
对于这样的显赫官职,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洋洋自得,他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战功卓著,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称得上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曾国藩是一个很富有心计的人,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不可一世。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处世也更加谨慎。在这个时候,他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良狗烹”的厄运。身处高位的他,想起了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他曾国藩可不想做这样的人。
于是,他就给弟弟曾国荃写信,嘱劝其将来遇到机缘,要尽快地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为了让弟弟听从自己的劝告,曾国藩叫他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罪,清廷本想追查,但好在曾国藩很知趣,进城以后,恐怕自己功高震主,树大招风,于是就急急忙忙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的有才之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做完这三件事,形势立刻发生了变化,多方面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也都不再上奏弹劾了,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无话可说,只好不再追究。
后来,曾国藩又给清廷上奏折,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会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没有了昔日的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是个颇有心计的人,考虑问题也很周到,他在奏折中只请求清廷遣散湘军,但是在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留下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要挟朝清廷的意图。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就开始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曾国藩不自己把问题提出来而等着清廷来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自己的地位肯定也是保不住的。
就在朝廷琢磨着该如何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曾国藩自己主动提出了遣散湘军的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个目的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所要达到的。
评点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章太炎对他的评价最为客观,称他“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他淡化了自己头上的光环,瞻前顾后,委屈自守,最终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菜根谭》中说:“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则危;能事不宜太华,太华则衰;行宜不宜过高,过高则谤兴而毁来。”韬光养晦的目的在于趋时避害,麻痹对手,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它是精明人的一种策略。
说话要看对象
为人处世要灵活一点,在面对不同的人时,要调整自己的应对之策,不能一概对待。古语云:“夏虫不可以语冰”。同样的道理,跟讲道理的人才可以讲理,对那些不讲理的人讲理只能是对牛弹琴。
说话是一种艺术,必须看对象,分场合。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会取得不一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有的人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并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尊重对方,有时候也能保护自己。
孔子带着他的几名学生出外讲学、游览,一路上十分辛苦。这一天,孔子一行人来到一个村庄,他们在一片树荫下休息,正准备吃点干粮、喝点水,不料,孔子的马挣脱了缰绳,跑到庄稼地里去吃了人家的麦苗。一个农夫上前抓住马嚼子,将马扣下了。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一贯能言善辩。他凭着不凡的口才,自告奋勇地上前去企图说服那个农夫,争取和解。可是,他说话文绉绉,满口之乎者也,天上地下,将大道理讲了一串又一串,尽管费尽口舌,可农夫就是听不进去。
有一位刚刚跟随孔子不久的新学生,论学识、才干远不如子贡。当他看到子贡与农夫僵持不下的情景时,便对孔子说:“老师,请让我去试试看。”
于是他走到农夫面前,笑着对农夫说:“你并不是在遥远的东海种田,我们也不是在遥远的西海耕地,我们彼此靠得很近,相隔不远,我的马怎么可能不吃你的庄稼呢?再说了,说不定哪天你的牛也会吃掉我的庄稼哩,你说是不是?我们该彼此谅解才是。”
农夫听了这番话,觉得很在理,责怪的意思也消释了,于是将马还给了孔子。旁边几个农夫也互相议论说:“像这样说话才算有口才,哪像刚才那个人,说话不中听。”
看起来,说话必须看对象、看场合,否则,你再能言善辩,别人不买你的账也是白搭。
《世说新语》有这么一则故事。许允担任吏部侍郎时,大多任用他的同乡,魏明帝曹睿听说后,就派虎贲武士去拘捕他。他妻子跟随出来告诫他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让他向皇帝申明道理,而不要寄希望于哀情求饶。带到后,明帝核查审问他,许充回答说:“孔子说‘举尔所知’,我的同乡,就是我所了解的人。陛下可以考察他们是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我愿意接受应有的罪名。”考察以后,结果各个职位都安排了当用的人,于是才释放了他。许允身上衣服破烂了,明帝下令赏赐新衣服。
许允提拔同乡,是根据魏国的荐举制度。不管此举妥不妥当,它都合乎皇帝认可的“理”。许允的妻子深知跟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争,于是叮嘱许允以“举尔所知”和用人称职之“理”,来抵消提拔同乡、结党营私之嫌。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来选择说话的绝好例子。
南齐的徐文远也是这样一个人。
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跟随父亲被抓到了长安,那时候生活十分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侗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李密,于是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李密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兵士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心效仿伊尹、霍光,在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仍然希望能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李密答谢说:“我敬听您的教诲。”
后来李密战败,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谦恭地对他行礼。有人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倨傲,但却对王世充恭敬万分,这是为什么呢?”徐文远回答说:“李密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像郦生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王世充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查看时机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唐朝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评点
徐文远之所以能在五代隋唐那么混乱的局势下保全自己,而且屡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没有一刀切。
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针对不同对象和对象的不同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做事要分轻重缓急
做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完成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必须要弄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该缓的地方缓,该急的地方急,做到缓急有度,轻重有序,使事件的进程在自己的掌握之内。眉毛胡子一把抓,只会使事情越做越糟。
秦始皇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六国的军事进攻当中。他决定先从最弱小的韩国开刀,然后由近至远,从南往北;先三晋,再荆楚,再燕齐,逐一灭亡六国。于是从秦王嬴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开始,秦国对六国的最后一战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正式吞并各国。
韩相对强大的秦国来说,小小的韩国犹如老虎嘴边的羊羔,只有浑身战栗的力量了。韩非死后,韩王安自知韩国难保,于是主动提出“请为臣”,不敢再与秦并称为王。但是,这并不是秦王嬴政所要求的最后结果,他不是要六国臣服,而是要它们的江山、土地和人民。所以韩王安“请为臣”,并不能使自己苟安多长时间。
秦王嬴政十六年(公元前231),韩王安又把南阳全境献给秦国。秦始皇派内史腾做南阳假守。第二年,秦始皇命令内史腾就近攻韩,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韩军,生擒韩王安,至此韩国灭亡。秦始皇下令在这里设置颍川郡。
灭亡韩国后,秦始皇命令秦军继续收拾赵国。因为赵国紧挨秦国,军力又强,不先破赵国,秦军东出始终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此时赵国遭灾,正可趁火打劫。
公元228年,赵国灭亡。
韩国、赵国灭亡以后,三晋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魏国完全处在了秦军的包围之中。
早在公元前231年,在秦军的进逼下韩国把南阳全部献给秦国时,魏国也不落后,跟着韩国采用这种剜肉医疮的不是办法的办法,把丽邑献给秦国,以此来换取几天的残喘。秦军向韩国、赵国进攻时,自身难保的魏国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出兵援助它们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军一个一个地收拾它们。
灭赵以后,秦军与燕国发生一些纠缠,耽搁了一些时间,没有立即对魏国采取行动。直到秦军攻下了燕国的都城蓟,迫使燕王喜逃往辽东,燕国灭亡在即的时候才调头回来抽空解决眼皮底下的魏国。
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军在王翦的儿子王贲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魏都大梁城外。魏军严阵以待,准备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谁知,秦军将大梁团团围住后并不进攻,而是筑堤引来了黄河水,采用水攻。魏军在水里苦撑了三个月,终因城被泡坏,无法再守,魏王极不情愿地出城投降。秦国尽取魏国之地,魏亡。
三晋灭亡,燕国无还手之力,剩下的就是楚国和齐国了。先对付谁?秦王嬴政选择了楚国。于是,楚国“荣幸”地成为第四个被灭亡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