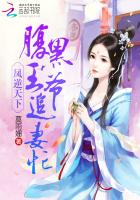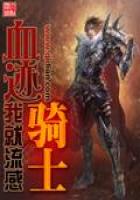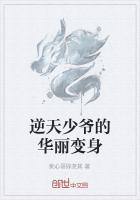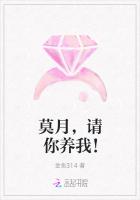那个初冬,我们游荡到一个山村,见有一个干薯秧垛,就坐在垛前,让阳光抚慰我们饥饿的肚子。我不经意地撕一根干薯秧放进嘴里嚼,觉得干薯秧苦涩里透出一丝甜。于是,我们就撕扯着吃起来。一会儿干薯秧垛就被我们撕扯得一塌糊涂。突然,一个黑脸老汉从村里奔出来,目光穿过尘埃,噼噼啪啪落在我们身上,大叫:“哪来的一帮浑小子,到这里来糟践人!”我们望着愤怒的老汉,惊恐不已,但仍贪婪嚼着薯秧。老汉见我们一个个饿死鬼似的吃得那么凶,一下呆住,愤怒顿飞,忙说:“孩子们,这些薯秧都捂坏了,吃了会中毒的!哎,看把你们饿的。”他略一沉吟,“孩子们,我家里有煮熟的红薯,走,去我家。”
我们和这位老汉素昧平生。他的邀请使我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忸捏起来,但还是经不住他一再督促。我们走进老汉家,交谈起来,才知老汉姓张,是大队支书。张支书家的饭桌上摆放着煮熟的红薯。红薯散着缕缕的香甜,馋得我们一个个直流口水。张支书脸上的慈祥一波一浪荡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快吃吧。”我们客气一阵儿,最终还是忍不住拿起了红薯,香飘万里地吃起来。吃着吃着就吃湿了眼睛。走时,张支书又让我们每人带上了几个红薯。他说:“你们这些牛犊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只吃五两饭怎么能行?也是暂时困难,挺挺就过去了。以后要是饿极了再来找我,可不兴乱吃了,要吃出麻烦来,你爹娘还不疼死。”
日光融融,温暖地照射着一棵棵小树。山水潺潺,使张支书的话语更加情意深长。我们品味着张支书的话语,嗅闻着袋里红薯的芳香,不觉又一次湿了眼睛。张支书把我们送出老远。我说:“张支书,谢谢您啦,您回吧。”张支书说:“客气啥,从战争年代,我这里就是同志们落脚的地方,吃顿饭是不上唇齿的事儿。”
我们撕坏村人干薯秧垛的事儿,很快传进校长的耳朵。校长治校极严,一听我们违反了群众纪律就要处分我们。我得知后,一种惊恐迅疾转成颤儿传遍全身。这天,我躺在床上瞧着屋笆,直把满屋瞅黑也没起来吃饭。等到熄灯铃响过后,我悄悄爬起来,顶着满头颤抖的寒星,踩着高低不平的山路,摸到张支书家。张支书见我张口岔气深夜来访,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叹了一口气,将校长要处分我们的事情对他说了。他吸一阵儿烟,胸有成竹地说:“甭怕,这事儿有我呢。”
第二天,张支书推一大捆干薯秧头,和一篓鲜红薯到学校来了。张支书墨菊一样的脸庞浮在一车红绿中,一下惊亮了满校园的目光。我急忙领着张支书去见校长。张支书接过校长递来的香烟,把些许拘谨吸进肚内,吐出一团浓浓的温馨说:“校长,前天,这孩子和他的几个同学帮我把一垛干薯秧打成糠,给我省了不少力,我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酬谢,只有这些薯秧头子和红薯,一点儿心意,您别嫌少。”那个初冬,这车薯秧和红薯能使一个班的学生一天不挨饿,太珍贵了!校长一听,他的学生是在外边做了好事,而不是像班主任汇报的那样违反了群众纪律,高兴起来,便和张支书亲切交谈起来。谈着谈着,就谈到师生饥饿问题,谈着谈着,张支书就主动提出负责给学校联系买一些干薯秧,磨细了掺到薯面里,做成馒头,让学生充饥,度过暂时困难。
不久,我们便去张支书的村子搬运干薯秧。张支书为我们熬好了一锅薯面粥,让我们吃。粥的香甜招得我们肚子咕咕乱响。张支书眉眼含笑地说:“同学们喝呀,还愣着干啥。”于是,我们每人盛一碗吸吸溜溜喝得粥香伴着快慰满院飞。张支书收拣起那些个快慰摁进他的烟锅里有滋有味地吸起来。张支书忘情地吸着烟,忘记了喝粥。那一大锅粥,转眼,就被我们喝光。
我们挑起捆好的薯秧上路了。张支书送我们一程又一程。我们呐喊呼叫着,绕一阵儿九曲盘山路,就过五龙桥。五龙桥是用原木排起来的过涧桥,悬在半空,荡出许多危险。我们男生英雄气十足地过了桥;可几个女生望着五龙桥,一个个抖着小腿,不敢越雷池一步。张支书怕出意外,就跟带队的老师替她们挑着担子送她们过桥。张支书没有吃中午饭,挑过几担,头冒虚汗,身子直打晃;但他还是接过一亮丽女生的担子,振作精神,踏上了五龙桥。担子嘶哑沉重的叫声,碰碰撞撞响在桥上。猛地一股劲风携带着枯草树叶飒然而至,撞了张支书的胸,绊了张支书的脚,吹飞了张支书挑的一捆薯秧。张支书叫了一声,身子晃了几晃,晃出我们一片惊呼,就跌进流水呜咽的五龙桥下。
张支书被人从河里救起,送进医院。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我们围在他床前,只知抹眼泪,不知说啥好。倒是张支书忍不住颤抖着伸出手,亲热地拉着我说:“看,我还有的是力气呢,明天误不了帮你们联系买薯秧。”
张支书话一出,我们全放声哭了。我们沐浴在从窗外射来的一片阳光中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