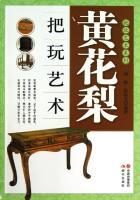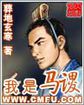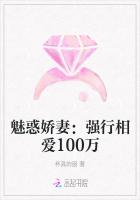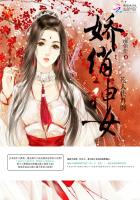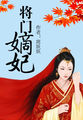——记西部画家王天一鲍文清
藻鉴堂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颐和园的藻鉴堂认识了来自西部的画家王天一,说起来这次邂逅,还真有点戏剧性。
藻鉴堂是颐和园的园中园,坐落在昆明湖西边的一个向湖中伸延的小岛上,三面临水,草木葱茏,景色绝佳,文化部选中这里作为画坛大师们共商国画艺术复兴的聚会之所,来的人都是国画界的顶尖人物,有当时健在的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叶浅予、何海霞、关山月、朱屺瞻等,还有至今仍很活跃的吴青霞、白雪石、许麟庐等大师级的画家。这批国画界的大腕们,刚刚度过了文革那场恶梦般的年代,相聚一起自然有一种重获解放的感觉,互道平安倾诉衷肠,偌大的厅堂里欢声笑语一片,我作为一个报道文艺界多年的记者添列其中,自然也感觉到一种少有的快乐。
只是有一个人我并不认识,他比大部分与会者显得稍微年轻,是画室里最忙的一个人,一会儿迎客,一会儿送客,端茶倒水,毕恭毕敬地向大师们请教着什么……。画家们共进晚饭后,有的回卧室休息,有的回家,画室里只留下他一个人留守。我想,这大概是文化部请来的杂工,是专门为大家服务的。一次,在观摩大师们的作品时,我忽然发现一张独具一格的“牵牛花”。这张画从未见过,一簇迎着朝阳怒放的蓝色牵牛花,花色艳丽中透着淡雅,生动活泼之态跃然纸上,构图简练,画风异常清新明快,我环顾左右问,这张画是谁画的?大家的眼光一齐转向了我一直误认为杂工的那个人,许麟庐问我:“你不认识他?就是这位来自西部的画家王天一!”,我马上向他道歉,请他恕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
他五十出头的年纪,四四方方的脸上挂着一付眼镜,脸上浮着敦厚谦和的笑容,说话的嗓音很响,也很自信。因为太喜欢这张“牵牛花”了,我提出采访他的要求,他婉拒说:“有这么多大师级的画家在,你还是写写他们吧!”同他们相比,我只是一个花鸟画的新兵,实在要写,过二十年再说吧,那时,估计我的花鸟画可能会成为气候,同时,我的经历很坎坷,简直是不堪回首,到那时我再向你倾吐吧。”
光阴荏苒,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这期间他曾来过北京,一次给中南海画画;一次是同我商量出版魏晋墓画册的事。2000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接到了一封来自甘肃画院的信,是王天一写来的,信中说,王天一个人画展定于2000年10月26日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开幕,恭请莅临指教信的末尾他还写了一首七言诗,云:
步履荆棘赶斗牛,迎来旭日照神州。生平不做春风梦,愿吹军号到金秋。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他二十年前同我在藻鉴堂草坪上讲的一番话。同时从他的诗中也悟出了他信中的一番玄机: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正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他的花鸟画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风格,他准备在这二十年中刻苦作画,使自己的画在中国画中自成一派,那时必携画来京汇报,画展的同时他将向新闻媒体尽情倾吐一下他多年压在心头的块垒。
画展如期开幕,当年在藻鉴堂共处一堂的画友,再一次聚集在中国画研究院。老一代画家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步态龙钟,有的坐着轮椅赶来祝贺。展室中鲜花遍地,祝贺声不绝。王天一为这次个人画展准备了150幅作品,有寻丈巨制,也有小品册页,内容包括花鸟、人物、山水及西部风情,写意熊猫等,集中展示了王天一近20年来的国画创作风貌,这是西部画家在北京举行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一次个人画展。王天一和他的相濡以沫的老伴张帆端坐在鲜花丛中,脸上挂满了喜悦的笑容。
看完摆满楼上楼下四个展室的作品,行家及观众一致认为王天一在花鸟画上,传统绘画功力特别深厚,题材非常广泛,这是一般花鸟画所不及的。不仅有四君子,十大名花,同时也画新花野卉,通过画家之手注人了新的思想境界。他的花鸟画给人以清新奋进之感。王天一半生坎坷,可他的画却充满了朝气。也说明了王天一的精神境界是极其高尚的。牵牛花给人朝气蓬勃之感,马兰花给人以坚强不屈的启迪。他画的竹传统面貌很强,但造型既不同于古人,也不是自然的写生,画家既有新的笔墨规律,也有新的思想感情,是宏伟而不是清秀,是雄健挺劲而不是舒风细雨,别人画竹枝竹梢,他还画竹根竹笋,天真可爱,在自然的环境之中,贯注了人与自然的理想境界。十一幅熊猫各有面目,非常生动。从他题记中可以了解王天一曾深入深山老林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写生。王天一画展的一部分是山水画,和花鸟画一样是在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力基础上,以写实的手法创作的。有真实感,而不是自然摹仿。在他的山水画有小青绿,也有水墨浅绛,随意画成,千变万化。王天一的画展作品里还有近二十幅人物画;有借鉴古代壁画的,也有历史人物画创作,这与他的历史知识和对绘画高超的修养分不开的,有幅历史人物画《李广》白发苍苍不下战场,这也是王天一个人思想的写照。对艺术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很坚强。
二十年来,王天一所探索的道路是全方位的。尽管说以花鸟画为主,但山水、人物都涉猎了。而且绘画水平都相当高超。综观他的绘画境界,对人,对社会充满了爱,不仅传统功力极深,而且艺术面目非常新颖,时代气息十分显明。
以上是我看了画展及听了专门为王天一画展所开的美术评论会对他二十年游学与修炼所得的一点印象。我不能不感叹,王天一真是一条汉子,说到做到,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我还有一个问题:王天一前五十年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画展后,我到王天一的寓所拜访了七次,听他和他的夫人推心置腹地讲述了画家的人生之路。
小画家
没到过甘肃的人,也许会把那个地方视为地老天荒之地,殊不知那里有许多地方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位于陕甘川交界处的成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公元8世纪唐代大诗人杜甫入川时就曾在这里驻足并曾打算定居于此。
1926年11月,王天一就出生在成县一个耕读之家,也许是受到山川灵气的熏陶,王天一自小就与绘画结下了割不断的情缘。上小学时,他的一个舅舅是他的美术老师,舅舅李成画的是清代水墨,不管谁向他要画,他都乐于从命。小天一总是跟在他的身边,宁神静观,涂涂抹抹,舅舅见他如此痴迷,就破例拿出一些时间,认真教他笔墨功夫,印手画手,看花画花,画双勾线条,有时舅舅画什么他也画什么,但他还嫌不足,舅舅就从书柜里翻出清代几位着名书画家的画册来给他看,舅舅还把珍藏的画册《芥子园》画谱给了他,不到两年他临摹了个遍。翻着他临摹的作业本,父母不得不郑重地考虑儿子的前途问题了。父亲的原意是让他读几年书以后,去杂货行当伙计,学做生意。母亲却慧眼识珠,看出他是一块学画的料,就劝父亲改变主意,让儿子多读几年书再去学画,父亲拗不过母子的苦求,只好同意。
舅舅家比较穷,一辈子教书,一辈子给人义务作画,以能画画送人为最大快乐,自己白搭上纸笔墨不说,到死也没给子女留下一张画,有时画画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抓两把黑豆在炉火上炒炒权当夜宵。成县还有位姓姚的画工,擅长各种画,笔墨线条很好,王天一就主动登门拜访,求他指教,他只许看也不教,从他那里也学得一些绘画技巧。还在小学时代他就怀揣画本,到处临摹。离家不远有一座关帝庙,庙里有彩塑和壁画,这里的桃园三结义和出五关的故事令他着迷,一点一滴临摹下来。回家以后就“依样画葫芦”照着小画本放大来画。‘没有纸墨笔砚,他就在家里家外的墙上、地上、影壁上到处点画自己喜欢的景、物、人,爱画的精神有点出奇,渐渐有了点小名气,这里人家为了美化穷困单调的生活,买来纸、笔,请他画条屏、中堂、门画、窗花、绣花样,他自然乐于从命,他的绘画作业,每每在课堂上被老师批为100分,他像中了状元一样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此更加痴迷,成了乡里县里知名的小画家,这是十几岁上发生的事情。小学毕业之后,考上成县师范学校,开始接触西方绘画艺术,课堂上学素描造型和西方绘画的基础知识。课堂外临摹自然、景物,应人所邀给个人画些画,虽然粗糙、却颇似模似样的作品,也还大气,乡人称赞自己更是非常得意,他更加认定了“画画也是职业,也能挣饭吃”的道理。成县师范虽然能接触绘画,但毕竟不是专科,他觉得这个天地太小,便一心想飞出去,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抱负。18岁时,只身去西安投考技艺师范学校的美术科,校长很欣赏他的美术天才。但看他过于自立和成熟便怀疑他是陕甘宁边区派来的卧底者,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这是他生平遭遇的第一次挫折。但他学画的心不死。
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当时西安局势很紧张,没考上学校的他只好流落街头。幸亏遇到了学校的一位教师顾群,他是一个好人,见王天一背井离乡,孤苦无依,便收他为课外学生,单独教他绘画,并照顾他吃住。半年后师母侯杰因是西安地下党被捕入狱,顾老师一家陷人困境,王天一在西安呆不下去了,只好辞别老师回到成县,他找到了师范的老校长,推荐他到成县初中当美术教员。一年多的教学生涯,更加强了他学习绘画的决心,积足了路费,旋又转头来到了成都,考入四川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科,师从毕晋吉学国画,师从李有行学西画,其间他到成都青龙场昭觉寺也曾受到过当时客座教授张大千作品的熏陶,大开眼界。这个学校学风好,教育质量高,他如饥似渴地打造绘画基础,各方面进步很快。
但好景不长,这时已是1949年,西安已获得解放,四川也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川陕公路,学校停课,王天一只得打点行装,徒步从成都沿蜀道剑阁经广元入甘小道,走了七天回到陇南家乡。此刻,解放的曙光已临近甘肃,小画家王天一的艰难的求学之路已经快走到头了。此时陇南地下党在成县发展,为蓄积宣传力量,经他一位小学老师介绍,加入了地下党,准备迎接新时期的到来。
军旅画家
在陇南家乡,王天一迎接了甘肃全境的解放,1949年冬天部队南下时,他和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女友张帆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担任七军文工团的美术教员,张帆担任老同志的文化教员。参军前,他画了一张绘画,画上是一个长衫褴褛的乞丐,身背了讨饭筐,拖着一根要饭棍,题目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意在警示自己,丢开画笔,就是这个下场。现在呈现在他俩面前的是一片光明,再也不必担心“徒伤悲”了。在部队受到的教育使他原来的“画画是为了挣饭吃”的思想得到了升华,逐渐懂得了“画画为了宣传,宣传是为了革命,革命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朴素的人生道理。部队是供给制,一天三顿饭不用愁,主要任务就是美术宣传和画画。二十几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给宣传队画拉洋片的脚本,给基层的人们画领袖像,给爱好美术的战士上绘画课……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叫苦叫累,他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有意义。
抗美援朝开始了,能打仗的都上了前线,有特长的留了下来,他被调到西北军区文化部战士读物出版社当美术编辑,黄胄是创作组长,他和黄胄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切磋绘画艺术,互帮共进,得益匪浅。他的最大收获是增强了美术创作源于生活的道理。他的第一部创作,就是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完成的。这是一组反映解放军部队建设天兰铁路的28幅小油画,从自然景观、劳动场面、战士生活、劳动模范的精神风貌,各方面描绘出建国初期那种特有的战斗化生活和艰苦创业的忘我精神。这组作品参加了当时西北军区第一届文艺大检阅,王天一被评为部队优秀文艺工作者,获得一枚一级文艺奖章。接着他又创作了油画《巡逻归来》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追歼》、《猎归》参加了全国青年美展和西北美术作品展览。以后他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完红军在甘肃境内走过的长征路,从甘川边境一直走到会宁,他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会宁三军会师后,毛主席在一个晚会上高声吟诵了他的长征诗。此前,他很想画人物画,历史题材也不好画,但他在红军会师后的胜利心情的鼓舞下,为创作积累了部队的素材。他作为画家的最大愿望是创作巨幅的油画《瓦子街大捷》,当时,他们的创作组接到中央军委“西北要拿出一幅大画”的指示,到陕北宜川瓦子街体验生活后,计划创作组每人都拿出一张草图,结果王天一的构图被选中,作品完成后,在全国美展获得了殊荣。王天一等甘肃新一代画家的名字也第一次在全国上了榜。
王天一的军旅生涯前后延续了六年,他万万没想到,正当大有作为的时候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厄运,先是审干,他中学时期曾被集体拉入三青团,想不到在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都被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自然和参加地下党的问题联系了起来,是否真的加入了地下党也受到了怀疑。总之,他再也不能留在部队了,必须转业。考虑到他在部队的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让他转到省文化厅美术工作室继续搞绘画。这当头一棒的打击,使他几乎晕头转向,但好在还有继续作画的环境和条件,只要是这个权利不被剥夺,再大的委曲也能忍受。转业到地方以后,审查还在继续,莫须有的罪名上纲上线。他的假地下党员的问题被主观武断地肯定,接着又是双反运动,检查他在画报上发表的作品,说他画上的贫下中农“画胖了,像地主”,于是又被扣上了只专不红,白专典型的帽子。1957年反右他侥幸躲过,可是随之而来的反右补课,他却没有躲过。据说甘肃文化艺术单位百分之五的比例不够,硬要凑成此数,于是王天一在劫难逃,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保留公职,劳动改造。这时,甘肃省刚刚成立了一个地方戏陇剧团,王天一被发配到陇剧团。
陇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