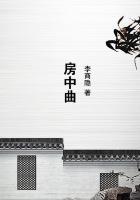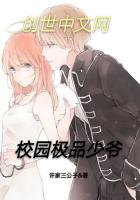惊蛰的一声春雷,把冬眠了一季的万物给彻底唤醒了,大地仿佛一夜之间就泛起了新绿。那一声春雷同时也唤醒了歇了一冬的农人。惊蛰一过,清明也便不远了。“清明下秧,不用问阿爹阿娘”,这是代代相传的古训。春分一过起畈做秧田,筛谷选稻种,仓库孵秧子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待到清明,秧田里已经是绿意盈盈生机盎然。这是全队人生存和生活的盼头。
稻秧壮了就该插秧了。插秧在我插队那地方叫种田。为何这么叫我无从查考,但这是一年中的大事。早稻成长期,气候好,雨水足,故早稻产量大大高于晚稻,一年的口粮、公粮、收入大多寄托在春种上了。
在稻秧呼呼往上拔的时日里,家家户户都准备开了。去市场上买了新土箕准备挑秧用,找好陈年的早稻草,修剪整齐了备着缚秧用,锯好一米见长的细竹竿,那是用来丈量行距的。最要紧的是种田绳。种田绳是一种细细的塑料绳,缠在一个木制的,形似三国名将典韦使用的短戟那样的农具上。这农具一头削得尖尖的,可以深深地插进泥地,人一拉塑料绳,它就如陀螺般飞快地转动起来。种田绳把耙得平整如镜的耕田切割出一米见宽的长廊,人框在其中插秧,不会越规矩一步。
要插秧先得拔秧。天还未亮全队的社员就围到了秧田旁,挽裤腿,卷袖子,踏入还瘆得人直打战的秧田。“开秧门,关X门喽”总有油嘴的汉子冷不丁地就一脸坏笑地嚷嚷起来。这是说,插秧是个累活,面对泥土背朝天,一天下来腰酸腿痛,晚上就没那劲了。喊声刚落,油嘴的汉子就遭到泥、水的痛击。这是年轻媳妇和娘儿们发动的攻势。于是,一阵欢快放肆的喧闹在秧田上空荡漾起来。
待大伙像蚕吃桑叶般地把秧田啃得七零八落时,队长一声令下,大伙就起程赶往要插秧的田畈了。留在秧田里的都是上了年纪的,继续为前方提供稻秧。田畈里早已天女散花般撒开了绿油油的秧捆。大伙就用灵巧的双手一株一株为大地绣上了绿色。日复一日,绿色渐渐地扩大再扩大,直至整片田野都缀满希望的绿色。全队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希望就这样被插在了土地上。
常言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一时”,除了说别误了时令,也包括田间管理。早稻种下去了,除了灌溉、施肥,耘田是很重要的一环。耕耘耕耘,只耕不耘也不会有好收成。秧插下后历经枯黄、返青、嫩绿,约半个月后施追肥,这就得耘田了。
耘田,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去杂草、松松土,就如给水稻按摩,让它舒坦一阵后长得更猛。但这活讲究责任心、认真劲。有个叫法很形象,叫“摸六株”,每株稻你得摸到让它伸伸腰,遇杂草就拔,再团成团把杂草深陷进稻田里做养料。这么大一片稻田,摸得不到位,拔得不干净,一时半会儿是很难看出来的。
耘田这活说苦确实很苦。干这活得跪着,一点一点地往前爬,往前摸。膝盖磨痛不说,还得经常惦记着别让蚂蟥光顾你的腿。一次耘完地回家,我饥肠辘辘,匆匆洗了腿上的泥,就冲向灶口做起饭来。只觉得大腿处有痒丝丝的感觉,一看,一条粗如拇指的蚂蟥正吃饱喝足了如红灯笼般悠悠地挂在大腿上。我怒从心头起,操起一把柴刀,把它按在石板上一顿猛斩,喷出的鲜血射了我满脸。现在想着心酸,当时却只有愤怒。
待到稻子长大了,耘田就更遭罪了。稻叶带着细细的齿,就像锋利的锯。大腿、手臂在稻叶长时间的划拉下,就被锯出了斑斑的血痕,一碰到水就火辣辣地疼。所以那时候那些细皮嫩肉的女知青都死活不干那活。
耘田也有乐趣。大伙儿一字排开,一人六株往前摸。一边不着边际地打诨海聊。队上哪家哪户的新鲜事、混球事、家长里短、汉子婆娘是妇女、姑娘的主题。队上的老古,祖上的古训,《三国》,《水浒》,谁家的媳妇、姑娘漂亮,干那事受用是男人们的话题。劳作的辛苦和漫长就是如此被打发的。还有一乐,耘田时大家都背着个“克篓”。爬着爬着,泥鳅、黄鳝就给拽上了,田螺青蛙就给抓住了。到了用餐时这就是美美的野味了。
刚下乡那阵听那些老农民说,稻子是跪大的,我不明白。在经历了耘田后,我明白了其中深切的含义,既有辛酸又有喜悦,很朴素又饱含哲理。
一接近小暑,稻子就开始扬花受孕了。那些日子稻田里是一天一个样。你盯着稻子看上几小时,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过一夜你去看,它悄悄地就挺胸凸肚了,没几天就灌浆长穗,低头弯腰了,一日比一日金黄。生命就是如此神奇,不知不觉间生生不息。
当满世界稻花飘香的时候,这一年中最忙、最苦、最累的“双抢”也到了。“双抢”也叫夏收夏种。在七月二十日到立秋这半个多月里,要把近四百亩的早稻割上来,还得把四百亩的晚稻种下去。最苦、最累的时候也是挣工分最多的时候,一个“双抢”下来挣的工分抵平时半年挣的,所以谁都不肯放弃。需要的工具如“沙尖”(一种锯齿状,形如弯月的镰刀)、种田绳、谷箩、篾垫、电动脱粒机等一应物什都准备俱全了。
人呢?也得做点准备,要补一下,以便有足够旺盛的精力和结实的身板来对付这二十多天的苦战。最方便的就是红豆熬白木耳汤,还有酒冲蛋。这说是补,实质是犒劳一下自己的嘴而已,让平时填满蔬菜、咸鱼的嘴,在这时散发点甜味和酒味。最奢侈的就数烧个“神仙鸡”了。取一只当年正月孵出养大的母鸡,约一斤多重,放血洗净。鸡肚里塞进香菇、茴香、葱姜等作料,放适量的油和酱油。用瓦甑倒扣在大铁锅里。这学问全在这烧火上。得用早稻草,一缕几根往灶肚里添火。这样烧出来的是文火。一般得花上个把小时鸡才能熟透。一开锅,屋里香气四溢,鸡身通黄透红,油光发亮,令人垂涎欲滴。这鸡吃起来也有讲究,得一个人一餐吃完了,不能与人分享。
割稻,包含割、脱粒、打草结、出谷箩、挑箩头、晾晒这一系列的过程,其中没一样是轻松的活。最累、最重的活是挑箩头。两箩筐刚从水田里脱粒的稻子,起码在两百斤以上,田畈离晒谷场有两三里路。这样就需要接力般地把谷箩担往晒场上挑。那时每年二十多万斤的早稻就是这样一担一担被挑上晒场的。这活是所有正劳力轮着干的,你若干不了,就永远别想评上最高的工分。所以,那时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能挣到最高的工分,我也是当仁不让,轮到了就咬着牙挺着。
炎热的田野上没一丝遮掩,别说是树就是电线杆子也很少,唯一能与烈日对抗的就是头上的草帽。但是,也有好的去处,那就是输水的渠道。“双抢”期间正是大量用水的时候,渠道里时常奔流着欢快凉爽的水。在谷箩担还没传到我这儿的空隙,我就会全身浸在渠道里,只露出个顶着草帽的头,心里想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这样和烈日对抗着。现在每到夏季我是不敢挽起裤腿的,一挽起,腿肚上都是青筋暴绽形似蠕虫般的血管,好几次吓着过同事和朋友。这静脉曲张的病,就是那时一暴热一暴冷落下的。
四十多年了,现在“双抢”的概念淡化了很多,收割在不少地方都已经机械化了,插秧也改为抛秧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都涌到了城市。坐在安着空调的办公室里,那一段岁月时不时会凸现出来。虽然,很苦,甚至还有点凄惨,但是,我还是有点留恋。毕竟我在那儿生活了五年多,劳作了五年多,在那儿踏入了社会,在那儿开始领略人生的风风雨雨、冷冷暖暖、善善恶恶……在那儿我留下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段——青春。所以,现在每每看到有些年轻人穿着名牌,吃着哈根达斯,哼着流行歌曲,还在那儿嚷嚷着寂寞啊、痛苦啊、无聊啊、人生太没劲了啊,我就想大喝一声:你种田去,耘田去,割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