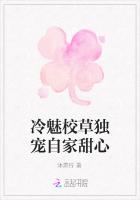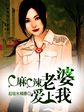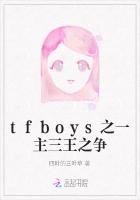谁没有记忆?然而谁的记忆如一个记者那样是连绵不断的节?
我的记忆源头是威尼斯。16世纪的时候,那里是欧洲的经济中心,是一个商业活动非常频繁的热闹都市。在这个日日如过节一般的商业都市里,各地来的商旅人士迫切需要了解和掌握关系其切身利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于是乎,当地很快便涌现出一批“专业人士”,他们专门采集有关政治事件、物价行情或船舶起航等方面的消息,或以单篇新闻的形式出售,或印成“报纸”沿街叫卖。后来,在《欧洲新闻史》上,这些专事采集和出卖新闻为生的“专业人士”,就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记者”。我记得,当我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看到有关“记者的来历”这个说法的时候,自身还离“记者”这个职业有着千里万里之遥。当时,在西双版纳密林的一座茅草屋里,几乎所有的知青伙伴都对我“就是想去‘威尼斯’”的宏愿报以哈哈大笑。而我自己,在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以后,至今还珍视那一天的“宏愿”为一个神秘的仪式,那是一个我永远难忘的节,“威尼斯”节。
最初,根据个人兴趣,我选择做一名文艺记者。记得我生平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如今已名满天下的史铁生,当时他还是一颗“新星”,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作《青年作家史铁生访问记》。其实,那仅是个副题,文章的主题是《每一条路上都有鲜花》。不知这个根据采访内容自然生成的题目有些什么魔力,抑或是“史铁生精神”真正感动了我,很快地,命运便呼唤我进入一个全然无知却又分明更具时代特色的新闻领域,即专门为一个新兴阶层服务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很快,“需要”一下子战胜了“兴趣”,我毫不迟疑地转向了。莫非真是“每一条路上都有鲜花”?
是的,这是肯定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命运攸关的一刻,应该被总结为我的“转向”节。它是我记者生涯的成人礼。尽管在生理年龄上,我是新闻这道门槛前的迟来者,但在新闻年龄上,我的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这个早熟的孩子的确经历了一个波澜不兴的“转向”节。
一眨眼的工夫,不仅和“中国企业家”打交道,而且和“环球企业家”打交道,在中国新闻界这个特殊的制高点上,我已经辗转腾挪了近20年之久。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20世纪90年代初应该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我服务于经济日报主办(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前身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也曾是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见证了改革开放中这个重要阶层从无到有的兴起和发展;在此之后,我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先由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后改为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环球企业家》杂志,推动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走向世界的这一历史进程。而无论自己在这两个杂志中的哪一个工作期间,作为一名记者,我都能够从自己的采访对象身上获得很多启迪和快乐。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我的记忆中真是有很多沉甸甸的节日……
例如鲁冠球,这个中国企业家中引人注目的常青树,早在中国厂长(经理)工作研究会评选的第一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就有他的大名了,而至今无论是在胡润榜还是福布斯榜或其他任何相关榜单中,还总能看到他名列其中。而这一点,早在19年前,即1987年11月26日于贵州铝厂会议厅的休息室里,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就颇有预感了。他的确是一个思维极其敏捷、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独特人物。不但回答记者的问题简练、精到,而且魅力独具、睿智无比,例如当我问到“‘枪打出头鸟’这句话,你个人有何体会?”他竟然脱口而答:“你要飞得再高点儿,他就打不着了。”这句答语当时令我惊异,至今仍然令我回味无穷。它也可谓是我的记者生涯中绵延不断的一个“节”了。不是“一字师”节,而是“一句师”节。
而像鲁冠球这样的采访对象,在漫长的记者生涯中,我自然还经历过很多很多。最近,作为《环球企业家》杂志主编,有幸被邀请担任《中国企业家》举办的“2006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排行榜”专家评委之一。当我在115位优秀的候选人名单中精挑细选并最后认定自己心目中的25位当选人物的时候,也曾信笔在他们中的一些名字的旁边写下自己的短评,如,张瑞敏:没有他,哪里有“中国制造”?如,柳传志:一个最可能成为“环球企业家”的中国人,等等。
我为当代中国有这样优秀的人物倍感自豪。我为自己作为一名记者曾经与他们“面对面”而至今如沐春风。
在记忆中,那就是我一个又一个的“记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