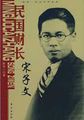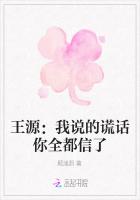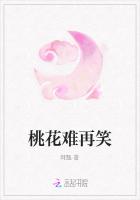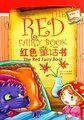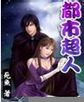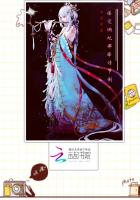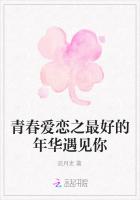170岁?这怎么可能?
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小学时的最后一位班主任王乐行老师,他今年已经87岁了;另一位也是我们小学时的老师李茂春,他曾经教过我们自然、美术、音乐、体育等数门课程,今年已经83岁了。这二位老师的年龄相加,正好170岁,你说对不对?
其实,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与这两位老师相聚的时候,郭启林、童道宁、高延昌、朱扬乙、时运龄和我,一共6个人,也都不小了:每人60岁,“六六三十六”,一共是360岁,再加上两位老师的170岁,我们这次相聚的八位师生的年龄总数,已经超过了500岁!
我们怎能不说起“500年前的孙悟空”?
那时候……
要说“那时候”话可就长了,还是先说“这时候”吧—
“这时候”应该从4年前说起。有一次我路过小学同学陈燕骥家的那条胡同,“沧海桑田,不知他还在不在”,心里这样想着,双脚已然进其院而步至了他家屋前。这里我曾来过,没想到这一次陈燕骥还真的不在。好在他的隔壁邻居告诉我,这屋子还是他的房,只不过他早已住到别处去了。但他有时候还回来看看。
就这么一线生机,陈燕骥就来了电话。那是一个热线电话。我们在电话中凑集了各自保有多年联系的小学同学邵云、刘雪新等一共8个人,并很快地在朱扬乙家“沧海桑田喜相逢”了。沙发还没有坐暖,我们情不自禁又不约而同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群策群力争取找到更多的小学同学。大家首先开始一个一个地仔细回忆那些我们曾经非常非常熟悉的可爱的名字:刘兴禄、胡玉明、李玉光、袁绍强、刘纪新、王凤彩、王小锁、张燕立、李千、戚志光、戚志民、曹秀峰、何世忠、杨小华、孙安平、杨永乐、刘君蔷、王宝珍、徐思伦、杜桂春、丁伟华、殷培良、黄洁、张小广、曹有光、李爱民、刘秀华、任淑兰、康淑兰、邱向台、王兆凤、徐成桐……
真是奇迹!沧海桑田又怎抵得上刻骨铭心?一个个尘封的名字就这样激流般奔泻而出,令人不由得想到泰戈尔曾经说过:“河流唱着歌很快地流去,冲破所有的堤防。但是山峰却留在那里,忆念着,满怀依依之情。”庄生梦蝶,我们是“山峰”?抑或“山峰”是我们那纯真无比的少年时代?
可悲的是,那一晚我们的“四处出击”竟“无一斩获”。当我们置身在曾经的小学校附近曾经的一个又一个小学同学家的院子里时,遭际的几乎都是一问三不知。更有一些同学居家的胡同或院落,早已被拆掉了,如今正可谓“世上新人换旧人,旧人惟有故人寻”了。但我们仍然未减“寻找”的执着,只不过人生至此,我们心里都隐隐地知道,我们不仅是在寻找过去的影子,其实也是在寻找我们尚很漫长的未来。
我们决定到北海五龙亭去玩儿。“让我们荡起双桨”自然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最回味无穷的歌声。但当我们在北海岸边的绿椅子上又一次吟唱起这首“永远的歌曲”的时候,又怎能不想起曾经带我们这些“小孩儿”到这里春游或“过队日”的老师们?
由此引发了我们与王乐行和李茂春两位老师的第一次相聚。那是2004年春天,我们从北海五龙亭出发,直奔王老师当时所住的雍和宫南侧柏林寺街而去,这是我们时隔很多很多年以后又一次见到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欣喜连连自不必说。看到王老师身体尚健,我们又携王老师一起去看李老师。二位老师彼此也有很长时间未见面了,我们大家相见甚欢。然后,我们请二位老师一起去吃地坛南门的“金鼎轩”……
王乐行老师不仅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在人生道路上“从文”的第一位恩师。20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记述王老师当年曾经给过我许多阳光雨露的散文,发表在1985年9月11日北京日报上。当时也曾想过把这篇文章寄予王老师看,但不知他的地址,又由于工作较忙,便搁置了。没想到这一次在王老师的家里,竟然见到了我那篇文章的放大样儿!原来王老师的一位亲友,当年不知怎样读到了这篇文章,并复印大了一篇给王老师看。王老师自然认得他的姓名并对我有所印象,于是“珍藏”我曾写的这篇文章一直到今天。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后来我也曾想过好几次,这也许就是“天注定”的一种缘吧,因为我至今也还珍藏着将近50年以前王老师曾经给我批改过的作文本呢!在那个纸页原本粗糙、册页有些泛黄的16开作文本里,王老师的任何批阅都是一丝不苟的,连删你的句子都是必用木尺比着画的,而且一定是用红钢笔水横着、等距离地、平行地画两道,而且这两红道绝不会画得一长一短。他这种“从文”的认真态度和“敬畏”精神,浸润于我少年时代纯净的眼与空荡的心中,并在漫长的岁月里发芽、成长,以至于最终成就了一个“编审”的文字生涯。其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王老师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人格魅力。例如在我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写的一篇作文之后,他的批语是这样的:“想想,重点要放在哪儿?怎样分段?我相信,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将近50年过后,每当我看到王老师当年曾经给我这个12岁的孩子写过的这两行批语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会感到身上暖融融的,心里热乎乎的。要知道我小学时的作文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而那篇作文却仅仅得了75分!而就在这罕见的“问题”面前,王老师的“(你)想想”和“我相信”是多么不同凡响啊!而这种不同凡响,又怎能不在我漫长的人生路上余音绕梁?
这就是与两位老师又一次相聚时,至今留给我的最主要感慨。第二次相聚是2005年的春天,王老师已搬家至朝阳区农光里附近,我们同往他家拜贺,并在他的新居合影留念。又一个春天来到了,2006年我们第三次相聚,地点就在离王老师家不远的“大鸭梨”。这次相聚最令人欣喜的是又多了一位小学同学张燕立。而近几年中,邵云曾通过派出所,时运龄深入几个单位,朱扬乙也曾知会外地亲友,等等,我们的“相聚”队伍还是很难再扩大。真是太难了,斗转星移,或物是人非,或物非而人渺。亲爱的小学同学们,你们若有幸看到这篇文章,请一定与我们联系啊!1960年毕业于北京市东城区十一条小学的老朋友们盼着你们归队哪!
真是年年难聚年年聚。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与春天一起,又一次相聚于王老师家附近的“大鸭梨”。别看敬爱的王老师已经87岁了,我在电话中问他还能不能上“大鸭梨”那高台阶,他的回答是“没问题”。至于已经83岁高龄的李老师,自然又是他的得意门生童道宁亲自上门把他接来的。在我们的共同记忆中,教音乐的李老师曾经造就了童道宁小时候的一段“歌星”生涯,至今道宁家里还珍藏着他那时候灌制的木纹唱片呢。
人的一生中真是有很多的小事情或小细节,只能与特定的一部分人共享。而这些特定的人士中,首推家人,其次就是老师了。当然还有我们各个时期不断变化的好朋友们。在前不久与两位共170岁的老师相聚中,同学们纷纷对我的上述感慨表示认同,童道宁并且说道:“能够与大家共享我生命中曾经有过的一段快乐时光,真是三生有幸!”
郭启林则进一步提议:“让我们共享王老师和李老师的身体永远健康!”
余音绕梁。又是一年春草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