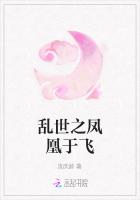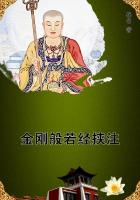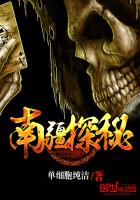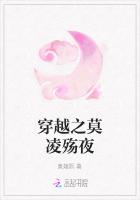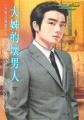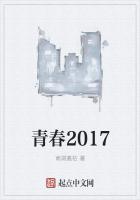—《忆娘》赏析
即使是尚在学龄的少年朋友们,也常常会有一些涌上心头的人和事,需要写成回忆性的文章。王宗仁《忆娘》这篇散文,在“忆”的手法上颇多可取之处。
既是“忆”,就存在一个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时空跳跃问题。这可谓写回忆性散文劈头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忆娘》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开篇就是一比,“有如一朵心绪缠绵的云”—这样,作者就贴切地获得了“又飞向远方”的自由。紧接着,“我离开故乡已经二十多年了”—一下子切近正题。然后是另起一段对“生我养我的地方”的一些真切描绘。由远及近的空间之“隔”就这样了若无痕地被作者“处理”掉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如此高超的“忆”的手法。
作者对时间之“隔”的处理手法也是耐人寻味的。“真怪,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常常想娘”,这是刚化入又淡出,为全文之忆一波三折的最初之点。当作者进一步回忆娘为他缝补衣裳时,“嘴里还哼着一支古老的曲调—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觉得那曲调是从遥远的山那边传过来似的”。可别小看这两句当中的那个“破折号”,它实在是作者“由彼而此”的一绝!谁能从中注意到时间之“隔”呢?但语意又分明是从“二十多年前”到“现在”的一转。这里的“破折号”好比是盛载着作者真挚、深厚情感的一座小桥,使读者很容易地就从彼岸而通达了此岸。再往下,“娘那时候”如何如何,“这一天”怎样怎样,我们又不知不觉地跟随作者回到“娘”的身边去了。当我们正为娘“突然转身擦抹眼泪”而动情不已的时候,“当时我八岁”又一下子使我们置身到今天,并且“一直到今天”地“忆娘”不已……
这种时空的跳跃是写回忆性散文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功,实际上它也是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在《忆娘》中,作者还有这样一些艺术手法值得我们借鉴:
置自己所忆对象于一个特定的氛围,以增强忆念形象的立体感。文中对“生我养我的地方”的种种叙说,既是“忆”的凭借物,又是对忆念对象的艺术铺垫。
注意“忆”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适度。《忆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对老母亲的忆念,但具体“忆”的内容是“二十多年”以前的,所以在作者笔下,“娘那时候并不算高龄”以及“在我们村的娃娃世界里”的种种描绘,都非常符合当时的母子关系,也当然吻合现在的忆念之情。
紧紧把握住“忆”的线索,绝不旁逸斜出。忆亲娘,集中在娘的缝补上。“我想娘,总是跟那个线团连在一起,当然,还有牵在线头上的那根明晃晃的针。”作者是这样宣告的,读罢全篇,也深感《忆娘》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其他如情蕴于“忆”,熔载有致,篇末升华,等等,都是《忆娘》的成功之处。至于思想性,对于贫寒之娘的缝补之忆,谁又能掩卷而不沉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