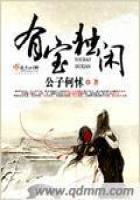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都能够跟残疾人有所接触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有幸的是,我最近读到一篇题名《矮子》的美国小说。这篇似乎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小说,不但吸引了我,而且强烈地震撼了我、深深地教育了我……
他出生在“侏儒”世家,“到马戏班子去挣钱是不堪回味的。这世界似乎没有我的一块栖身之地”。他深深地为自己的“矮”而感到痛苦,于是乎,他每天晚上都要来到海滨艺场,然后花一角钱悄然钻进路易斯变形房。这个变形房里有一块巨大的“哈哈镜”,他总是站在此镜面前,微闭双眼,舍不得睁开看。“瞧啊,他张开眼睛了,直瞪面前那块巨大的镜子。镜子里的映像使他欢喜不已。只见他先眨巴一下眼睛,然后踮起脚尖,接着侧身,扬手,前鞠,最后笨拙地跳了几步舞。大镜里则相应映照一个眨着大眼迈着巨大舞步的高大身躯和一双又细又长的胳膊,最后还有大大咧咧一鞠躬!”读至此处,我不知道自己是喜还是悲,只觉心中一热,潸然泪下。但还有比“矮子”的“幻乐”更令人难以品透的滋味儿:有一天,这面能把“侏儒”变成“巨人”的“哈哈镜”被换掉了。在新镜子面前,个子大的人都会变得极其渺小,“天哪,何况一个矮子,一个小矮子,一个黑矮子,一个蹒跚而孤独的矮子呢?”一阵惨叫,又一阵惨叫,又一阵惨叫……
偷偷把镜子换了的人,就是这个变形房的售票员拉尔夫·班哈特。他这种对待残疾人的“恶作剧”态度实在令人深恶痛绝。岂止是唯此一“恶”而已?他早就扬言“可以把他逗得转圈儿”,还“装作傻乎乎”地跟“矮子”说话,甚至骂“矮子是细胞养的,矮子是松子儿”……在健康人应该如何对待残疾人方面,这个“虐待狂”实在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员!面对此公,谁能不变得更惊醒、更善良一些呢?
美国虽然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但除了有耐人咀嚼的“矮子”心态,除了有令人切齿的“虐待狂”以外,也还有“让我们互相理解”的楷模英范客观存在。她,就是这个海滨游艺场的另一个工作人员—爱弥。虽然明知其为小说人物不足为凭,但读着、读着,我还是为她对待“矮子”的善良态度深深打动了。当她发现“矮子”的“幻乐”以后,不但“双眼涌出了泪水”,而且对拉尔夫说道:“我强烈地爱上他了。”这种“爱”,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啊!正是基于这种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类之“爱”,爱弥竟然发现了“矮子”比格先生原来是一个作家,并且十分肯定又富有哲理地对拉尔夫说:“无论你我还是这码头边的其余任何人都永远不会变成他那样的人。这真荒唐,真荒唐。生活注定他虽然活在人间,却只能当马戏演员。生活虽然没有迫使我们去演马戏,而我们却待在海滨的这个游乐场里。两者似乎相距千里,这是怎么回事,拉尔夫?我们具有的只是身体,他具有的却是头脑,他思索的东西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出来啊!”爱弥的这番肺腑之言,不但表述了她对“矮子”作家的崇敬与热爱,而且体现了她对人生价值一种成熟而可取的看法:健康人与残疾人因生理上的差异享受生活恩赐固然有多寡之分,但其对社会的贡献也许恰成反比,难道这不是有目共睹的某些客观事实吗?“矮子”就是这些“事实”中的一个,爱弥对他的理解不仅是口头上的,而且非常有闪光的行动:她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一面“矮子”所需要的那种镜子(他需要的真是“镜子”吗?这真是作者妙不可言的一喻),准备送给他,并且美好地祝愿他:“日复一日,甚至在春寒料峭的黎明时分,你都可以悄然起身,对着这块明亮的大镜子举手伸足,欣然欢笑,独自欣赏自己那魁伟的身躯。”但可惜的是,爱弥的镜子还没有送到,“虐待狂”的偷换之镜却令比格先生“狂怒地蹦跳起来,神经质地号叫着,啜泣着,泪渍满面,嘴巴大张。他闯进万点萤火的夜幕里,愤怒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一边恸哭,一边朝海堤奔跑”……
这是一个“美国的悲剧”吗?不,它对我们这个社会里健康人与残疾人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有丰富而生动的借鉴意义。尽管它出自美国现代作家雷·布雷德佰百之手,但我衷心地希望,每一个有幸看到这篇小说的人,都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篇小说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