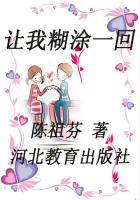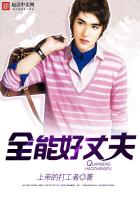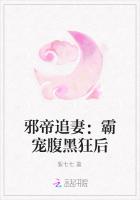一
戏冠全国的北京人艺,最近又在其“小剧场”里上演了鲁迅先生的《过客》。以我之孤陋寡闻,犹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文艺》上,曾刊有山东作家肖平的一个短篇,题目是《墓场与鲜花》,内容是描述两个男女主人公在“文革”前后的人生际遇,特点是故事中始终有鲁迅先生的《过客》相联串。当时我曾为这篇小说鲜明的特色、深刻的内涵所倾倒,后来也曾注意到它被评上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再往前追溯,1939年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的时候,抗敌协会剧协曾把《过客》化装演出,胡风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过客小释》;1940年8月,香港文化界召开鲁迅60诞辰纪念大会,并于即日晚演出了《过客》。
从以上数十年间的片段事实,我们可以集中为这样一种认识:鲁迅先生的《过客》,不仅是其全部译著中唯一可以上演的作品,而且成了深邃的中国社会舞台上颇为人民所珍爱的一个保留剧目了。
二
其实,《过客》不过是几千字的一个小诗剧。
说它是“诗剧”,它又明显地没有歌德的《浮士德》或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那种分行的形式或韵白,所以,若准确名之,《过客》其实是一个散文诗剧。所谓小诗剧,不过是一种不严格的习称。
或谓:鲁迅的《过客》是一种“短剧体的散文诗”。
即使在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于我们的文学体裁研究者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问题。
但我们应对鲁迅先生的这一发明创造采取“拿来主义”则是毫无疑问的。
三
从《过客》中我们可以幽深地感受到,“短剧体散文诗”表面上是剧、文、诗三位一体,其合理的内核仍然是一颗诗魂。
这颗浓郁的诗魂,在《过客》中是采取象征主义的手法来表现的。
所谓象征主义,一般均以法国波德莱尔于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为始祖,它主要地是一个诗歌流派。
鲁迅的《过客》师承欧洲象征主义,但又摒弃了波氏等人的颓废与神秘。他把寓意深远的象征方法和入木三分的现实描绘完美地结合起来,独创了一种中国式的象征主义,并且由诗而至“短剧体的散文诗”,极大地拓展了象征主义的新边疆。
这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一种表现方法上的突破。
四
《过客》中的环境,最是常言所说之典型环境:黄昏,杂树和瓦砾,荒凉破败的丛莽,小土屋,一段枯树枝,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这固然是旧中国腐败凄凉之社会环境的艺术写照,又何尝不是人之生命长途中都会遇到的艰窘时刻的逼真象征。
创造典型环境是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的。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描给我们的三个人物,都可谓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个口口声声“太阳下去了”的“老翁”,只知“前面是坟”,认为“不如回转去”,他显然是一个在人生的坎坷处失却斗志,悲观厌世者。而那个约三四十岁(人到中年)的“过客”,尽管“走得渴极了”,却只知道“前面”,誓言“我不回转去”,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勇于韧性战斗、奋然而前行的强者形象啊!至于那个“约十岁”的“小女孩”(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只知道前面“有许许多多野百合,野蔷薇”,其纯真催人泪下,又颇令每一个趋向成熟的读者感到揪心。这是一个满怀希望、向往光明的新人的象征,富有深入髓骨的艺术感召力。
三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还在走着人生的长途。鲁迅先生的神来之笔,一直让他们走进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中:是学习“过客”负重而前行,还是首肯“老翁”的“夕阳咏叹调”?抑或是满足于“女孩”那种“鲜花”般的梦幻?
回答,回答!每一个认真看完《过客》的人都要作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负责任的回答—
这就是鲁迅先生作为“人类灵魂的考问者”的权威之所在。
五
不仅如此。“奋然而前行”的“过客”,其实也有自己生命的另一面:
他“眼光阴沉”(加重号系笔者所示)并没有闪着明亮的光,这不仅是来路之黑暗所使然,而且昭告着他对自己未来的善恶并不肯定。
的确,他“从东面的杂树间跄踉走出”之后,曾经“暂时踌躇”;他也曾对“老翁”所说“料不定可能走完”有所“沉思”;也曾对“老翁”的“休息”劝告“默想,但忽然惊醒,倾听”—并诚实地宣告:“我愿意休息。”
对于小女孩给的“布”,他也曾“颓唐地退后”,这只能解释为他当时对于实现稚嫩者的期望尚无把握,深恐自己挑不起这一副人生的重担。最后:“过客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
“闯”,固然是“奋然而前行”了,但尚有“夜色跟在他后面”—“阴沉”,这又是一种“阴沉的目光”!
但正因为尚有这种“阴沉”,“过客”之奋然而前行才更有意义,也才更加真实可信。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曾经说过:“出自内心的,也就能进入内心。”
这就是《过客》之所以能够深入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艺术力量之所在。
六
《过客》写于1925年3月2日。当时的鲁迅先生,思想上正经历着一个大飞跃前的苦闷时期。这一点,正如冯雪峰同志后来在1949年4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流露了鲁迅的虚无感和阴冷心境最厉害的,莫如他的散文诗集《野草》。”
的确,《野草》中的《过客》,主要反映了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流露出存在于当时作者思想里的同样的冲突。当时的鲁迅先生,一方面感到了黑暗势力的浓重,着力地描绘了它;另一方面又觉到战斗不能松懈,坚持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鲁迅先生自己在1925年4月11日(即《过客》写完一个多月时)致赵其文的信中曾经说过: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是的,《过客》是一曲悲壮的战歌。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过客”将永远鼓舞我们更勇猛地向前,去谱写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