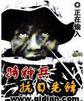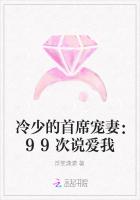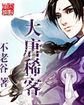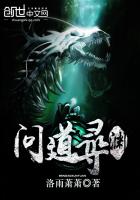这所全球最大的藏书库,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这里的每台资料信息储存与检索装置,可容纳100张光磁盘,每张磁盘中储存的信息,相当于10000页印刷品的内容。任何人只要能辨认字母和按动打字机键盘,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出所需要的东西。光磁盘只有激光束触及,从而使资料免于千百双人手造成的磨损。这种机器还能将阅完的文献放回原处,避免了任何图书馆都感到头疼的“丢书”问题。
国会图书馆与国会大厦之间,连接着一条长达330米的传送管道,以加快图书的传递。图书馆的电脑网络使每位议员,在办公室里使用一个终端来接收信息。美国国会图书馆没有采用一般图书馆的借书证或阅览证制度,它对所有的人开放。他们认为国会图书馆不仅仅为立法机关服务,而且要为选举国会议员的公民们服务。
流连伦敦图书馆
陈原
我到伦敦是6月下旬。夜间八九点钟还像白天似的光亮,不冷也不热。英国朋友说,这是英国少有的迷人的夏日-这些天竟然没有下雨。我记得艺术家茹可夫有一幅钢笔画-《英国博物馆》:背景是博物馆的正厅和侧厅,前景则是博物馆前面空旷的广场。湿濡濡的天气,戴着高筒礼帽,穿了燕尾服,拿着“士的克”的绅士们,以及穿着婆娑的长裙,打着雨伞的女士们……如今我到了这幅画中的境界,还是我们在图画中看惯了的那一座古老建筑,还是正面那几根罗马柱,还是屋檐下的一些希腊式浮雕。不过昨天没有下雨,没有看见打开着的雨伞,也没有高筒帽和燕尾服或长裙---这些英国绅士淑女的服式似乎随着世纪的推移,也进了博物馆了。广场围了铁栏杆,两边进口处都有一块刻着“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两个名字的铜招牌,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大英博物馆”。
图书馆从博物馆分出来,那是1973年7月的事。图书馆独立扩展,主要是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我本来以为英国人是很保守的,但图书馆独立这桩事却打破了我的成见。我去了著名的圆形阅览厅,这就是马克思当年常去的地方。这个圆形阅览厅是1857年落成的,到现在已一百多年了。阅览厅作为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建造的时候,正是这个老大帝国的黄金时代。殖民主义者到处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这个阅览厅却保存了很多血泪斑斑的历史文献。这座建筑物的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取光是自然光,光线从很高的圆屋顶下四周巨大的玻璃窗透进来,很大面积的阅览场所都显得十分明亮。屋子周围是三层楼书架,每一层都从地板竖立到屋顶。一进此室,便如入“书林”,确乎是壮观得很。据说书架一层一层连接起来共长60英里,那就是说约近100公里,几乎等于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沿着周围的书架“伸出”了一条又一条的长书桌,书桌是一个座位接一个座位的,据说总共有600个座位,也就是说同时可以接纳600个来此做学问的人-介绍说,每天平均要查找2500种书。我想,书架上陈列的各种工具书,各国百科全书,以及常用的重要参考书,当然随便翻阅,所谓查找2500种书,想必是通过圆形阅览厅中心服务台借来的。
进入这个圆形阅览厅,要申请一种特别阅览证。马克思和列宁当年都申请过,N先生把他们的申请书复印件拿给我们看,马克思的签字就是我们在典籍上常见的那个签字,不过列宁用的是假名,看不到我们熟悉的签名式。列宁来此是1902-1903年,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半时间就花在这个阅览厅里。N先生领着我们穿过“书林”,去看马克思当年经常在那里工作的座位(据说不止一个)。曾听说马克思脚下的地板也磨损了好几寸,但这传说可惜没被证实,也许地板已经修补过,而且铺上有吸音功能的化纤地毯了。
这个圆形阅览厅,实在令我倾倒。我真想在这里流连几小时,几天,乃至几个星期,查找一些近代史上我们本来就没有,或可能已经散失的资料。可惜不行。那只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了。那天,我看见三三五五的研究者,错落地坐在那里用功,没有满座。特别使我倾倒的是,偌大的一个阅览厅,竟然鸦雀无声:没有说话声(虽则有时一两个人交头接耳),没有打电话声(虽则中心服务台常有人在打电话),没有脚步声(虽则不时有人到3层楼高的书架上去翻书),更没有斥责声和咒骂声,没有我们常常碰到的嗡嗡声(不知什么声响)。这叫做图书馆。这叫做研究室。这叫做工作。到此一游,你才体会到看书是个什么气氛,你才体会到马克思和列宁如何善于利用这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图书馆,检出它所珍藏着的一切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写下了打烂资本主义世界的“指南”。
无需乎引用数字来证明这里藏书的丰富,平常人对抽象的数字很难引起具体的形象,我只想说这个图书馆在独立以后,有一个大变化,那就是增加了电子计算机设备。特别是查找现代科学资料,只要家里有电话,有终端机,便可以通过计算机中心取得你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当然要付钱,并非“无偿服务”。
最现代化的图书馆
吴岳添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1988年的这一天,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希望建设一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大型图书馆。法国到底是个文化大国,一声令下,有关部门闻风而动。时过七年,由建筑师多米尼克·佩洛设计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便大功告成。该馆楼层面积达38万平方米,供读者使用的书架长度为30公里,藏书量为1200万册。其规模为世界第二,而现代化程度则居世界第一。
1995年3月,密特朗总统主持了新馆的落成仪式。目前正在进行内装修,另外从原来在黎世留街的旧址迁入新馆用了半年时间,现已于1997年初向公众开放。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是巴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让·法维埃。
他发表过《美男子菲力普》、《弗朗索瓦·维庸》、《百年战争》和《中世纪辞典》等二十多种著作,从1975年起任法国档案馆馆长,1994年1月18日被任命为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由于人们对建设这样一个图书馆有些疑虑,他特地让法国《读书》杂志的记者提前进馆参观,并回答了有关的问题。
新馆的设计以方便读者和环境舒适为原则,四座巨大的藏书楼状如四本打开的大书,矗立于塞纳河畔,可谓别具匠心。四座高楼的中央是一个大花园,栽有250棵大树,其中一些欧洲赤松已高达30米。为了保持环境的安静和卫生,花园不向公众开放。不过为了方便公众的游览,在塞纳河上架一座桥梁,把图书馆与河对岸的贝西公园连接起来。
新馆由藏书楼和底楼组成。底楼又分为底层和上层(即二楼)。
底层是供研究者使用的,分为五个部分:哲学、历史和人文科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录音录像(视听设备)。有人担心研究者们在底层是否会像在“洞底”那样感到气闷,其实完全是多虑。因为底层正对花园和塞纳河,不仅视野开阔,而且景色宜人。上层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馆,沿着通向花园的走廊走到尽头的展览厅、音乐厅和商店。但是第一次进阅览室时要登记,以后每年登记一次。登记后领取一张磁卡,一年内可以免费进入阅览室。登记者应年满18岁,不过16岁的中学毕业生可以例外。普通读者如有正当理由,也可凭临时证明到底层去取书。
馆内全部采用信息系统进行管理。阅览室内放有电脑,读者不用跑来跑去查书目卡片。外地读者把自己的微机和图书馆的网络联接起来后,只要在微机上打出自己的名字、磁卡号、以及所借书名和借阅日期,他一下飞机或火车就可以直接去图书馆,坐在为他保留的座位上看他要借的书。法国国家图书馆拥有法国的全部藏书,法国各地还有不少图书馆藏有各种外国书籍。为了方便读者,新馆和国内外的50多个图书馆实行联网,读者立刻就能知道在法国有没有他要借的书,如果没有,还可以查询哈佛、华盛顿和法兰克福等著名图书馆,以便复印。
法国国家图书馆原来在黎世留街,现在馆内的手稿、版画、照片、钱币、奖章、地图等将仍留原处,书籍则在开馆前半年陆续运入新馆。从底层书库装起,随着每年的进书逐渐升高楼层,估计将在2045年时装满四个藏书楼。有些人担心大楼的玻璃会透进阳光,使图书受热变形,其实这里的保护措施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图书馆。书与外层玻璃窗之间隔着好几层木板和玻璃,每一个夹层之间都有空气流通。珍本善本更是放在中二楼内加以特殊保护,有专门的空调和防护设备,需凭证明才能借阅。为了以防万一,新馆还采用缩微胶卷和缩微照片等先进技术来保存图书,做到万无一失。
新馆把木材、玻璃和钢材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看起来犹如一件艺术品。新馆建成后为了维持运转,国家仍需要投入巨资,据说每年将高达十亿法郎。新馆的设计使用寿命为三个世纪,有人以为电子出版物等高科技产品将取代图书,因此不再需要图书馆了。法维埃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家里有许多好唱片,可是他依然常去听音乐会,不能认为将来人们在家里可以用电脑办理一切,就再也不用出门了。
牛津图书馆掠影
许达然
街在牛津有些已被近代挤成巷了,名字却仍不肯改,仍错杂着熙攘,蜿蜒着幽静。从街的熙攘走入巷的幽静仿佛浏览古典散文,无节奏却协调,无韵律却隽永,还常碰到历史典故。
三十五个学院的历史组成牛津大学的现在。过去它如一个用来自各地的石头所砌成的矛盾拱门,以人文与理性两柱扛着宗教站了六百多年了。门上“承溜石雕”悬挂着哥德式的恐怖以及小天使的温和微笑。笑靥天真爬满皱纹,有翅膀的飞不上去,捧书的总待在那里,读得脸黑嘴哑了,蒙的眼神仍瞥向街巷与学院。
踱进学院,拥来一园清静,草坪惹人踯躅。自十三世纪以来,各时代的校舍倒了又建,矗立着黄灰石的庄严。过去破了补上现在,贴染着时间的泼墨,剥蚀竟如明瓷的细纹展显不裂的典雅,而意味更在图书馆里,在拉德克利夫阅览馆和博得廉图书馆内的韩福瑞阅览室,我虽花不少时间仍得不到什么结果,但因不觉得是浪费生命,居然还开心。在十四世纪创立的默通学院图书馆,看不懂用铁链牵住的书,竟也磨了一个下午,荒唐只为些盎然古意。
意古而又堂皇的是各学院的教堂。教堂塔尖虽总让我觉得是飞不了的秀丽,不如烟囱可传播些成灰的消息,但我仍常忍不住进去,看斑斓的玻璃窗筛出阳光的装潢,辉映着破碎的统一,衬托奢华的虔诚。然而这幽闭也使我感到阴凉,怀疑神祝福窘困的人。记得雪莱有两行诗说生命像彩色玻璃圆顶,污染永恒的闪烁。或许我不相信永恒,总认为窗玻璃的诡谲搅乱光明,骚扰冥想。不宁静的似乎是思索者。有时我也坐下,无神可拜,就想些俗事。晚间我偶尔去基督会学院、新学院、茂得兰学院或皇后学院的教堂听音乐。但听他们起劲地奏管风琴,简直要唤醒中古与文艺复兴才罢休,只是再逼真都无法把历史译成现在了。
然而历史仍投影街巷。历史里有传统。传统有些如老树已蛀,他们还膜拜,希望虫死,死抱传统惩罚抗议者。主张主权在民的洛克就曾在1684年由国王下令解除教职。甚至在十八世纪牛津还是一个“中古”的大学。各学院坚持各自中古的利益,虽有科学教席,却忽略科学教育,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医学教授才只有四个学生。现在还矜持的传统有些无非古怪的古俗,例如学院餐厅在一群画像凝视下用拉丁文祈祷后吃饭时还有人服务,久了居然不觉别扭。例如连王子都不许把书借出博得廉图书馆,馆内书目不是印在卡片上而是贴在本子上,有的已脱落了。
美国社区图书馆的感受
潘非
我于1989年、1991年、1995年三次去美国探亲,看望我最小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陈平和庞静。前两次我住在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州大学城(庞静在宾大读书),第三次去是住在西海岸洛杉矶的一个名叫南帕萨迪那的小城(陈平在洛杉矶工作)。这个小城只有23000多人口。我闲住无事,便经常步行去这两个小城的图书馆,很方便,阅读中文的报刊杂志,借些学习英语的录音带以及中文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回家看。渐渐地,图书馆成了我旅居美国消磨时光的好朋友。回国以后,我还常常对朋友们称赞美国这种小型图书馆好。就拿洛杉矶的南帕萨迪那公共图书馆来说,它规模不大,只是一所平房,但已有100年的历史,藏有英文、法文、中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中文的书籍不算少。还有录音带、录像带、电脑、复印机等,我感到它比较突出的优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