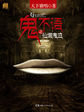那会儿在巷子口,闲汉银贵抽着福娃递给他的烟,耸着肩膀,斜视着他不断嘿嘿地笑。福娃不耐烦地问:“你笑鸡巴什么哩呢?”那闲汉分明看透了他的心事,故意拿他一把说:“难住了吧,把你福娃也难住了吧?你以为盖起一座一砖到顶的院子这辈子就消停了?想得太美了吧?老天爷让你有两个儿子,就是让你受两份罪。难住了吧?把你一天骄傲的,你骄傲什么呢?!”福娃无奈地嘿嘿两声。那闲汉越发得意了,卖个关子说:“也不白抽你的烟,我有办法让你不熬煎哩。”福娃不屑地说:“你有个球的办法,有办法你就不是这球样!”银贵也不生气,依旧嘿嘿嘿嘿地笑:“我要指给你一条路,你怎么谢我?”福娃“哈”一声说:“你看你这怂样子,你要真能,我摆一桌,和你喝一瓶!”那闲汉先看看两边没人,对福娃招招手,压低声音说:“你往跟前走走。”福娃不由附耳过去,只听闲汉那张臭嘴热气烘烘地说:“你不就是想卖几具棺材给老二娶媳妇嘛,你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把厦子底下那几具棺材敲敲,那东西是个老虎,能吃人?就有那该死的立马完蛋,你的棺材不就卖出去了?”
福娃赶紧瞅瞅两边,幸好没人,也压低声音说:“不能干这事吧,让人知道了还不骂死我?”银贵“啧”一声说:“你看你这人,这又不是害人,该死的活不了,这办法只是解决一下他死了用不用你棺材的问题。”福娃又递给他一支烟说:“我再想想,这话你可不敢跟第二个人说。”银贵嘿嘿笑着说:“我等着你请我喝酒哩。”
福娃把镰刀把举起来,可是敲不下去,他能看见那棺材板下面的确躺着一个人,那是谁呢?他看了门口一眼,那里没人,嘟囔了一句:“该死的活不了!”把心一横,瞪圆了眼,镰刀重重地敲击到眼前的棺材板上,发出空洞沉闷的回响,然后,他又接着在这具棺材上敲了两下。不知为什么,他有些毛骨悚然,只望了望另外的两具,终于没有去敲。他把镰刀挂回墙上,抱起玉米秸秆重新把那三具寿器盖好,走出厦屋,没有敢回头去望,甩开罗圈腿,慢慢踱到灶屋去烧水,准备沏一壶大叶茶来打发剩下来的白日时光。
一条巷子里的正元家的女子出嫁,二福也去帮忙。村子里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到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去帮忙,其实是帮闲,喝喝茶吃吃饭斗斗酒,捧个人场,干活的自然有那些年轻的。闲汉银贵嘴里常常淡出鸟来,盼着谁家有个事情,早早就赶去,拉条板凳,半拉瘦屁股坐板凳头上,跷起二郎腿,裤腿挽起老高,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那不抽白不抽的香烟。一边不时瞥一眼灶上,等着打牙祭,一边冷笑着打量这一圈的人,盘算着一会儿和谁斗酒以便多喝两杯。
貌似伟人的二福吸引了银贵的兴趣,那闲汉不说话,只是望着二福笑,他知道一会上了场,怎样用一句话戳到二福的疼处,让他来者不拒地把酒灌下肚去。银贵的主意是:只要有一个人喝多了,场就能晚散一会儿,最好喝到月偏西。
二福不知道闲汉在打他的主意,酒瓶子一开,起初大伙都会有一小会儿的腼腆,直到有个家伙平举着胳臂把酒杯伸到桌子中间大吼一声:“日他妈,喝一家伙!”这个人永远不是闲汉银贵,他的策略是暗里使劲,底下烧火。喝开后,银贵殷勤地给大家倒酒,他拿眼角瞅瞅二福说:“啧,正元不行,让喝这鸡巴便宜酒,大席都不敢上汾酒。”就有人反对:“喝你的吧,让你喝这也不错了,满桌子有能让喝起汾酒的主儿吗?”银贵马上说:“你忘了,二福家的艳出嫁的时候,二福让你喝的不是汾酒?”对手瞪起眼说:“胡球说,二福多会让喝汾酒了,别说艳出嫁的时候了,军娶媳妇的时候他已经倒灶了。”有那老实人诚恳地说:“早些年二福的确能行,这几年他不行了,他也‘二蛋’。艳出嫁的时候你喝他汾酒了?还不是喝的这个猫尿?”二福一直笑眯眯的,像个佛爷爷。银贵就把在座都扫了一眼,咕咕鬼笑:“看来我记错了。”
二福拿起酒瓶子,慢腾腾地说:“倒上。”
一群帮闲的父辈好容易散了场,更深露重,月光把树影投到东墙上,该死的猫头鹰不知在谁家的屋脊上鬼笑。闲汉银贵打着满足的嗝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村子深处走去,剩下几个人把不说话光打嘟噜的二福送到大门口,问道:“能行吗?用送你进去吗?”二福笑眯眯地摆摆手。但大伙还不放心,对着那亮灯的窗户大喊:“莲——”
莲和回娘家住的女子艳把沉重的二福扶回到床上躺下,艳拧着眉头埋怨:“闲得没事干,又喝多了!”出外屋看电视去了。莲没有力气给二福脱衣服,就那样给他盖上被子,问了一句:“有凉茶你喝吗?”二福笑笑,呼噜打雷一般响了起来。莲出来坐在女子身边看电视,咯咯地笑着说:“今晚我和你
一起睡,你爸别把我熏死!”艳盯着电视,含混地说:“我爸吧,真是的!”
八
莲做好了早饭,冲蹲在花池边上刷牙的女子喊:“叫你爸和你二哥起来洗脸吃饭。”艳含着牙刷喊:“爸——,二哥——,吃饭哩!”莲不满地骂道:“叫花子女子!”她亲自来到小儿子住的角屋,站在窗子外面喊:“海,海!”海烦躁地答应:“知道了!”莲骂道:“我把你个死娃娃!”她回到自己屋里,看到二福睡得很安详,就爬上床去把窗帘拉开,上午的阳光射进屋里来,莲借着光线看到二福的脸色有点发青,就一边嘟囔:“这死人怎么不打呼噜了?”一边往跟前凑,她怔了怔,怕烫似的用手掌尖碰了碰二福的脸,发现二福已经冷冰冰硬邦邦了。
第一个听见二福家哭喊的是福娃,他正站在厕所撒尿,抖了抖,尿了一裤子。福娃出来厕所沉着地对戳在那里的老婆说:“快到二福家看看怎么了。”两口子就往门外跑,孙子在后面追,福娃老婆回头说:“娃,娃你在家,奶奶一下就回来。”
二福死了。闲汉银贵宣布,那天在正元家喝的酒不太真,可能是工业酒精勾兑的,他也差点没死了。无论酒的真假,南无村的人得出一个结论:二福是喝死的。他们认为恓惶归恓惶,这总归是一个笑话。
二福死了,大伙要笑自然是笑话莲,婆娘们聚在二福家陪着莲哭天抹泪,比死了男人的还恓惶。这都不是装的,就算女人的心是硬的,她们的眼皮却总是软的,管不住自己的眼泪。可也有那偷偷把眼睛扫来扫去只管到处打量的,早在心里开始笑了,顾忌着场合不合适,硬是要装出和别人一样的善良来。这样的人不是不善良,是莲的冤家,婆娘尤其村槽里的婆娘,谁能没一两个冤家幸灾乐祸呢?只看那个子最大的婆娘叫俊的,高挑饱满,脸盘也还周正,只是眼白大黑珠小,嘴角老要撇来撇去沾着一点白唾沫。这是个会说笑的,即便儿子在外打工的时候强奸杀人被政府枪毙了,媳妇扔下娃娃跟人跑了,也还能泰然自若地坐在巷子口和人扇风,说我娃在南方太忙了,干的事情太重要了,好几年也没请一天假回来。又骂媳妇子脸皮太厚,跑到南方找自己男人去了,说出来可真够辱没人的哈哈。俊只把一村子的人当傻子,一村子的人只道瞒着她一个人,以至于她竟然从来没被别人戳破,还能掩耳盗铃地搜罗别人的笑话。
埋了二福,莲在巷子里和人说笑,嗓门听起来更大了,那些等着看她守活寡背后好讲笑话的婆娘,只能当面骂她:“没心肝的眉眼!”
真正成了笑话的是福娃,都在传说他敲棺材结果把亲弟弟敲死的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也不能认定这事情就是闲汉银贵讲出去的,南无村很有几个称得上“先知”的,更不乏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的“镜子”——可怜人总是依靠笑话别人的可怜来觉得自己活得还不赖。
装殓二福的寿器,正是福娃用镰刀把儿敲过三下的。但福娃认定二福是自己喝死的,迟早是要喝死的,和自己敲棺材没一点关系。但心里还是亏,半夜睡不着,因此来年侄子海结婚的时候,作为大伯的福娃包揽了一切事宜,替死去的弟弟做主了,为此他在南无村获得了一个好名声。
九
二福没死的时候,女子艳就住娘家了。原本艳的两个女娃子没跟来,二福死了,她们来哭姥爷,来了就没再回去。两个挂着鼻涕虫的外孙女来了就没回去的事,开始她们的姥姥莲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一来二福死了,莲成了寡妇,身边没人心里寡得慌,有女子和女子的女子缠在身边,她还怕她们回去哩;二来大伯子福娃和她商议说,二福死是死了,死了也放不下的是老二海的婚事——艳都两个娃了,当哥的海还打着光棍——二福肯定比活着的人还着急这件大事,那么没必要等守满当年的孝再给海办事,只要七七过了,就办喜事,老二一准不会怪咱,还要托梦感谢咱,“你说呢军他妈?”莲擦把眼泪骂起了二福:“管他高兴不高兴,他死球了算球,我和娃们还要美美地活哩。还守一年的孝?他活着不如人,耽误了我娃的事,死了还要看他的脸色,看他个死人敢!”福娃也不好说什么,帮着发落了二福,紧着就开始操办海的婚事。这样,艳的两个女子一直住到二舅娶了媳妇,还一直住着。
海结婚后,住着五间北厦西头的两间,把大个衣柜堵住原本和东头三间串通的门,就算独立门户了,只是吃饭还在一起。艳和两个女子住在娘家,莲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新媳妇的脸色渐渐不好看,开始骂起了自己的命不好,嫁了海这么个没出息的,人家结了婚都单门独院过,自己一过门就得给小姑子看娃娃。隔着个立柜,莲听见了,艳也听见了,莲对艳“哧”地笑一声,压低声音说:“别理她,你就当是狗叫哩!”艳翻翻白眼,呵斥自己的两个人事不懂的女子:“你俩要再敢往人家那边跑,看我打折你俩的狗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