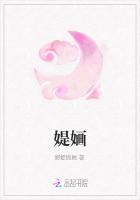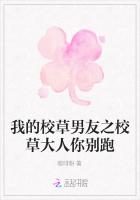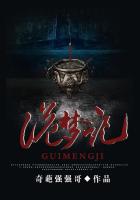战难,和亦难
山西的失守与黑旗军的惨败,使得光绪十年的春节黯淡了很多。
蛰居湖南故里的郭嵩焘,就是这幅巨大暗色画面中,一个早被遗忘的不起眼的小墨点。
早在中法纠纷之初,郭嵩焘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越南是扶不起的阿斗,中国内部问题又重重,应对其断然进行战略收缩。所以曾纪泽主张“投一羊以斗众虎”,郭嵩焘反驳:投一羊不足以斗众虎。恭亲王在西太后的强硬立场下主持边军入越,郭嵩焘也表反对,认为这是危险的玩火举动。中国应断然从越南进行战略收缩,首要问题仍是对内进行自强型改革。
这番言论在当年自然不受欢迎,他唯一的听众只有同乡好友朱克敬。两人在对外问题上较有共识。由于信息传递的迟缓,郭嵩焘直到十二月二十日始获知山西的失守。五天后,通过李鸿章的来函,这个噩耗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虽说是意料中事,但郭嵩焘还是为国家的又一次国力虚耗而痛心。倒是朱克敬很有些怨气得伸的快感,当场口占绝句一首:“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回头顾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
这里的老李指的是李鸿藻,老张指的是张佩纶。前者是清流的宗主,后者是清流的干将。两人一直持盲目的主战姿态。
战既不利,只有再谈。
1884年4月初,法国海军少校福禄诺在香港以密函一件托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德国人)带至天津送交李鸿章,提出四点议和条件:
1.云南通商;
2.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但措词可顾全中国体面;
3.撤调曾纪泽;
4.早日议和,兵费可极力相让。
反之,如果大清不允,法国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福禄诺指出:“中国南边三省素有内匪,现既与法国交界,法国如肯接济乱党,中国之边疆必永无肃清之日矣。”
对此,李鸿章认为,第一条可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滇境通商,他日果得人妥办,于国民决无大损,可于各海口通商之事验之。法人既得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使妥订约章,画界分守,当能永久相安,可于中俄接壤之事验之。”
第二条只是承认事实,除非能以实力改变事实,不然也只能以“顾全中国体面”为底线。
第三条纯属法国人的意气用事,属虚不属实,中国自不必在这等地方激怒法国人,所以也可允。
这下可不免又捅了舆论的马蜂窝。在外人看来,这无疑是湘淮两系之间的又一轮内耗。说白了。李鸿章在借刀杀人,公报私仇。实则不然。
在李鸿章看来,既然大势已去,“李宝协议”是想都不要想了。新约必然又要失去更多的东西,谁签谁挨骂。国内肯定是李中堂自己签。国外呢?自然是驻法大使签。换句话讲,谁当驻法国大使谁倒霉。关键时刻,李鸿章用自己的追随者许景澄换下恩师的爱子,正是不忘师恩的表现,更是对小字辈人才的保护。至于许景澄到任前的外交交涉,则暂由李鸿章的淮系亲信李凤苞代理。可惜外间不懂,纷纷责难李鸿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倒是曾纪泽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为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又说,“侄之志愿虽未遂,侄之体面仍存,中国议论则不可知,若西洋各国,则尚无议侄者,此李相之见爱处也。”
至于第四条主动声明“兵费可极力相让”,可见只是法国人的谈判余地,我们就要力争不赔款。
总之,“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于是,清政府于四月初四日(4月28日),下旨:“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许景澄着充出使法国、德国并义(意大利)、和(荷兰)、奥三国钦差大臣,未到任以前,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着李凤苞兼署。”以示和谈诚意。
李鸿章则被授予全权与福禄诺“从长计议,订立约章,言归于好”。
光绪十年四月十一日(1884年5月5日),福禄诺抵达天津,开始了新一轮的和谈。
法国人之所以选择福禄诺,原因一在福禄诺久在远东,熟悉清国情势;二在他与李鸿章有一面之缘,易于和谈。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两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这个简明条款共五款,主要内容如下:
1.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应“保全助护”中国和北圻的边界。
2.“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
3.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允在云南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
4.法国允“现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并将以前与越南所订有关北圻的条约作废。
5.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
如何认识这个“简明条款”呢?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大清国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能一不赔款二不割地,在当时那个强权横行的世界里,无疑是一次外交上的好成绩。
其次,正如李鸿章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清廷无论如何改变不了法占越南这个基本事实,再打下去只能徒增损失,两败俱伤。
和“李宝协议”相比,这次大清无疑失去了更多的利益,原因无他:形势所迫。正如李鸿章在“李福协定”签订后说的:“此次议款之速,实因桂、滇各军溃败,越事已无可为也。”又说,“去冬(法军)克山西,黑旗军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归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约内载明情愿不向中国索偿,尚属恭顺得体,足以风示各国。”
但是,这也是大清国的底线了。所以李鸿章后来会晤美国公使杨约翰时才说:“天津简明条约,中国已让到极头的地步,法国已尽占便宜,我为议和大臣知之最悉。”
总之,这次和平来之不易,对双方也都有好处。可惜,到头来却还是一场镜花水月。
两声霹雳
就在李鸿章奔忙于外交战场的同时,清廷正因北宁的惨败而进行一连串的人事调动。
先是在3月26日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另派湖南巡抚潘鼎新署理广西巡抚,贵州巡抚张凯嵩署理云南巡抚。
继而在三月十二日(4月7日),廷旨逮问黄桂兰、赵沃,黄、赵所部由署广西提督王德榜接统。但不等圣旨到达,黄已含恨自尽。赵则押送京师,与徐延旭一起被判斩监候。后特赦往西部充军。徐死于起程前夕,赵则不知所终。至于不听调遣的党敏宣则直接于军前正法,以儆效尤。同时又召两江总督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运筹中枢。遗缺则由湘军另一元老级重臣曾国荃补任。
三月廿五日(4月20日),预感不妙的张树声主动上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缺,“解任专治军”。结果,他的上奏未到京师,朝廷已开始严厉斥责他对北宁失败的“责任”。又由于张树声是淮系,而中央派往西南战场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是湘系,两人屡起摩擦,中央干脆于四月廿八日(5月22日)下决断:准张去职,只负责广东防务。另调太后的红人山西巡抚张之洞接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闰五月,又下旨将张革职留任。
这一轮的调动已是让人眼花缭乱。更让人震惊的事情还在其后。
北宁的惨败,原因很多。徐延旭的委任不当无疑是一大原因。而追其本原,当初朝廷只所以重用徐大人,正是由于以张佩纶、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们的大力举荐。这就为一些人的公报私仇提供了机会。
前文说过,张树声的那个“清流腿”儿子张华奎,屡遭清流讥讽,故而对张佩纶与李鸿藻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他自不会放过。
于是小张不惜花重金行贿,买通一批言官,上书弹劾张佩纶和李鸿藻。由于后者身为军机重臣,一时不易摇动,火力遂空前集中在张佩纶的身上。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就在这时发生了。
詹事府左庶子盛昱耐不住张华奎的一再缠磨,遂于三月八日(4月3日)也上了一道弹劾奏折。这份奏折首先抨击了张佩纶与李鸿藻的“轻信滥保”,酿成大祸。接着笔锋一转,将火力移向李鸿藻:
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事,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之所以有这一转,据说是由于盛庶子与张幼樵私交尚可,故来了这么一招“偷梁换柱”。可是盛庶子与李鸿藻也不是没有私交,于是他又随之对整个军机处都来个弹劾大扫描,如此重臣人人有份,反而法不责众,至少板子不会打到实处。而他攻击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的理由也很有意思。
原来,北宁兵溃之后,唐炯、徐延旭虽被革职拿问,但恭亲王考虑到战火未熄,拿问之事不宜搞得风声太大,以免乱了自家阵脚。所以未明发上谕。在盛昱看来,“逮问疆臣而不明降谕旨,二百年来无此政体。”所以一定要有个说法。
这样的弹劾奏章,可谓标准的雷声大、雨点小。因而在当时,几乎无人拿这份弹劾当回事。作为当事人的恭亲王没当回事,政治嗅觉空前敏感的李鸿章也没当回事。可晴天霹雳却突然平地炸响。
三月十三日(4月8日),太后以盛昱的折子为切入,发表懿旨,宣布恭亲王奕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特将军机大臣奕欣、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恭亲王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退休,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既别无建白,亦不无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
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刑部侍郎许庚身、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旋命贝勒奕匡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而作为重要当事人的恭亲王,此时正被派到东陵主持慈安太后的去世三周年祭奠。一切与24年前的申酉政变何其相像!
消息传来,极度震惊的李鸿章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朝同罢,汲取乳臭陋儒,更合足愭此危局?兴献用意殊不可解。小臣一疏,岂遂动听?恐弄成明季世界,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这里的“兴献”指的便是醇亲王。“兴献”典出明世宗。明世宗以旁系入主至尊,为其本生父上“兴献帝”尊号,引发大礼议之争。醇亲王正是当今皇上的本生父,所以李鸿章才借用了这个典故。
清流们也是一头雾水,正如李慈铭所说:“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所不解也。”
这就是晚清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甲申易枢”。
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当年咸丰帝暴卒后,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联手除掉这八个辅政大臣,另成立以后者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剿发捻,勤远略,发起自强新政,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个在君主专制国家里极不同寻常的二元权力结构。恭王的背后是文官集团,两宫太后的怀中则抱着至高无上的小皇帝。
起初双方尚能合舟共济,还真就平了内乱,并开展了“自强新政”(洋务运动),史称“同治中兴”。但是国家的制度并没有改变,不要说郭嵩焘所倡导引进的君主立宪制了,就算是隋唐的宰相制度也没有恢复。所以恭亲王与当年的张居正一样,只是大家心中的宰相,实则与万千官僚一样,也不过天子脚下的一个奴才罢了。偏偏西太后的权力欲又极强,还有点男权化倾向,老想着当不是武则天的武则天。莫说恭亲王,就是皇上,她也是不舍得放权的。所以同治暴死之后,才又抱了另一个小皇帝入宫,只有如此,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牢牢抓住至高无上的权力。既然要成为绝对权力,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就必须走人。尤其在东宫太后三年前莫名其妙地突然去世后,恭亲王更成了西太后最后的集权障碍物。而盛昱的奏折无疑就提供了这个“走人”的借口。甚至不惜让整个军机处跟着陪绑。
那么,西太后所选择的继承人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
新班子虽然平均年龄降低三岁,但无论能力还是威望,均远不如老班子。其中除阎敬明尚属精明干练之外,礼亲王世铎贪财好货,能力低下,有“非礼不动”之称。额勒和布倒是一生“廉洁自守”,但能力同样低下。张之万虽出身状元,但“一无所长,惟作画颇有家法,为数十年来置官所未有”。(文廷式语)至于许、孙二人则贪财好货不弱于世铎,奸诈又过之。
但在太后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绝对忠于自己。这就足够了。
至于在第二天命醇亲王商办军机大事更是暗藏玄机。从表面上看,醇亲王作为恭亲王的七弟,当今皇上的本生父,正该是西太后最忌惮的人物才对。实则不然。
原来,醇老七这个人一向是志大才疏、胸无城府。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清廉自守”。但偏偏这老七又是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更是个极端的仇外分子,所以对他六哥的那些个洋务运动、妥协外交,也就不免大有意见了。西太后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遂借老七之手赶走老六。而更绝的还在于,老七这个人虽然在对外问题上力主强硬,可在人身关系上却又是个极懦弱、极胆小怕事的主。